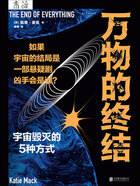
量化宇宙的厄运
当然,在我们中的一些人看来,宇宙末日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意识到宇宙随时都可能毁灭的那一刻。当时,我和本科天文系的同学一起坐在菲尼教授家的客厅地板上,参加我们每周的甜点之夜,而教授坐在椅子上,他三岁的女儿坐在他腿上。他解释说,早期宇宙空间的突然拉伸扩张,也就是宇宙暴胀,仍然是一个谜。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开始,又为什么结束,目前我们也没有根据说它不会再次发生。谁也不能保证,当我们在那间客厅里吃饼干喝茶时,不会发生一场谁也无法幸存的急速空间撕裂。
我感到自己像挨了一记闷棍,似乎我再也无法相信脚下地板的坚固。在我的脑海中永远刻下了这样一幅画面:那个小女孩坐在那里,在突然间变得不稳定的宇宙里旁若无人地手舞足蹈着。而教授则露出了一丝幸灾乐祸的笑容,转向了下一个话题。
现在我已经是一位公认的科学家了,终于理解了那种笑容。思考如此强大、不可阻挡而又可以用数学精确描述的过程,可能会让人病态般地着迷。我们的宇宙可能的未来已经得到了描绘、计算,并根据现有的最佳数据对可能性进行过加权。我们也许不能确定现在是否会发生新一轮激烈的宇宙暴胀,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我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方程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观点:尽管我们这些渺小无助的人类没有机会影响宇宙的结局,但我们至少可以开始了解它了。
许多物理学家对宇宙的浩瀚和强大到无法理解的力量已经有些见怪不怪了。你可以把这一切简化为数学,调整一下方程式,然后生活一切照旧。但是,当我认识到万事万物的脆弱性,以及我自己身处其中的无能为力时,这种震惊和眩晕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而当我抓住这个机会突然闯入这种宇宙视角后,有一种既可怕又充满希望的感觉,就像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感受生命的脆弱和无法想象的巨大潜力之间的微妙平衡。据说,从太空返回的宇航员对世界的看法都会有所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总观效应”。在高空看到地球后,他们可以完全感知到我们的小绿洲是多么脆弱,以及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作为也许是宇宙中唯一能够思考的生物,本该是多么万众一心。
对我来说,思考宇宙的最终毁灭正是这样一种体验。能够将思绪投放到时间的最深远之处,并且拥有能条理清楚地论述它的工具,是一种智力上的奢侈。当我们问道:“这一切真的能够永存吗?”我们是在暗中确认自身的存在,将它无限延伸到未来,评估并审查我们的遗产。知悉一个最终的结局给了我们背景、意义,甚至希望,并允许我们自相矛盾地从琐碎的日常关注中退后一步,同时更充分地活在当下。也许这就是我们寻求的意义。
毫无疑问,我们肯定越来越接近答案了。无论从政治的角度看,世界是否正在分崩离析,但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都正生活在一个黄金时代。在物理学方面,最近的发现、新的技术和理论工具使我们能够实现以前不可能的飞跃。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完善对宇宙起源的理解,但对宇宙如何终结的科学探索现在才刚刚复兴。来自强大的望远镜和粒子对撞机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了令人兴奋(或者令人恐惧)的新的可能性,并改变了我们对宇宙遥远的未来演变中哪些事情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观点。这是一个正在取得惊人进展的领域,使我们有机会站在深渊的边缘,窥视终极黑暗。并且,你知道的,我们的窥视是可量化的。
作为物理学范畴内的一门学科,宇宙学的研究其实并不是为了寻找意义,而是为了揭示基本的真理。通过精确测量宇宙的形状、其中物质和能量的分布及支配其演变的力量,我们找到了有关现实更深层结构的线索。我们可能倾向于将物理学的飞跃与实验室中的实验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我们对支配自然界的基本规律的了解,大部分不是来自实验本身,而是来自对它们与宇宙观测结果之间关系的理解。例如,要确定原子的结构,需要物理学家将放射性实验的结果与阳光谱线模式联系起来。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认为,正是令木块从斜面上滑下的力使月球和行星保持在其轨道上。这最终引出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它对引力进行了惊人的全新解释。广义相对论的有效性不是通过地球上的测量,而是通过对水星轨道异动及日全食期间其他恒星视位置的观测来证实的。
今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地球上最好的实验室里通过几十年的严格实验而建立的粒子物理模型并不完整,而关于这一事实的线索我们是从天空中得到的。对其他星系(像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一样包含数十亿乃至数万亿颗恒星的集合体)运动和分布的研究已经向我们指出了粒子物理学理论中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还不知道解决方案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宇宙的探索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宇宙学和粒子物理学的结合已经使我们能够探测时空的基本形状,清点现实由哪些零件构成,并穿越时间回到恒星和星系诞生之前的时代,以追溯我们的起源——不仅仅是生命体的起源,还是物质本身的起源。
当然,这个认知过程是双向的。正如现代宇宙学增进了我们对极小尺度的理解,粒子理论和实验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宇宙在极大尺度上的运作。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的结合,与物理学的本质有关。虽然大众文化会让你相信科学研究就是灵光一现的时刻和惊人的概念逆转,但其实我们了解的进步更多来自将现有的理论推到极端,观察它们在什么情况下会崩溃。当牛顿让球滚下山坡或观察行星在天空中的运动时,他不可能猜到我们需要一种引力理论来应对太阳附近时空的扭曲或黑洞内部难以想象的引力。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有一天会希望测量引力对一个中子的影响[4]。幸运的是,宇宙真的非常大,给了我们很多可以观察的极端环境。更妙的是,它令我们有能力研究早期宇宙,研究整个宇宙都是极端环境的时期。
关于术语,这里简单说明一下。作为一个通用的科学术语,宇宙学指的是对整个宇宙的研究,自始至终,包括它的组成部分,它随时间的演变,以及支配它的基本物理定律。在天体物理学中,宇宙学家是研究真正遥远事物的人,因为这意味着对宇宙开展相当多的观测,并且在天文学中,遥远的事物在时间上也处于遥远的过去。光从它们那里出发后,在到达我们这里之前已经旅行了很长时间,有时是数十亿年。一些天体物理学家主要研究宇宙的演变或者早期历史,另一些则专门研究遥远物体(星系、星系团等)及其特性。在物理学中,宇宙学可以偏向于更加理论化的方向。例如,物理系(相对于天文系而言)的一些宇宙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学替代公式,这些公式可能适用于宇宙诞生后万亿亿分之一秒内的情况;另一些人则研究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修正,这些修正可能涉及如黑洞般只能存在于更高维度空间的假想物体。一些宇宙学家甚至研究完全假设出来的有别于我们这个宇宙的宇宙。这些宇宙有着全然不同的形状、维数和历史——以便深入了解那些有朝一日可能被发现与我们有关的理论的数学结构[5]。
这一切的后果便是,宇宙学对不同的人来说意味着不同的东西。一位研究星系演化的宇宙学家在与一位研究量子场论如何使黑洞蒸发的宇宙学家交流时,可能会完全不知所云,反之亦然。
至于我,我喜欢这一切。我第一次知道有一门叫宇宙学的学科,是在我大约10岁的时候,通过接触斯蒂芬·霍金的书和讲座。他谈论的是黑洞、扭曲的时空和大爆炸,以及各种各样让我感觉自己的脑袋无法承受的东西。我怎么也听不够。当我发现霍金自称宇宙学家时,我知道那就是我想成为的人。多年来,我在整个领域内做各种研究,在物理系和天文系之间跳来跳去,研究黑洞、星系、星系间气体、大爆炸的复杂性、暗物质,以及宇宙眨眼间消失的可能性[6]。在我误入歧途的青年时期,我甚至还涉足过实验粒子物理学,在核物理实验室里玩过激光(无论记录上怎么说,那次火灾都不是我的错),在一个40米高的地下充水中微子探测器周围划过橡皮艇(那次爆炸也不是我的错)。
现如今,我非常坚定地成为一名理论家,这也许对大家都好。这意味着我不进行观察、实验或分析数据,不过会经常预测未来观测或实验的可能结果。我主要在一个被物理学家称为现象学的领域工作——这个领域处于新理论的发展和它们被实际检验的阶段之间。也就是说,我找到创造性的新方法,将研究基本理论的人对宇宙结构的假设与观测天文学家和实验物理学家希望在他们的数据中看到的东西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我必须大量学习一切事物[7],而这其中也有着极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