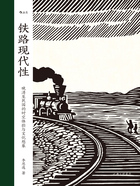
现代性的言说方式之二:理论思辨的建构
海德格尔在《世界作为图像的时代》中总结出了关于现代的五个根本现象——科学的诞生、机械技术的出现、艺术进入美学的视界、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以及对神的舍弃。“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乃是同一个过程。”[31]这一经典论断蕴含了有关现代性的两层意义,继而为后来现代性理论规划了两个方向。首先,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一定关乎某一/某些历史时期,尽管对时期的划分可能存在不同。其次,现代性是关乎人与世界的一个现象,而现代性的这一面逐渐被默认为一种整体的社会现象、集体的历史实践、抽象的经验范畴,或者简单讲,一个什么都能装的意识形态术语。
比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鲍曼(Zygmunt Bauman)对现代性的定义就是兼顾这两者的典范。“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当作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反思世界的秩序、人类栖居的秩序、人类自我的秩序——以及这三者之关联的秩序;现代性是思想,是关怀,是意识到自身的实践,其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实践并为自己有一天如果终止或仅仅是衰落而所留下的虚空感到担忧。”[32]“所谓现代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反思过程的开始,一项对批判和自我批判或多或少先进的尝试,一种对知识的渴求。我们在一系列文本和文献中接触到它,其带有自己时代的标志,然而又超越了时尚的诱惑和新奇的模仿。”[33]
卡林内斯库(Matei Călinescu)有关两种现代性的著名区分,也是遵循这两个方向对现代性自身的矛盾特征进行阐释。在19世纪上半叶的某个时期,所谓现代性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分裂:一则是作为西方历史文明中某一时期的现代性——科技进步、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的产物,包含进步的信条、对科技造福人类的自信、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对行动和成功的崇拜等——第一种现代性即布尔乔亚(bourgeois)观念下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而第二种现代性则是从一开始就采取激烈的反资本主义姿态,痛恨中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最终演化为先锋(Avant-garde)的一种美学概念。[34]
当然,各种有关现代性的理论因为不同学科背景、知识结构的差异而各有偏向。比如政治哲学出身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将现代性解释为西方文化的没落危机,而首要的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在从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到卢梭再至尼采的探讨中,施特劳斯勾勒出现代性所经历的三次浪潮,并论证现代性作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在经历过这三次浪潮后,再也不可能为我们自身提供一个统一坚固的基础。即不再有可以区分好坏的规范标准,我们也不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35]深受启蒙哲学熏陶的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则为一种根源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理想提出了辩护。他坚持“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项事业由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们制定,建立在他们致力于按照各自的内在逻辑去发展客观科学、普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主的艺术这些努力之上。哈贝马斯认为不能让启蒙背负所有权力的罪恶,现代性并不是“恐怖主义理性”(terroristic reason)的产物,而是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之间的一种斗争,也是生活世界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36]从后移民的角度看,现代性又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操作下,向外移民扩张的一部分。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说道:“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看,现代性已被视为导致了将统一性和普遍观念强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其使命就是将有序强加给无序,把服从的规则强加给未开垦的处女地。事实上,现代性使得欧洲人可以把自己的文明、历史和知识作为普遍的文明、历史和知识投射给别人。”[37]
不过所有现代性的理论模型中,影响最大的仍然是资本主义批判论述,即把现代性视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部分,对现代性的言说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方面的代表首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两人分别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和意识形态角度建构现代性的理论框架。哈维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历史具有使生活节奏加速的特征,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致世界有时似乎是内在于我们而崩溃了”。[38]
他以“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来形容这一处境,而其正是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在文化表征以及日常生活层面上对资本主义扩张、变革、危机的一种回应。詹明信则提出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叙事范畴,承载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喜欢讲的故事与承诺,而“现代性的理论,只不过是作为修辞的现代性自身之投射”。[39]他更是巧妙地将现代性划分为三种不同风格的文化表征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串联在一起,论证前现代、现代及后现代等时空体验、文化表征都是资本主义特定时期内的历史产物。[40]
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关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将现代性到来的绝对速度视作现代社会制度从传统社会秩序中分离出去的主要识别特征。他认为,时空分离作为现代性动力的主要来源时,时空转换与现代性的扩张同时展开;进而以“脱域机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这一概念阐释社会活动从原有的在地语境中抽离出来,在更广阔的时空系统中重新建立起新的抽象体系。在此脱域过程中,社会关系的确立包含了对抽象系统的信任(比如时分秒这样的时间秩序和个人归属的单位体制)以及知识的反思性运用。[41]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则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加速现象分解为技术加速、社会变革加速及日常生活加速三个相互作用的不同层面,由资本对速度的追求所驱动,三者构成一个相对自主的循环系统。[42]
相较于第一种言说方式,这种对现代性的言说更像是一种解释,借由将之前的形容词、比喻、想象置换为抽象名词、术语和论证,在去经验化的基础上,发展出种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思辨。事实上,在这种言说框架下,现代性总是被默认为一个抽象但完整的社会历史实体。相对于现代性经验的显现,这类理论家对现代性的历史起源和政治作用更感兴趣——与其将精力放在不可能穷尽的物与感受的描述上,不如力图对现代性的社会功能及造成的历史影响予以一种合理解释。但这也使任何关于现代性的言说永远受制于背后看不见的知识权力、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无意识。事实上,对抽象理论的癖好本身也是现代性的病症之一,在试图彻底抹杀经验的同时又前所未有地强调经验之独特,最终导致理论与经验的互不相容。[43]理论思辨这一言说方式的最大风险是沉溺于名词术语的快感中,以此替代知识上的努力,回避对真正问题的思考。
经验与理论之间的不可调和是摆在每一位现代性研究者面前的难题。但对于一个中国现代性的研究者来说,这尤其体现为西方知识理论和中国的历史经验之间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它有时被表述为历史(中国历史的特性)和价值(西方的普遍现代性)之间的斗争[44],或者直接简称为“西方理论”对“中国经验”的模式[45]。在其中,任何关于现代中国的研究都可以被转换为某些理论的试验场。或者用一则历史数据为其证实,或者又用另一则个案调查将其证伪。而后者又总是落入“中国特殊论”的怪圈——尽管这一提法背后充满强烈的情感诉求,可它的秉持者们却似乎忘了所有的非西方国家在各有各的不同历史经验这点上倒没有谁是特殊的——或许所谓的西方国家也概莫能外。即使我们能制造出一套以中国为中心的“理论”,但对于其在认识论上的价值、思想的意义方面依然半信半疑。因为这种在不改变关系本身的基础上要求调换位置的做法,本身就是在重复西方理论的范式。[46]西方的理论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吗?又或西方的理论适宜于中国的语境吗?这些难题困扰了我多年,直到在铁路的帮助下我才意识到我所焦虑的很有可能只是一些伪问题: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是能完全拿来用的——西方的理论当然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它连西方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如果这个“西方”存在的话);但也没有任何理论是完全不能用的——因为理论本质上就是围绕人与物的经验而引发的话语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