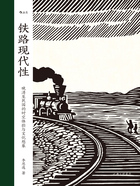
物的启示与可能
人与物、理论与经验,也许并没有它们表面上那般截然对立。说到底,解释的过程必然涉及描述,而描述本身也不可能完全避开解释。就像人内心最纯粹、最私密的东西无法仅仅从我们自身直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才会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物也要借助非物的对象来显现自己,主动参与到人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活动中。只要我们没有预先设定人与物、文化与技术是完全不同的范畴,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其实是在言说着彼此。以物之名的研究潮流最近十几年又在欧美学术界风起云涌,“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后人类”(Posthuman)或“非人类转向”(Nonhuman Turn)等术语层出不穷。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对于物的理解与探索与这些新兴理论没有直接的联系,反倒是受惠于拉图尔(Bruno Latour)早期从物的角度对现代性展开的批判,以及海德格尔中后期有关物的沉思。
拉图尔可能是最早直接将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诸种割裂危机归咎于物的历史被剥夺——作为主体的人和客体的物之间不对称、不平等的分类系统。他并不相信是什么凭空出现的时间意识、公共空间、民族国家划分了自然与社会,导致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是上述不对称、不平等的分类系统被投射进了空间(自然vs社会)和时间(传统vs现代)领域。拉图尔也不满意过去的社会学、人类学不假思索地将“社会”(同样适用于“自然”“文化”“技术”等)视作一种确定无疑的整体现象,并为所有事件提供一种所谓的“社会或文化解释”,即在自然或社会现象背后操纵、牵线的权力、结构、阶级、资本、性别等抽象实体。[47]“没有人观察到一则事实、一种理论、一个机器,可以独立于其所诞生的网络而单独存在。”[48]他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宣称根本没有一个叫“社会”/“文化”的领域存在,有的只是运动、替换、转换、翻译及参与——众多异质事物之间的联系。它用一种普遍的对称原则来处理人和物,将它们放进更为宽广、复杂的异质网络中一起进行分析。[49]对此最常见的误解就是以为它要求我们假装桌子、椅子有着和人一样的感受、语言和内心活动——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在我看来,拉图尔对“恢复物的阐释地位”之强调以及ANT理论,其实是建议我们要用言说主体一样的方式去言说客体,用呈现人一样的办法来呈现物。如果我们接受主体是多元的、复杂的、处于不断变化的建构之中,那么我们也不要理所当然地把物仅仅当作静止的、被动的、千篇一律的“死物”。ANT这种异质、多元的“块茎”(Rhizome)网络[50],让物在其中成为一条流变的轨迹,一个平等的“行动者”;我们借此展开探索,“跟随行动者自身,或确切地说,那些使它们行动的循环流通的存在者”[51]。
在这种对物的理解中,铁路的位置也会发生迁移:不再是“人—世界”之中出现了铁路这一物和技术,而是伴随着铁路的出现,我们对于世界的书写必须以“人—铁路—世界”的方式进行。[52]所以在本书中,我将铁路视作参与中国现代性这个复杂网络中的一员,跟随其流动:穿梭于技术、社会、身体、意识形态等不同的知识脉络;浸入又逸出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这些常见的叙事范畴。就这样,铁路成了一条可供辨识、追溯的线索,也是一种能动的联结和提供反思的纽带。
至于海德格尔的繁杂论述,我主要用两个绕口的关键词来把握其特征——“在世之在”(being-in-the-world)和“物之物化”(thinging, or the thing things)。首先,他将“在世界中存在”规定为此在的一种基本建构,是存在者本来就具有的存在方式。没有脱离世界之外而存在的主体/客体,因为“在先行于自身已经在世的存在中,本质上就一同包括有沉沦地寓于所操劳的世内上手事物的存在”。[53]“世界”这一概念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几经变化:从早期的“在世之在”到后来“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以及最终“世界是包含天、地、神,及有限性的人这四元的整体”。但世界作为一种本源上的容纳结构这一含义是一以贯之的。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批判了西方思想中三种常见的对于物的理解方式,它们分别将物视作不同属性的载体、多种感官受众的统一体,以及质料和形式的结合。[54]海德格尔认为这些看法过于贫乏,未能把握艺术作品的物性本源。因为从“在世之在”的前提下来看,“物”也有动词的属性——所谓“物之物化”;它根本上是一种和人有关的聚集(Versammlung),持续聚集着世界的关联,令世界与我们切近(nearness),也让我们得以在这世上停留。[55]后期海德格尔又从艺术作品的物过渡到日常之物——比如桥和水罐(the bridge and the jug),他在《筑·居·思》中以极富诗意的笔调描绘了作为物的桥梁是如何以自己的方式聚集起大地、天空、神圣者和终有一死的人。我将他的论证思路在这里做简要的概括:
1.桥当然是一物,但绝不仅仅是作为桥的物。
2.人们对于物的一般想象,过于贫乏地估计了物的本质:首先想象有一个空间,其中存在一座桥;然后桥开始能表达其他的一些东西;最后桥成为一种象征。这其实是把物想象成一个未知的X,然后为它附加上一些属性。
3.但桥并非只是连接早已存在的两岸。事实上,河岸能作为河岸而显现仅仅是因为桥跨越了河流。桥在以自己的方式让两边的河岸横亘于彼此,一边对着另一边。
4.桥是一物,但倘若不是它本质上聚集起了天、地、神、人这四重维度(即世界),桥根本不会是桥。[56]
那些对海德格尔这种绕圈思考完全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从张光直对“楚王问鼎”这个故事的卓越解读中获得类似的启发。张光直提出,“物”这个关键词在《左传》中的释义并非“物品”(objects),而是“牺牲”或“助天地交通之动物”。“夏代铸造铜鼎时在上面铸造了一些‘物’的形象,这样人们就能一目了然地认出哪些是能够帮助人类交通天地的器物,哪些是无助甚至有害的动物。”[57]换言之,汉语“物”的本源意义就是对天与地的沟通。所以,套用海德格尔的语言,我将自己对于铁路的研究概括如下:铁路当然是一物,但如果不是它以自己的方式在语言、视觉、事件、国家、运动、他者中聚集起现代性的世界,铁路也不会是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