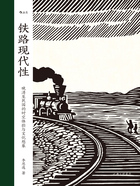
现代性的言说方式之一:经验的追踪与描述
现代性最著名的说法,必然要归属于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他从一开始就把现代性理解为与时间、速度有关的某种矛盾性体验。“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20]有趣的是,虽然波德莱尔的这句名言今天仍然是人们谈论现代性势必援引的经典依据,却鲜少有人真的会接受现代性仅仅是一些形容词的修饰。齐美尔(Georg Simmel)紧随其后,依然是把现代性看作一种新的生理和心理经验,但具体到紧张多变的都市空间,在其中生活的现代人不得不理智与震惊并存。[21]在1909年撰写的《罗丹艺术和雕塑中的运动动机》一文中,他宣称: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来体验(das Erleben)和解释世界,是固定的内容在易变的心智中被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都被心智过滤掉,而后者的形式永远变动不居。[22]
本雅明关于现代性的言说最难概括,多半源于他致力于为我们展现的是一连串关于现代性的辩证意象,所谓现代性的“碎片和瓦砾”,是“存在于背景中由来已久的新”。[23]它是拱廊街、街道、城市本身和它的废墟;是与作为古代性的巴黎相对的大众,消费的、革命的、仅仅是在街上来来往往无定形的大众;是商店里展览的、时尚和广告中宣传的商品;是全景图、摄影机,以及伴随摄影的震惊体验和想象;是闲逛者、懒汉、赌徒,以及妓女;是马克思、波德莱尔、卡夫卡;当然,还有机械复制时代灵光的消失,和那个背对未来、面朝过去的历史的天使。某种意义上,本雅明践行了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所谓“不要想,去看!”(Don’t think, look!)的信念——通过对现代性碎片的挖掘与修复,将其保存在一连串人与物的辩证意象之中。
福柯(Michel Foucault)对于现代性研究范式的重建和理论思辨方面的影响至今无人能敌。虽然他更多被视为具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家、思想家,但他的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性皆是得益于追踪、复原、重塑话语、空间和身体在历史语境中的经验形态,以此重构现代性权力关系的谱系。除了在有关疯癫、监狱的具体研究中有所体现外,福柯在《什么是启蒙?》这一短文中直接表明了自己对于现代性的经验倾向。“为什么我们不能将现代性设想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段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一种与同时代的现实发生关联的模式;一种由一些人所做出的自愿选择;总之,是一种思考和感受的方式;也是一种行动和表达的方式,其同时标志着某种归属关系,且将自身呈现为一项任务。”“与其致力于区分‘现代’‘前现代’或‘后现代’这些不同时期,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试着探究现代性的态度如何自形成伊始就与各种‘反现代性’的态度处于争斗之中。”[24]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亦是从一种经验的角度切入现代性的理论研究——他选择了速度这一典型体验,进而将其转化为一种超历史的、普遍的人类学范畴,发展出一套“战备现代性”(logistical modernity)的论述。一方面,他认为人类的感觉认知能力因为加速而与现代战争机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军事及电影技术如何改变了我们的视觉,现代武器是如何成为经验的认知工具;[25]另一方面,他亦分析了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为人类的经验和感知所带来的冲击:我们的移动速度与生活体验成反比,被一种所谓“引擎制造的恐惧”困扰。在被动的加速度过程中,我们不再是运动经验的主体,而沦为技术机器运作的物件——这种由机械速度引起的现代性焦虑处境正是他所称的“否定的视野”(Negative Horizon)[26]。
此外,对现代性的经验论述自然会和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文化表征、文学文本的解读结合在一起。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的文学批评可算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从歌德的《浮士德》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从波德莱尔的抒情诗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水晶宫”及“地下人”,圣彼得堡的都市街道和纽约的建筑空间——伯曼没有借助任何理论名词的权威性,而是直接进入历史与文本之中体会经验的力量、美感以及深度。毕竟,对他来说现代性就是一种经验和感受,关于“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人、生活中的各种可能与危险的体验”[27]。与此类似,在中文语境里,现代性的热潮和现代文学研究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李欧梵一方面立足于具体的历史文本,通过研究鲁迅、郁达夫等人的文学作品来探讨现代性的文学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从文化研究的路径追寻现代的时间意识和空间体验之转变,将其与晚清的印刷文化、民国上海的都市空间,以及现代主义的文学想象结合在一起。[28]王德威则提出了著名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之概念,颠覆了现代文学论述中长期以五四运动、新文学运动为正统的现代性叙事,将晚清小说作为一种新型文化场域涵盖在启蒙与颓废、革命与回转、理性与滥情、模仿与谑仿四个阐释框架中重新探讨,勾连出现代性的复杂经验。[29]近年来,他更提倡在革命与启蒙之外,将“抒情”作为主导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种可能,考察其于现代主体的建构作用。[30]
以上种种关于现代性的言说方式都可以归结为描述,即在挖掘、阐释某一时期的文本和事物的基础上勾勒出现代性的经验和感受。在批评者看来,他们的修辞往往胜过推论,过于依赖寓言或隐喻的阐释模式,或者仅仅借助关联和想象来对现代性进行界定。究其原因,这种言说方式所做的工作本来就是对经验的归纳。如果现代性的本质事关经验,那么任何言说与描述都意味着对经验的归类和对直观的抽离。况且归纳永无止境,这样现代性不仅是未完成的事业,注定更是永远完成不了的事业。现代性经验的描述就像它们言说的对象一样,将自身设置成了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言说不可言说之物、抵达不可抵达之彼岸,倒也因此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此外,我们总是可以利用矛盾的辩证法,将部分升华为整体,将新轮回为旧,将本雅明关于现代性碎片与废墟的研究视作有关现代性本身最灵动的发现。然而对于信奉去经验化的理论派来说,这种做法更多是在表达一种审美的姿态,欠缺理论思辨的洞见。事实上,在对现代性经验的言说中,不论是主动拒斥还是无奈回避,有关理论的焦虑始终沉潜其中。这在中国现代性的研究领域更是形成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宣称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不适合中国的历史语境;另一方面又强烈渴求任何新的理论学说,特别是对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