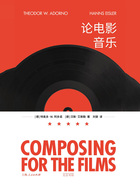
导言
电影不应被孤立地当作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去理解;只有把它看作运用了机械复制技术的当代文化工业之最具特色的媒介,它才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工业所传递的大众信息决不能被视作一种由大众原创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已然消失或是尚未出现。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方,就连自发性民间艺术的残迹都已消失殆尽,它充其量只存在于落后的农业区域。在这个高度工业化的时代,大众被迫去寻求放松和休息,以令其在异化劳动进程中所消耗的劳动力得以恢复。这种需求乃是大众文化的群众基础。强大的娱乐工业就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它还不断地制造新的需求并对其加以满足和再生产。
文化工业并非20世纪的产物,然而,只是在最近的数十年当中,它才实现垄断并被精心地组织起来。而正是因为这一进程,它获得了一种全新的品格——它已经变得无所不在。趣味和接受大都已经实现了标准化;此外,尽管产品具有多样性,消费者却只有表面上的选择自由。生产过程被划分为不同的行政领域,介入这一机制的任何东西都将承载其标记,进而被简化、中性化、平庸化。严肃艺术和流行艺术之间、通俗艺术和高雅的自主艺术之间的旧有区分,都不再适用了。所有的艺术,作为填充休闲时间的一种手段,已经变成了娱乐,尽管它还会吸收传统的自主艺术的某些材料和形式,以便构成所谓的“文化遗产”。正是这一混合的进程废除了艺术的自主性:让一个合唱团来唱《月光奏鸣曲》并且让一个看似神秘的管弦乐团伴奏,类似这样的事情如今比比皆是。不愿屈服的艺术被彻底排除在消费之外而陷于孤立。所有东西都被分解、被剥夺其真实含义,并被再度组装起来。这一进程的唯一标准就是尽可能有效地抵达消费者。受操控的艺术就是消费者的艺术。
在文化工业的所有媒介当中,电影最全面、最清楚地展示出了这一混合的趋势。与电影的技术元素——画面、对白、声音、剧本、摄影和表演——的发展与整合相同步,社会层面已经商品化的传统文化价值也呈现出混合的趋势。这样的趋势早先就非常重要——在瓦格纳的音乐戏剧中,在莱因哈特的新浪漫主义戏剧中,在李斯特和施特劳斯的交响诗中;此后它们被电影吸纳,构成了一种戏剧、心理小说、廉价小说、轻歌剧、交响音乐会和时事讽刺剧的混合物。
对于工业化之文化的批评性检视并不意味着对往昔寄予感伤的赞美。此种文化寄生于过去个人主义时代的成果而获得繁荣,绝非偶然。一方面既不应该把旧的个人主义的生产模式看作优于这种文化的模式并因此而将其放置在它的对立面,也不应该认为是技术导致了文化工业的野蛮状态。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并不适用于一切场合。至于何种技术资源可以用于艺术,应该取决于内在于后者的需求。技术为未来的艺术打开了无限的可能性,即使是在最贫乏的电影当中也都极其明显地会有这样的时刻。但开创了这些机会的原则同样也紧紧地联系着巨大的商机。关于工业化文化的讨论必须揭示出以下两个因素之间的互动:未来大众艺术的美学潜力及其当下的意识形态特性。
本书余下的部分将致力于承担此项任务,尽管难免挂一漏万。其中,我们处理了文化工业内一个严格限定的区块,即电影音乐的技术与社会潜力及其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