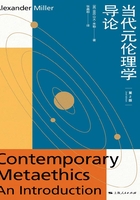
3.6 道德态度问题与开放问题论证
除了上述四个问题,情绪主义还面临如下问题。情绪主义的核心主张是,道德判断表达的不是信念,而是非认知的情感、情绪或感受。那么,道德判断究竟表达哪种情感、情绪或感受呢?如果情绪主义者不能合理地回答这个问题,他对道德判断的解释就显得空洞。
艾耶尔颇为明确地认为,道德判断表达一种特殊的感受,即伦理感受(ethical feeling)。在前面第3.1节引用过的《语言、真理与逻辑》的那段话里,我们看到艾耶尔提到“道德上”的反对、“特殊”的震惊和“特殊”的感叹符号:
接着说这种行为是错的,我并未做出任何关于这种行为的进一步陈述。我只是在表示我对这种行为的道德上的反对。这就像我用一种特殊的震惊语气说出“你偷钱”,抑或加上某些特殊的感叹符号写下这句话。[Ayer,(1936)1946,107,楷体部分是我标注的]
以及:
所表达的感受是一种特殊的道德上的反对。[(1936)1946,107,楷体部分是我标注的]
伦理符号……所出现的句子不过是表达对某种行为或情况的伦理感受。[(1936)1946,108,楷体部分是我标注的]
到20世纪80年代,艾耶尔仍然在谈独特的道德情感:
当[人们]做出情绪论所设想的那种道德判断,他们只是表达自己的道德情感,并鼓励他人分享这些情感。(Ayer,1984,30)
但艾耶尔这里所说的“道德上反对”这样的特殊伦理感受或情感到底指什么?对此,艾耶尔似乎有两种选择。一方面,他可以主张道德判断表达的感受或情感是无法还原的道德感受或情感,即完全是一种不可分析、自成一类的伦理感受。另一方面,他可以主张道德判断表达的感受或情感,可以根据非道德的感受和情感进行分析。我要论证的是,这两种选择都不可行。
为什么艾耶尔不能直接主张道德判断表达自成一类的或者无法还原的伦理感受?如果我们说道德判断表达无法还原、自成一类、不可分析的伦理感受,就不能根据感受来解释道德判断。什么是道德判断?那些表达伦理感受的判断。什么是伦理感受?那些由道德判断表达的感受。这样的解释纯属徒劳。何况,认为道德判断表达无法还原的伦理或道德感受,这有悖艾耶尔的证实主义。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艾耶尔如何理解将心理状态归于他人。他写道:
有意识的人和无意识的机器之间的区别,可以归结为不同种类的可感行为之间的区别。要断言一个表面上属于有意识的存在的对象,实际上不是有意识的存在,而只是木偶或者机器,只能根据这一点:它无法通过那些人们据以确定意识有无的经验测试。当我知道一个对象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有意识的存在根据定义所必有的样子,我便知道它确实有意识……当我断言一个对象有意识,无非是断言在应对任何可能的测试时,它可以展示出意识活动在经验上的表现。[(1936)1946,130]
所以,例如“琼斯疼痛”这一陈述有字面意义,是因为存在某些可观察的行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的出现可以证实这一命题。与这种行为主义分析相联系的问题,如今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讨论(例如,参见Carruthers,1986),但即便抛开这类问题,从艾耶尔的证实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观点来看,“道德判断表达无法还原、自成一类的感受”的观点显得很成问题。是否存在一些可观察的行为表现,可以构成对这种特殊的道德或伦理情绪的表达吗?我们不知道艾耶尔如何能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能设想表达反对的那些可观察的行为模式,但哪种可观察的行为可以表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道德上或伦理上的反对?缺少对这个问题的合理回答,“道德判断表达自成一类的伦理感受”的观点能否与艾耶尔的证实主义和行为主义相一致,就值得怀疑了。
“道德判断表达无法还原、自成一类的感受或情感”的主张,还面临一个更有力的批评:通过审视我们的道德考量经验,表明没有这样的感受。克里斯平·莱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是否存在……某种独特的道德情绪上的关注,这种关注可以单纯从现象学上得到确定,并区别于我们对其他各种价值的感受,在我看来这是很不值得考虑的问题。当人们对正确的事情关注正确的理由,便满足了美德的要求:没有必要再感受到一种特殊性质的关注……我怀疑的是,我们能否在道德判断现象学中找到足够基本的东西,以使“道德经验”的概念起到某种重要作用。(1988a,11—12)
诚然,我们可以试着将伦理感受解释为一个主体考虑某个道德判断时所具有的那些感受,但这种解释对情绪主义者来说没有用处,因为他要根据道德感受来解释道德判断,而不是相反。我们能理解一种可以独立于道德判断的概念进行解释的、无法还原的伦理感受吗?提出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是,追问我们能否理解这样的想法:某人(例如,一个幼小的孩子)不能做出道德判断,却能体验一种特殊的伦理感受。莱特同样很好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我们不太会认为幼小的孩子拥有幽默的概念,但幼小的孩子会因为做鬼脸和其他扮丑行为而发笑,这不妨归因于他们发现这些举动是好笑的。对于道德价值,我们可以找到类似的、前概念的东西吗?设想一个幼小的孩子因为看到骑师鞭打他骑的马而痛苦。这算一种表示道德上反对的原始情感吗?应该不难看到,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解释。孩子也许是被马蹄的巨响或者骑师的面具吓到了,也许是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1988a,11—12)
一种情感之所以是道德情感,是因为它来自道德考量的过程,来自形成道德判断的过程。但由于要根据道德判断表达的那种情感或感受来解释道德判断,情绪主义者对“一种情感为什么是道德情感”的解释,必须独立于“这种情感来自形成道德判断的过程”的看法。如果我们只能依据道德判断来解释道德感受,情绪主义者所要求的解释方式就不可能了。
所以我们有许多理由表明,为什么艾耶尔不能直接说道德判断表达自成一类、无法还原的伦理感受或情感。但艾耶尔何不断然抛弃“道德判断表达的感受或态度是一种特殊的伦理感受或情感”的观点?这么做可以削弱以上三个反驳的力量。如果我们将“杀人是错的”这一判断解释为只是表达对杀人的“普通”(common-or-garden)反对,不主张这种反对感受是某种特殊的伦理感受,那么我们似乎不必格外担心能否以经验方法证实一个主体拥有这种感受。 而且,这种“普通”的感受确实无可争议地存在,莱特的批评也就化解了。
而且,这种“普通”的感受确实无可争议地存在,莱特的批评也就化解了。
然而,这样的建议自身又会面临一些反驳。这里我将概述其中的两个反驳。
对道德判断的暗中消除
上述建议似乎蕴涵着,不存在一类具有独特道德内容的判断。我判断“杀人是错的”,就类似于判断“辣妹组合的最新单曲很糟糕”或者“鳗鱼冻不好吃”。正如后两个判断表达我对某种粗俗音乐和食物的厌恶,“杀人是错的”这一判断也只是表达我对杀人行为的厌恶。在后一种情形中,厌恶的程度或许更强,但区别也仅此而已:这些判断所表达的情感并无性质上的差异。但这样一来,我们似乎就接近于否认存在道德判断,或者至少是通常设想的道德判断这样的东西:按照通常的设想,“杀人是错的”这一判断在内容上确实有别于关于辣妹组合和鳗鱼冻的判断。因此,这不是暗地里消除了道德判断吗?![艾耶尔也许会说,基于刚刚提出的那些理由,他固然无法抓住我们的伦理语言的所有独特性质——已知其中一个性质,即伦理话语不同于关于审美价值或口味需求的话语,但他可以被理解为提出了一种关于我们的伦理实践的修正解释,换言之,他提出我们实际的伦理语言可以由一种替代语言所替代。这种建议的问题在于,根据艾耶尔本人认可的观点,它会使伦理学情绪理论所处的地位不再优于艾耶尔拒斥的主观主义和功利主义等各种自然主义式认知主义所处的地位。当谈到这些认知主义理论,艾耶尔写道:“我们当然不否认可能创造一种用非伦理词项定义所有伦理符号的语言,甚至不否认创造这样一种语言并以之取代我们自己的语言是可取的;我们否认的是,从伦理陈述到非伦理陈述的所谓还原与我们实际的语言约定相一致。”[(1936)1946,105]艾耶尔显然认为,不像自然主义式认知主义,情绪理论确实具有与我们实际的语言约定相一致的优点,而如果艾耶尔采取修正论进路,这种优点将不复存在。那么接受情绪理论而排斥自然主义式认知主义理论,似乎是没有根据的。](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26DC4C/163179531053883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1317175-y1OkpD1U06gIM5YenQp2zVJjHQJuW5Wf-0-5615d4f0246d48557593fa88c8258117)
艾耶尔可以试着坚持认为,判断“杀人是错的”所表达的情感,在性质上类似于关于辣妹组合和鳗鱼冻的判断所表达的情感,同时继续认为存在一类特殊的道德判断,因为他可以论证说使一个判断属于道德判断而非其他某种判断的,不是它所表达的情感的类型,而是表达情感所基于的特殊理由。前面提到的三个判断都表达相同的反对感受,但它们的表达所基于的理由截然不同。这样,我们不就有办法区分道德判断、审美判断和味觉判断等不同种类的判断了吗?
不管这种见解本身有什么样的优点,它显然不能为艾耶尔这样的情绪主义者所利用。看看前面(第3.1节)艾耶尔提出的对道德分歧的解释,就能明白这一点:
正因为当我们着手处理有别于事实问题的价值问题时,论证无法奏效,我们最终只好诉诸谩骂。[(1936)1946,111]
根据这里所使用的“论证”的意思,和某人进行论证便是和他进行推理。那么,艾耶尔对道德争端的解释蕴涵着虽然关于人们对事实问题的看法,亦即信念,可以和他们进行推理,关于他们的非认知感受和态度却不可能进行推理。如果这是可能的,艾耶尔对道德分歧的正式解释就会失效。而这表明,艾耶尔不能采取上面所说的做法。我们区分道德判断、审美判断和味觉判断时,不能主张“尽管它们表达同一种情感,这些情感的表达则是基于不同的理由”:因为根据艾耶尔的观点,我们的情感和我们关于事实问题的信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完全没有理性方面的基础。
情绪主义与开放问题论证
如第3.1节所指出,艾耶尔反对自然主义版本的认知主义的主要论证是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有意思的是,相同的论证可以用于反对这一观点:道德判断表达赞成和反对的普通情感。让我们考虑:
(17)采用反证法(reductio),假定通过概念分析表明,“琼斯判断杀人是错的”等价于“琼斯表达了反对杀人的非认知情感”。![艾耶尔谈到“一篇哲学上严格的伦理学论文不应该做出伦理宣告。但它应该通过对伦理词项的分析,表明所有这些宣告属于何种范畴”[(1936)1946,103-104,楷体部分是我标注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艾耶尔的情绪理论的重要主张涉及一种分析等价关系或者达到一种概念分析。](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26DC4C/16317953105388306/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1317175-y1OkpD1U06gIM5YenQp2zVJjHQJuW5Wf-0-5615d4f0246d48557593fa88c8258117)
那么,
(18)“琼斯表达了反对杀人的非认知情感”的意义包含着“琼斯判断杀人是错的”。
但这样一来,
(19)认真地提问“琼斯表达了反对杀人的非认知情感,但他判断杀人是错的吗”的人会显示某种概念混乱。
并且
(20)对于任何“普通”、非认知的反对情感,“表达那种情感的行为是否等同于做出道德判断”总是一个开放问题。也就是说,这总是一个开放问题:表达那种情感的人做的是道德判断、审美判断、审慎判断,还是其他判断。提出这种问题的人不会显示概念混乱。
所以,
(21)“琼斯判断杀人是错的”不可能分析地等价于“琼斯表达了反对杀人的非认知情感”。
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个论证面临某些非常严重的困难(第2.3节),但这里我想说的要点只是针对个人(ad hominem)的如下看法:艾耶尔本人用于反对自然主义式认知主义的论证,实际上同样可以用于反对“道德判断表达赞成和反对的普通感受或态度”的主张。
尽管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失败了,但我们已经在第2.4节看到,达沃尔、吉伯德和雷尔顿提出的这一论证的现代变种,对分析自然主义至少构成一种暂时性的反驳。这一版本的论证能用于批评艾耶尔这样的情绪主义者吗?为了类似地构造一个反对艾耶尔的情绪主义的论证,我们可以关注这样的事实:道德话语的一个显著功能是说服他人,尤其是促使他人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如彼得·基维(Peter Kivy)所注意到的,查尔斯·斯蒂文森发展的那种情绪主义很好地抓住了道德话语的这一特征:
伦理争论的直接目的蕴涵在道德价值词项的规劝意义中:晚期斯蒂文森称为“准命令”意义。这些词项表明我们的赞成,但它们也促使他人接受我们的态度。“我赞成;你也得这么做”,这大致就是斯蒂文森对“好”的分析。(Kivy,1992,311;另参见Stevenson,1937和1944)
这似乎是一个概念事实:当我判断“琼斯判断x是好的(坏的)”,我会期望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琼斯将倾向于要求我分享他赞成(反对)x的非认知情感。 我判断“琼斯做出了一个道德判断”,有别于我判断“琼斯做出了一个审美判断”或者“琼斯做出了某个非道德的味觉判断”,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例如,在琼斯做出一个审美判断的情形,要求我分享他对于判断对象的非认知态度,似乎是空洞和无力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头脑清楚、心理健康的主体判断“杀人是错的”,却不在乎我是否赞成杀人;但很容易想象一个头脑清楚、心理健康的主体判断“鳗鱼冻不好吃”,却不在乎我是否钟爱它们,抑或判断“《庄严弥撒曲》是绝妙的”,却不在乎它是否对我本性中非认知的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如基维所说:
我判断“琼斯做出了一个道德判断”,有别于我判断“琼斯做出了一个审美判断”或者“琼斯做出了某个非道德的味觉判断”,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例如,在琼斯做出一个审美判断的情形,要求我分享他对于判断对象的非认知态度,似乎是空洞和无力的。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头脑清楚、心理健康的主体判断“杀人是错的”,却不在乎我是否赞成杀人;但很容易想象一个头脑清楚、心理健康的主体判断“鳗鱼冻不好吃”,却不在乎我是否钟爱它们,抑或判断“《庄严弥撒曲》是绝妙的”,却不在乎它是否对我本性中非认知的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如基维所说:
我们很能理解,为什么对道德赞成的表达同时应该是规劝他人同意自己。当我表达我的道德态度,目的在于使他人以特定的方式行动;因为近乎处于整个道德制度核心的是保护各种利益,防止伤害,促进人类福祉,确保公平对待,等等。美学中有类似的东西来解释“审美命令”的存在吗?当我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完全不依赖于我的审美品位和态度,这种品位和态度也不会激发任何相关的人所关心的行动,我就不应该有丝毫的兴趣,规劝他人分享这种品位和态度。(1992,313;另参见Kivy,1980,尤其是358—364;and Railton,1993a,286)
给出了上述看法,我们现在可以提出如下开放问题式的论证,以反对“道德判断表达普通的非认知情感”的观点:
(22)判断“琼斯判断x是道德上好的”和期望“其他条件不变,琼斯将倾向于要求我分享他赞成x的非认知情感”之间具有概念联系(修正的内在主义)。
(23)合格、有反思能力的言说者相信他们能够想象头脑清楚(并且心理健康)的人判断“琼斯表达了赞成x的情感”,却不期望“其他条件不变,琼斯将倾向于要求我分享他赞成x的非认知情感”。
这里所想象的人也许确实疑惑,琼斯所表达的赞成或反对是审美上的、味觉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
(24)如果判断“琼斯表达了赞成x的非认知情感”和期望“其他条件不变,琼斯将倾向于要求我分享他赞成x的非认知情感”之间没有概念联系,我们就可以期待合格、有反思能力的言说者具有(23)中所描述的信念。
所以,
(25)除非能更好地解释(23)中所描述的信念,我们就有理由得出,判断“琼斯表达了赞成x的非认知情感”和期望“琼斯要求我分享他的非认知情感”之间没有概念联系。
所以,
(26)除非能更好地解释(23)中所描述的信念,我们就有理由得出,判断“琼斯判断x是好的”不等同于判断“琼斯表达了赞成x的非认知情感”。
所以,
(27)除非能更好地解释(23)中所描述的信念,我们就有理由得出,判断“x是好的”不能依据“表达赞成x的非认知情感”来分析。
跟之前一样,我们并未得到一个击倒式论证,而是给情绪主义提出了一种挑战。鉴于艾耶尔不会选择去寻求道德判断和表达感受之间某种非分析的同一关系,他似乎只能选择否认(22)中的联系是一种概念的或内在的关系,并转而论证,判断“琼斯做出了关于x的道德判断”和期望“琼斯要求我分享他对x的非认知态度”之间,充其量是一种偶然的和外在的关系。借助后面这种论证思路,艾耶尔这样的情绪主义者 能否合理地回应上面的论证。
能否合理地回应上面的论证。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这里我无法讨论。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但这里我无法讨论。
由此,我们的结论是,艾耶尔未能令人满意地回答这个问题:道德判断表达的是哪种非认知态度?那么,是否有某种可行的非认知主义,既可以避免第3.5节中所说的问题,又可以避免道德态度问题?接下来的两章,我们将考察布莱克本的准实在论和吉伯德的规范表达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