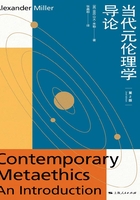
3.5 情绪主义的问题
|问题1| 蕴涵错误问题
情绪主义是一种投射主义(projectivism)。当我们在一个评价性判断中使用“是错的”,例如,当我们判断“杀人是错的”,似乎是把“错的”当作一个谓词,就类似于我们语言中的非评价性谓词。换言之,我们把“错”视为杀人这种行为的一个属性。由此,我们认为“杀人是错的”和“黄金是金属”相似,因为“错的”和“金属”都是真正的谓词,指向事物的真正属性。但根据情绪主义,用这种观点来解释“杀人是错的”并不正确:当我们把“错”视为事物的真正属性,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将我们的情感或情绪投射到世界上。“错”并非真的是世界中的事物的一种属性,而是我们对世界产生某种态度或情感时投射到世界上的某种东西。如布莱克本所说:
我们将态度、习惯或者其他承诺投射到世界上,这些东西不是描述性的,但是当我们说话和思考时,就好像它们是我们的话语所描述的那些事物的一种属性,我们可以对这种属性做出推理,进行认知以及产生误解,等等。投射就是休谟所说的“将所有自然对象涂上和染上来自内在情感的颜色”,抑或心灵“通过自己给世界着色”。(1984,170—171)
情绪主义的问题是,解释这样的投射如何可能不是一种差错或错误。如果我们的言谈和思考显示存在“好”这种属性,而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属性,我们的言谈和思考不就有很大缺陷吗?对此,为了避免这种错误,合理的反应不应该是要求消除或者至少修正我们的道德实践吗?
在日常生活以及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上面这样的担心。例如,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胜利》(Victory)中,故事的讲述者和故事里的戴维森船长疑惑,海斯特将莱娜救出臧加科莫的旅行乐团是出于什么动机:在海斯特心里,这种行为是情急之下利用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还是解救一个受折磨的人?由于海斯特具有一种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世界上的倾向,讲述者和戴维森担心海斯特是否因此犯了这种错误:当他的行为实际上只是情急之下利用一个漂亮的年轻姑娘,他却以为是在解救一个受折磨的人:
戴维森和我都怀疑这在本质上是否是解救一个受折磨的人。我们不是两个以自己的性情给世界染色的浪漫主义者,但我们早已对海斯特的为人心知肚明。(1915,66—67)
由此,戴维森和讲述者排除了海斯特的错误,但这么做的前提是认为他倾向于以自己的性情给世界“染色”,从而可能陷入某种相关的错误。
我们再看一个更普通的例证,即具有字面意义上的投射功能的投影仪。设想一位解剖学讲师用投影仪向学生展示关于人类大脑的幻灯片。他调试投影仪,使之照射到一面平整的白墙上。讲课过程中,讲师和学生的讨论就“仿佛”墙上有一张人类大脑的图片。比如,讲师问一个学生图片的哪一部分表示小脑,另一个学生让讲师指出图片上的脑干部分。但显然,墙上并非真的有图片,而只有投影仪所投射的图像。在某种意义上,这在眼下的例子中不会让我们感到担心:讨论时“仿佛”墙上真的有一张图片,这无非是一种方便而无害的虚构。然而,当我们判断“史密斯折磨猫的行为是错的”时,认为自己是在“投射”,就很令人不安了。我们真的可以接受这样的看法吗:史密斯的行为并非真正是错的,“错”这种属性只是投射我们的忧虑或震惊?
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对道德属性的理解上是投射主义者,他如何避免这样的蕴涵:将道德属性赋予事物总是会让我们陷入错误?
|问题2| 弗雷格—吉奇问题
这个问题以彼得·吉奇(Peter Geach)的名字命名,他在Geach(1960和1965,在后者中,吉奇将这一反驳归于弗雷格)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经典的现代阐述。根据情绪主义,当我真诚地说出“杀人是错的”这个句子,我不是在表达信念或者做出断言,而是表达某种不具有真假的、非认知的情感或感受。
由此,情绪主义者主张,在“杀人是错的”表面上用于断言杀人是错误行为的语境中,这个句子实际上是用于表达一种反对杀人的情感或感受。然而在有些语境中,“杀人是错的”即便表面上也不是用于做出断言,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语境?句子“如果杀人是错的,那么让弟弟杀人是错的”便是一个例子。显而易见,即便在表面上,这个句子前件中的“杀人是错的”也不是用于做出断言。那么,情绪主义者如何解释“杀人是错的”在诸如条件句前件这样的“非断言语境”(unasserted contexts)中的功能?由于它在这种语境中不是用于表达反对杀人,对其语义功能的解释必定不同于解释“杀人是错的”表面上表达直接断言的情形。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解释下面这样的有效推理:
(8)杀人是错的。
(9)如果杀人是错的,那么让你弟弟杀人是错的。
所以,
(10)让你弟弟杀人是错的。
倘若“杀人是错的”在断言语境(8)中出现时的语义功能,不同于它在非断言语境(9)中出现时的语义功能,以上述方式推理的人不就完全犯了偷换概念(equivocation)的错误吗?上述推理如果是有效的,(8)和(9)中出现的“杀人是错的”必须具有相同的意义。而如果“杀人是错的”在(8)和(9)中具有不同的语义功能,它在(8)和(9)中当然不会有相同的意义。所以,上述推理看来和如下推理一样无效:
(11)我这瓶啤酒有一个头。
(12)如果某样东西有一个头,那么它必定有眼睛和耳朵。
所以,
(13)我这瓶啤酒有眼睛和耳朵。
这个推理显然无效,因为它偷换概念,“头”在(11)和(12)分别出现时具有不同涵义。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这个问题:在基础逻辑中,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已知推理是否有效?一种途径是构造真值表(truth-table),检查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所有的前提为真而结论为假。如果有这种情况,推理无效,反之,则推理有效。但是,如果推理的某些前提[例如(8)]甚至不能依据真假来评价,这种办法又有什么意义?
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弗雷格—吉奇问题为什么不会困扰认知主义的伦理理论,这类理论认为“杀人是错的”具有真值条件,真诚地说出“杀人是错的”可以表达信念。根据认知主义,像上面(8)和(9)到(10)这样的道德假言推理,跟下面这样的非道德假言推理并无差异:
(14)下雨了。
(15)如果下雨了,那么街道是湿的。
所以,
(16)街道是湿的。
尽管事实上,“下雨了”在(14)中是断言的,在(15)中则否,为什么这个非道德假言推理仍然有效呢?答案显然是,(14)中通过断言“下雨了”所得到的事态,和(15)的前件所假言地引入的事态是相同的。(14)中的“下雨了”用于断言实现了一个事态(下雨了),而(15)则断言如果那个事态实现了,那么另一个事态(街道是湿的)也会实现。赋予相关句子语义功能的,自始至终都是简单的断言语境中所断言实现的那种事态。至于从(8)和(9)到(10)的推理,我们不知道情绪主义者如何能提出类似的解释:我们不知道“杀人是错的”在(9)的前件中的语义功能,如何能由它在(8)中所表达的情感来赋予。
由此,情绪主义者面临的弗雷格—吉奇挑战是:当道德语句出现在诸如条件句前件这样的“非断言语境”中,如何给出一种符合情绪主义的解释,可以不损害这些语句所构成的那些推理在直觉上的有效性?
|问题3| 分裂态度问题
如果“对”、“错”等属性只是投射我们自身的情感和态度,我们如何能认真对待它们?布莱克本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是:
投射主义者能认真地对待责任、义务、“神声音严肃的女儿” 这样的东西吗?倘若他否认这些代表着外在的、独立的、权威的要求,他如何能认真对待它们?那么,他一方面持有自己的道德承诺,一方面又认为它们是没有根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难道不是一种分裂的态度吗?(1984,197)
这样的东西吗?倘若他否认这些代表着外在的、独立的、权威的要求,他如何能认真对待它们?那么,他一方面持有自己的道德承诺,一方面又认为它们是没有根据的,这在某种意义上难道不是一种分裂的态度吗?(1984,197)
立场一贯的投射主义者真的能避免最终接受一种法国黑帮道义吗?(1984,ibid.)
|问题4| 心灵依赖问题
倘若如休谟所说,“对”、“错”等属性是“我们的情感的产物”(Blackburn,1981,164—165),不就意味着这些属性以一种可疑的方式依赖于我们的情感吗?情绪主义不就蕴涵着如果我们的情感发生变化,“对”和“错”也会发生变化(类似于投影仪上的变化导致白墙“上”的东西变化)?以及如果我们的情感消失,“对”和“错”也会消失(类似于毁坏了投影仪也就消除了白墙“上”的东西)?情绪主义能避免让道德以如此糟糕的方式依赖于心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