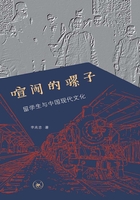
自序
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字:留学。自从1847年容闳等三名学子随美国传教士布朗夫妇东渡新大陆,首开中国人留学的纪录,这一百七十多年来,留学之潮由小变大,奔涌不息,其间尽管出现反复(如留美幼童中途撤回,“冷战”时期中国停止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总体上呈现着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中国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世界大串联”浪潮,至今方兴未艾。
从推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中国文化思想现代转型的角度看,留学的意义与贡献,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胡适将留学比作摆渡西方文明的“舟楫”,将留学生比作“舵手”与“篙师”;季羡林将留学生比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现代化的报春花,都是可以成立的。举凡现代中国的一切,从物质文明到文化思想,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莘莘学子从国外引进的。据统计,1900年至1937年在日本院校注册的中国学生的人数为十三万六千人;1854年至1953年的一个世纪内,中国留美学生达两万一千人;另据1945年《联大八年》的纪念册统计:西南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中,留学生一百五十六名,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留学,便没有现代中国。
百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中国的社会政治外交危机激荡的结果,种子其实多年前早已布下,且与“留学”有直接的关联。其远因,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当时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惊破了中国人的千年迷梦,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寻求“制夷”之道,遂有后来的洋务运动及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留学生派遣;其近因,则主要由三件大事构成:以中国的惨败告终的1895年甲午战争,在宣告中日国际地位发生逆转的同时,也宣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破产、西方近代文化的胜利,第二年,清政府就向日本派出十三名留学生,以此为开端,留学的大门正式开启,有识之士纷纷东渡日本;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进一步摧毁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其情形正如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从那次义和团失败之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外国。所以经过义和团之后,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过一天。”(《三民主义第五讲》,1924)在沿海地区的知识界,留学渐成一种风气;1905年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提前废除,釜底抽薪,断绝了中国学子历来的安身立命之路,是年留日狂潮勃兴,五千中国留学生一下子涌到东京,第二年激增到一万三千。至此,出洋留学之潮,已是沛然莫之能御。客观地看,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学子想接受地道的现代教育,成就一番事业,出洋留学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如开弓之箭。此后十年,正是中国文化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学取代旧学的时期,日译的西方新概念、新名词,通过留日学子之手铺天盖地涌入中国;与之同时,留学欧美的中国学子也不断地给故国输入新文法、新学理、新思想,尤其是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留美学子,在大洋彼岸酝酿了一场文学革命,不仅在理论上为新文学鸣锣开道,也在操作层面上为新文学的诞生做了示范。至此,中国的现代新文化已是呼之欲出。
缅怀前贤的留学壮举,不由令人感慨万端。莘莘学子在异域度过宝贵的青春岁月,孜孜矻矻,遨游于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海洋,含英咀华,为沉疴深重的祖国把脉,并为其设计未来。鲁迅和胡适,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留学时代写下的《摩罗诗力说》《非留学篇》,至今依然熠熠闪光。他们都具备文化圣人的气质,一个发誓“我以我血荐轩辕”,一个立志“他日为国人导师”。他们的救国方略都抓住了根本:一个主张“立人”,从精神入手,改造国民性,建设一个外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不失固有血脉的新中国;一个主张“树人”,通过滴水穿石的教育,为未来“造新因”。他们的思想基石,在留学时代就已形成,回国之后,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旗手。确实,没有他们的呕心沥血,唤醒国人,开启中国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及时地接轨,中国人的“球籍”恐怕真的不保。
然而,留学给我们带来的并非都是风和日丽的美景。纵观20世纪中国的文化景观,处处带有“半殖民地”的烙印,每一种流行的思潮背后,都有西方的依傍,什么中国的杜威、中国的歌德、中国的席勒、中国的卢骚、中国的左拉、中国的泰戈尔、中国的曼殊斐尔、中国的赫胥黎、中国的毕加索,不一而足,本土的文化圣祖,不是被打翻在地,就是被彻底遗忘;同样,中国思想界、文坛上无休止的争论,多半是西方已有论争的翻版,中国学子们挥舞着从西方师父那儿舶来的利器,打得不可开交,偌大的中国知识界,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各种思想、学说、主义在这里冲折较量,消耗着巨大的能量。在这种处境下,中国人失去了自己的价值标准与话语方式,一切唯西方马首是瞻,陷于被言说、被解释、被界定的可悲境地。这一切无疑都是留学带来的副产品。
追本溯源,留学本是西方强势文明在全世界扩张的结果,而落实到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超稳定”精神结构的农业文明古国,事情不能不变得格外尴尬。众所周知,中国人对留学的态度曾经历过一个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从将异域西方视若蛮夷鬼域,无人愿往,到对它顶礼膜拜,趋之若鹜。这个极具戏剧性的逆转过程,反映了自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经受过七十年的挫折和失败,中国人文化自信心失落,由“中体西用”向“全盘西化”倾斜,文化思想主权不得不拱手相让的严峻现实。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扭曲和伤害是无法估量的,造成了他们文化人格的分裂,精神定力的丧失。
更何况,“西方”并非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多元的存在,有英国式的,有法国式的,有俄国式的,还有日本式的。因此,如何西化,以哪一国为效仿的样板,便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从客观的结果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留学国的社会制度、政治模式和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年轻的中国学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所谓“留日派”“留俄派”“留欧派”“留美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当然,中国学子的家庭出身,固有的知识教养,乃至个人的性格气质,都潜在地制约着他们对异域文化的选择与认同,两者一经契合,便产生各式的西方文化代理人,比如胡适之于美国,丁文江之于英国,瞿秋白之于俄国,周作人之于日本;单独地看,他们自成体系,无懈可击,合到一起,便不免扞格,发生碰撞。这种碰撞到后来,在客观的态势上,形成了以胡适为首的留欧/美派和以鲁迅、郭沫若为首的留日/俄派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在社会矛盾不断升级、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背景下,冲突博弈,形同水火;而暗中操纵这一切的,是代表着人类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俄、美超级大国。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是没有任何留学背景的毛泽东,这位自学成才的伟人一向瞧不起留学生,早在1920年给友人信中就这样写道:“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对其有更严厉的批判——
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检来的。
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这种毛病,也传染给了共产党。
毛泽东对留学生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然而一面倒地否定,却有失公平。毛泽东固然没有留过学,但这并不意味没有受留学的影响,他的思想,他的理论,包括他用的词汇(如上述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等)很大一部分都是留学生从国外引进的,经过他的天才头脑的整合,变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斗争哲学。广义地说,近代以降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留没留过学,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受“留学”的影响。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是西风东渐历史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宿命,其是其非,都包含在其中。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传统的中国好比是驴,近代的西方好比是马,驴马杂交之后,产下现代中国这头骡;现代中国文化从此变成一种非驴非马、亦驴亦马的“骡子文化”。根据生物杂交的一般原理,第一代的杂种兼具双方的优点,品种最佳,之后逐渐退化。这个生物学原理同样符合中国现代留学史的实况。第一代留学生里多出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文化巨人,如严复、陈寅恪、鲁迅、丁文江、胡适、郭沫若等,他们为中国现代文化奠定了基础,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但随着时代变迁,岁月流逝,这种学贯中西、兼具马驴优点的“超级骡子”越来越少,他们的遗产也越来越难以为后人继承。然而仔细想一想,也只好释然:既然产生这种“超级骡子”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骡子文化”每况愈下也是情理中的事。到后来,“骡子”分成两大派:一派性近驴,姑且称“驴骡”,一派性近马,姑且称“马骡”;前者号称“寻根派”,后者号称“现代派”,他们争吵不息,经常上演“关公战秦琼”的大戏,表面上热闹,却少了祖先的眼光和气魄。“驴骡”个头小,势单力薄,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由于血液里文化基因的作用,时时萌发返本的冲动,弄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新古董,让辉煌的古典传统重新闪光一把;“马骡”个头高大,气宇轩昂,在现代的历史语境中一直占据优势,隔三岔五从西方师父那儿批发些新鲜玩意儿,各领风骚三五天,其语言是中式鸟语,深奥如天书,故只能在一个极小的行家圈子里通行。有意思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运昌盛,国粹行情日渐看涨,“马骡”们也纷纷鼓吹起中国传统文化来,用的却是他们的洋腔洋调。真是叫人哭笑不得。
应当承认,中国现代的“骡子文化”是一种不自然的、主体性欠缺的文化,它摇摆多变,缺乏定力,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刺激下每每陷于非理性的狂奔。过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化语境至少经历了六次剧烈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作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历史命运,我们无法对此做简单的臧否,只能心怀忧思,静观其变。众所周知,现实中的骡子不能生殖,故而性情暴躁。那么文化学意义上的骡子又怎么样呢?这一百年来接连不断的喧哗、骚动与争斗,是否就是“骡子文化”遗传焦虑的一种表征呢?
二十几年前留日归来,在反刍四年异域生活,写《暧昧的日本人》的时候,萌生了研究留学生文学的念头。当时只觉得这个题目有趣而且重要,上手之后,才发现自己掉入一个陷阱。凭自己可怜的知识学养,要想说清楚这个涵盖古今中西的题目,简直太难了。起初真是无从措手,中间几次都想放弃。能够坚持下来,完全是出于职业道德的鞭策,那种艰难,犹如西绪弗斯推着巨石上山。由于不擅长理论思辨,只好采取最笨拙的办法:一遍又一遍地细读文本和相关历史文献,发现蛛丝马迹,摸着石头过河。惨淡经营十余年,弄出这么一个东西。本书解读十余位中国现代文学/文化史上重量级的“骡子”,试图通过对他们的异域留学生涯及其结果的阐述,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一幅真实的历史图景。如果这本书有助于大家思考和理解今天中国人的文化处境,并且做出积极的反应,我的力气就算没有白费。
李兆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