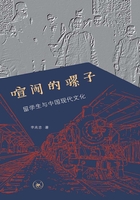
孤独的摩罗诗人
——寻访“原鲁迅”

1918年,中国文坛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狂人日记》诞生。
这是鲁迅出手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艺术上却是如此的精粹,令人惊叹。它取法于俄国作家果戈里的同名小说,却以忧愤深广的意境和炉火纯青的现代汉语,青出于蓝;西方的神韵,中国的气派,两者水乳交融,无迹可求。
按照法国批评家丹纳的艺术哲学之说,一座艺术高峰的周围,必有许多略低的次高峰簇拥,然而事情到了中国却有点例外,鲁迅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与其他的“第二”“第三”比起来,明显高出一大截。或许是上苍对中国的垂怜,像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不出一个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岂不太煞风景?
这一切当然不是空穴来风。鲁迅的特殊性在于:他艺术上的成功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结果,不像创造社诸公现炒现卖西方的新浪漫派,文名大振的同时,也留下许多遗憾;鲁迅是经过充分准备、漫长潜伏之后登上文坛的,丰沛的天才此时已磨砺得锋利无比,只等一声令下,便扬眉剑出鞘,摧枯拉朽,替中国的新文学开辟道路。
这一切都不能不追溯到鲁迅的留日生涯。日本著名汉学家伊藤虎丸在《鲁迅与日本人》一书中写道:第一次读到鲁迅留日时代的文章时,内心受到强烈冲击,原先认为那不过是一个中国留学生的习作而已,读后才发现:过去一直讨论的鲁迅的思想或小说主题,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找到原型,也就是说,一个“原鲁迅”已经存在。这个“原鲁迅”,无疑是留日七年刺激培养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以自己的方式认识了世界,发现了自我,诊断了中国的病脉,锁定了人生奋斗的目标,为十年后在中国文坛的崛起做了铺垫。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活。清末的东瀛,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与地理位置,成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小日本的压迫,列强的威胁,清政府的腐败,使留学生奔走呼号,无法安心于学问,鲁迅也不例外。然而,与其他人不同,鲁迅是以特立独行的方式加入救国行列的。
一提起鲁迅的留学生活,人们马上就会想起著名的“弃医从文”的故事,这个故事经过文学史家的反复演绎,已成为青年时代鲁迅的精神标志。鲁迅弃医从文的契机,是所谓“幻灯事件”,在《呐喊·自序》里鲁迅解释了过去仙台学医的背景之后,这样写道——
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从“鲁迅发生史”的角度看,“幻灯事件”意义非常重大,正是它,促使鲁迅弃医从文,如果没有这一专业的“转向”,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鲁迅,中国现代文学的版图将因此而大大地改观。仔细考量这件事,很有值得玩味的地方,因为“善于改变精神的”,并非只有“文艺”,教育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途径,比如留美时代的胡适就认为:树人之道,首在教育,并且希望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社会教育;而鲁迅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没提教育,说明鲁迅与“文艺”更有缘分。
值得一提的是,擅长保存文物、搜集资料滴水不漏的东瀛学者,至今尚未找到这些幻灯片,不得不使人对鲁迅的讲述产生疑问。日本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丸山升等人都认为,这些幻灯片实际上并不存在。然而,鲁迅讲述的“幻灯事件”是否属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否符合事物的真相。鲁迅显然没有凭空虚构,而是在事实的基础上做了一次合理的嫁接。鲁迅在仙台医专就学时,日俄两国的虎狼之师在中国的土地上正打得不可开交,大清帝国躲在一旁大气不出一口,作为战胜国的日本,那个勇于进取、以小搏大的日本,凭什么不蔑视中国?而身处东瀛狂热爱国氛围中的孤独中国学子,又怎么可能不受到刺激?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讲述此事时,已是归国十多年之后,十多年暗淡的人生经历,遭遇的一切挫折,写下的啼血文字,都在强化同一个意念:改造国民劣根性。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鲁迅再一次发挥自己的艺术本能,虚构一个“幻灯事件”,为自己的专业“转向”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不是很顺理成章的吗?
其实,对于鲁迅的弃医从文,本不应做太狭隘的理解,更不应将两者视为彼此孤立,或者非此即彼。事实上,医学与文学,或者说科学与文学,在鲁迅那儿始终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好比一个车轴上的两只轮子。鲁迅天性虽然更近文艺,对科学同样感兴趣,并且极为重视。鲁迅成长的时代,正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学说通过严复编译的《天演论》风靡中国知识界,给新一代学人带来空前震撼和希望之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先是进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又进南京矿路学堂读书,在那里接触了初步的自然科学知识,毕业后才有机会作为官派留学生到日本留学,鲁迅后来选择医学,仍然是沿着科学的路子。而且,即使鲁迅决定“弃医从文”,从仙台回到东京开始文学活动,对医学依然关注,这从鲁迅1906年的“拟购德文书目”购书单上列有大量医学书籍就可以得到证明。同样,即便从文学的角度考虑,医学对于鲁迅也有重要的意义,鲁迅自己就说过,他能够写出《狂人日记》,仰仗的是过去读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些医学上的知识。医学与文学最具互补性,一个着眼于人的身体,一个关注人的精神,唯其如此,作家中不少出自医生。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在鲁迅的医文互动中,“文”占据主导地位,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初到日本就读弘文学院时,就买了不少日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其中有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等。这一阶段鲁迅写了《斯巴达之魂》,翻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雨果的随笔《哀女》,其中慷慨激昂、洋洋数千言的《斯巴达之魂》,是应许寿裳接编《浙江潮》之约,一日之内挥就的,剑拔弩张的风格虽后来颇令鲁迅耳朵发热,却显露了他的丰沛的文学天赋。如此看来,鲁迅的“学文”是在“学医”之前,证明鲁迅天生嗜好文学。许寿裳这样描绘鲁迅的相貌:“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是一幅未来大文豪的真实肖像,这样的人不从事文学,岂不是天大的误会?
同样我们应该看到,鲁迅选择医学,背后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与一般人仅将医学当作谋生职业是很不一样的,正如作者在《呐喊·自序》中表白的那样,他学医的动机如下:第一,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中医耽误了的病人;第二,战时当军医救死扶伤;第三,有感于明治维新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然而据许寿裳透露,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宏愿:拯救中国女子的小脚,将所谓“三寸金莲”恢复到天足,后来经过实际人体解剖,发现已断的筋骨无法复原,只好断念。据多位留日同人回忆:鲁迅在仙台医专学习时曾解剖过尸体,男女老幼都有,最初动手时,颇有不安之感,尤其是对于年轻女子和婴儿的尸体,常产生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鼓起勇气不敢下刀;鲁迅还向他们描述过胎儿在母体中如何巧妙,矿工的肺如何墨黑,两亲花柳病的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等等。由此可见,鲁迅对待医学本身就带着极强的“文学性”。
鲁迅对待医学的这种高度的人文性、精神性和理想性,显示了他人格结构中道德超人的一面。从这个角度看,无论从医还是从文,对于鲁迅来说目标完全一致。其实,早在弘文学院时,鲁迅就注意到中国人的精神的问题,他与许寿裳经常讨论三个相关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他们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是诚和爱,换言之,是深中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历史上两次奴于异族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唯一的救济办法是革命。革命的方式固然有多种多样,然而对于鲁迅来说,最适合的莫过于文艺,《斯巴达之魂》正是这样的产物,它歌颂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强调的是“魂”。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书也起了重要的触发作用。此书于189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两年后日本就有译本(译为《支那人气质》)。作者根据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活经验,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了全面的批判揭露,误读与偏见之中不无中肯犀利的分析。鲁迅刚到日本时,此书正流行于日本的知识界,它与鲁迅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共鸣。
鲁迅最终选择了文学,表面上看,是“幻灯事件”刺激的结果,深层地看,则是文学家的天赋与超人气质的作用,证明理性意志终究敌不过天赋的本能。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时的一份考试分数单,完全证明了这一点:解剖59.3分,组织73.7分,生理63.3分,伦理83分,德文60分,物理60分,化学60分,各课成绩平平,唯独伦理一枝独秀,获83的高分,证明鲁迅超常的人文修养和文胜于理的智能结构。这也可以从另一件事得到证实:在上藤野先生的解剖课做笔记时,出于本能的爱好,鲁迅信手对下臂血管的位置做了大胆的移位,解剖图几乎成了美术图,后来受到藤野先生纠正时,他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藤野先生》)其实,那首《自题小像》(1903)早已暗示了鲁迅的这种精神价值取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辕轩。”气魄如此宏大,境界如此深邃,堪称千古绝唱,预示着鲁迅将以振聋发聩的文学之音承担医国的神圣使命。
1906年春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开始了另一种生活。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据朝夕相处的胞弟周作人的描述,鲁迅“过的全是潜伏的生活,没有什么活动可记”,博览群书,凝思默想,逛书店,收集书报杂志,翻译,写作,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这期间,鲁迅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吸收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精神成果,思接千载,神游万里,追本溯源,形成了自己对人类文明史,对东西方文化,对文艺的看法,在这个基础上开出了救世良方。
《人之历史》介绍西方科学界从古至今对“人”的认识成果,向人们展示了“人”的进化历史,表明鲁迅关注的焦点是“人”,而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科学史教篇》从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引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西方科学发达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人文演进的一个方面,科学不仅与人文难以割裂,而且它的发展有赖于人文的发达,因为“科学发见,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因此,作为一位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所以国人不可只求其枝叶,忘了根本;《文化偏至论》沿着这个思路阐发,认为科学发达的西方到了现代,文化上出现两种严重的“偏至”,一是重物质而轻精神,一是重“众数”而轻“个人”,对此,鲁迅针锋相对地提出“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主张,并将这种主张概括为“立人”。鲁迅认为欧美强盛,无不以物质和多数向世界炫耀,其实强盛的根本还是在于人,因此要在世界上生存,和各国竞争,“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的关键,首先在立人的“心”,即努力使人的“精神”变得深邃壮大,而要做到这一点,不能不依靠涵养“神思”的文学。而最能承担这一使命的,是那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的摩罗诗人,他们是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这些人无不志向远大,人格高迈,不畏强暴,骁勇善斗,秉有唤醒民众的神奇能量,即摩罗诗力,“摩罗”意即恶魔,上帝的死对头。在鲁迅看来,恶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恩人,所谓摩罗诗人,就是被正统保守社会视若洪水猛兽的精神界斗士;鲁迅推崇这批诗人,是有感于千年古国的萧条沉寂,求新声于异邦,希望打破死水一潭的僵局。在他眼里,上下几千年,纵横几千里的华夏,找不出一个西方那样的“摩罗诗人”,甚至连他十分喜爱的诗人屈原都不够格,因为他的诗篇“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鲁迅进而发出这样的追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贻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这些慷慨激昂之论,发自鲁迅内心深处,表明鲁迅决心追随西方“摩罗诗人”,做一名精神界的斗士,实现“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
确定了人生目标之后,鲁迅开始付诸行动,先是创办《新生》杂志,刊名取自但丁的《神曲》,又与弟弟周作人一起翻译介绍东欧各国被压迫民族的文学,印出《域外小说集》上下集,然而这些努力都未获成功。《新生》还没问世,资本已经逃走,撰稿人云散;《域外小说集》总共只卖出去二十本;甚至连呕心沥血著成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文,发表后也没有什么反响。这对鲁迅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如他后来哀叹的那样:“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
今天看来,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过分夸大了文学的作用,夸大了精神的作用。道德超人的气质,艺术家的气质,使鲁迅对“精神”格外重视,认定只有它才是根本,才是一切,因此对洋务派“竞言武事”,追求船坚炮利,对改良派热衷于“制造商估”“立宪国会”,都不屑一顾。然而,精神与物质、内容与形式本是一个互相制约的整体,精神的改良,离不开对形成这种精神的环境制度的改良,文艺固然重要,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同样不可缺少。这个道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不可能不明白,问题在于,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气质性格,鲁迅被社会的黑暗、历史的黑暗、人性的黑暗深深地攫获,不相信通过任何外在的手段能把中国改造好,唯其如此,他对维新志士提出的各种改良方案都不看好,而宁愿用“摩罗诗力”这一剂西方的猛药来唤醒国人麻痹的灵魂。因此,他对当时留日学生一窝蜂“学法政理化工业警察”,无人问津文学艺术很不以为然。一份保留至今的“拟购德文书目”(1906)清楚地显示了鲁迅当时的精神价值取向:上列的一百二十三种书目中,自然科学(以地质、生物、医学、人种为主)、人文科学(以文学、哲学、美术为主,其中文学史、文学作品占绝对多数)平分秋色,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事等社会科学的书几乎没有。从这份购书单中,可以看到鲁迅博大的知识结构中的某种不平衡,这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于事情的“内面”和“根本”,而对“外部”和“枝叶”则相对轻视。然而事实却是,鲁迅留日时代的作品精神内涵虽然超拔,却因文字的古奥晦涩无法普及于世,恰好证明“外部”“枝叶”也很重要。不过客观地看,这一次失败反而成全了鲁迅,使他大器晚成,潜伏十年之后,乘着新的历史机运再度出山,向黑暗发力,一鸣惊人,这回当然是用白话文,也就是鲁迅当年不曾在意的属于“枝叶”的白话文。
《呐喊》《彷徨》无疑是《摩罗诗力说》的延伸与形象的演绎,将两者互文地阅读,人们在发出会心微笑的同时,定会沉重地叹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无疑都是作者自己的化身,这些中国的摩罗诗人们,处境是如此的惨淡,他们不是疯掉,就是惨死,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立锥之地;洋溢在《摩罗诗力说》里的那份自信与豪情,此时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绝望,正如作者在《呐喊·自序》中沉痛表白的那样:“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番话实际上宣告了“摩罗诗力救国论”的破产,但这丝毫也无损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而且它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场伟大的破坏。
鲁迅在东瀛度过了整整七年的青春岁月,留下了洋洋大观的文字。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文字中,七年的留学生涯几乎是空白,作者目光所及是西方,思虑所在是中国,对眼皮底下的东瀛仿佛视而不见,甚至连“日本”两个字都看不到。归国之后,鲁迅也很少回忆那段生活,除了在少数几篇文章里略有涉及;写留日生活的只有《藤野先生》一篇,那也是在时隔二十年之后,并且有特殊的背景(当时鲁迅在厦门大学,正受“现代评论”派人士的压挤,心情郁闷,作了一系列怀旧文章,名为《朝花夕拾》,《藤野先生》是其中之一,结尾还特意点出:藤野先生是作者抨击“正人君子”的自勉力量)。一个人不怀旧,无非两种理由:一是往事不堪回首,另一是往事懒得回首,都证明着那段生活并不愉快。
确实,对于留日时代的鲁迅来说,日本只能是一个冷漠的、令人感到屈辱的存在,其中虽有藤野先生那样的有正义感的日本教授的亲切关怀,但这只不过像漫漫暗夜里的一支微烛,反而将黑暗衬托得更加清楚。关于这一点,“幻灯事件”已有形象的说明,然而比起“幻灯事件”来,“泄题事件”更具杀伤力。鲁迅的学医成绩并不出色,第一学年考试分数平均为65.5分,一百四十二人中排名第六十八,结果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疑心,以为藤野先生事先给他泄了考题,使他解剖学得了高分,于是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是查他的课堂笔记,使他饱受屈辱。关于这件事,二十年之后鲁迅这样写道:“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的疑惑。”(《藤野先生》)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了一年半,就不辞而别,连退学手续都是委托他人经办的。
然而,对于鲁迅这样的精神强者,小日本的歧视并不足以构成真正的伤害。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文化英雄,鲁迅不会为这类事耿耿于怀,事实上,对日本的岛国根性,鲁迅从未给过以牙还牙的抨击,这一点他与郭沫若很不一样;相反,他对日本的观察总是着眼于正面,结合鲁迅后来有关日本的零散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日本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新发户”,虽然没有卓越的伟人与独创的文明,却比僵化的破落户的中国更有生存的希望,在一篇文章中,鲁迅借厨川白村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这样写道:“著者呵责他本国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越的人物,这是的确的。他们的文化先取法于中国,后来便学了欧洲,人物不但没有孔,墨,连做和尚的也谁都比不过玄奘。兰学盛行之后,又不见有齐名林那,奈端,达尔文等辈的学者,但是,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上,他们是已经著了相当的功绩的,也许是著者因为正在针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杀。但总而言之,毕竟并无固有的文明和伟大的世界人物,……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象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新发户而生存,发达者更光彩。”(《出了象牙塔·后记》)第二,日本人有种打破砂锅问(璺)到底的、做事认真的气质,这种气质可以医治中国人的毛病。据日本友人回忆,鲁迅有一次同内山完造谈话时这样说:“中国的四亿人于今都害着病。这病叫作‘马马虎虎病’。这病如果治不好,中国是很难得救的,想找一找医这种病的药,却发现在日本人那里有,这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我们不妨排斥日本人,但必须买到这种药。”(内山完造《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临终前,鲁迅还留下这样的话:“我怀念日本。那些日本人有种打破砂锅问(璺)到底的气质。我是羡慕日本人这一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气质。不管什么,总是用怎么都可以来对付过去。不改掉这‘怎么都可以’,是无论如何不能革新中国的。”(岛崎藤村《鲁迅的话》)必须指出的是,鲁迅总结的这两点有特殊的语境,他对日本的肯定赞美并不是出于特别的喜爱,就像其弟周作人那样,而是另有一个令人绝望的参照——中国的存在。由此可见,日本在鲁迅笔下的空白,既不是出于通常的“大中华”对“小日本”的文化优越感,也不是由于狭隘的民族情感,而是鲁迅特殊的思维方式所然。确实,相对于鲁迅那样的博大深邃的胸怀,日本毕竟小了一点,也浅了一点,无法从根本上给中国提供充足的精神资源,这个国度里既不出尼采、叔本华这样的文化超人,也没有拜伦、雪莱那样的摩罗诗人,闻名于世的,只有那种接近“兽性爱国主义”的武士道、泯灭个性的集团性和礼仪烦琐的“人情美”,那些都是鲁迅不喜欢或者不感兴趣的东西。
日本鲁迅研究大家竹内好认为:鲁迅留学时代的文学运动与日本文学并无干系,这一点与后来的创造社形成鲜明的对照。周作人的叙述证实了这一点,据周作人介绍,留日时代的鲁迅对于日本文学殊不注意,对森鸥外、上田敏、二叶亭四迷诸人,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只有夏目漱石的讽刺小说《我是猫》《虞美人草》他比较爱读,对岛崎藤村的作品从不问津,自然主义文学盛行时只取田山花袋的《棉被》,佐藤红绿的《鸭》一读,但并不感兴趣。(《关于鲁迅之二》)这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一、鲁迅感兴趣的日本作家(前四位)都有留学西方的背景,关注的是他们的翻译评论而不是创作;二、鲁迅对那些本土趣味浓郁的日本作家没有什么兴趣;这证明鲁迅读日本文学,为的是了解西方文学,日本文学对于鲁迅充其量只有媒介的作用。
然而,这绝不意味日本文化对鲁迅无足轻重,事实恰好相反,七年的留日生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影响至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为鲁迅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的窗口、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和窗口,鲁迅了解了世界,发现了自我,形成了“立人”与“摩罗文学救国”的思路;第二,东瀛岛国的文化风土——那种非理性的悲情,对鲁迅的精神气质也有某种潜移默化之力。鲁迅本是一个理性丰沛的人,家道中落后饱尝世态炎凉所带来的心理创伤,给他的性格蒙上一层阴影,加上留日后受“弱国子民”的屈辱与岛国悲情的双重刺激,使精神天平倾向于非理性,形成了他特有的冷峻、深邃与虚无的思想风格;在此基础上鲁迅创造了自己的文学世界,遥遥领先于当时的中国文坛。然而,相对于鲁迅博大的胸怀与深邃的气质,东瀛岛国毕竟小了些,假如有机会到欧美留学,亲炙原汤原汁的西方文化,鲁迅定当有更大的收获。
中国现代留学史上,丁文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留学横跨东西,历时九年,其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充满变数,有心栽花的失落,与无意插柳的收获,相随相伴,让人领略到“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精彩。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创始人,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重镇之一;他被后人誉为“中国的赫胥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一位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与他早年的留学生涯是分不开的,那是丁文江的天赋与异域环境——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知识”与“情感”——积极互动的结果。他有一段著名的理论:情感完全由于天赋,而发展全靠环境,知识大半得之后天,而原动力仍在遗传,“情感譬如是长江大河的水,天性是江河源头,环境是江河的地形,情感随天性环境发展,正如江河从源头随地形下流,知识是利用水力的工作,防止水患的堤岸,根本讲起来也是离不开地形的”。那么,异域的“环境”和“地形”究竟给了丁文江什么样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