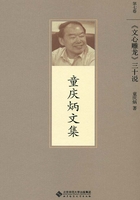
一、刘勰“意象”说溯源
中华古代文化中,早就有“意象”一词。根据安徽大学教授顾祖钊的考察,自古至今的“意象”可以分为五种: (1)在一般的“表意之象”或观念意象的意义上来使用,汉代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提出的意象观属于此种。(2)由于文艺心理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出现,心理学意义上的表象,也被翻译为“意象”,在心理学和文艺学两个学科都有学术意义,因此,应当承认心理意象存在的合理性。(3)刘勰提出的“内心意象”,是指艺术构思的结果和艺术传达前的“心象”,在创作学中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理应继承。(4)叶燮提出的“意象”是一种达到艺术“至境”的意象,这是一般“表意之象”的高级形态和理想形态,一种可以与意境概念并列的艺术至境形态,也应接受。(5)还有一种“泛化意象”,是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通称为“意象”。因为“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理论,一般称它为艺术形象或文学形象,为了减少理论术语的混乱,顾老师主张废除“泛化意象”,而代之以久已习惯的“艺术形象”或简称“形象”的称谓,这是对现代文论传统的尊重。显然,一个理论范畴的取舍应尊重历史和学术的科学性。[3]这些见解都是很有见地的,应该受到重视,并加以发扬。但是作者当时更重视的,是阐述王充的“表意”之象。
王充的“表意”之象是什么意思呢?有两段话是这样说的:
第一,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候,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
第二,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之庙……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
第一句话中的“熊麋之象”,是画在箭靶上的动物画像,而不同的动物画像,是不同的爵位的象征。据《仪礼·乡射礼》的记载,对于不同爵位的人,其箭靶的材料、质地和画像亦有不同的规定:“天子熊侯,白质;诸侯麋侯,赤质;大夫布侯,画以虎豹;士布侯,画以鹿豕。”显然,这种画像象征着等级森严的爵位。《礼记·射义》中说:“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大夫、士。”又云:“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故天子大射,谓之‘射侯’。”久而久之,箭靶也被称为“侯”,成了人们在乡射之礼上猎取爵位的对象。不同身份的人,只能射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侯”。“射侯”也成了“男子之事”和“饰之以礼乐”的特别隆重的、富有诗意的文化活动。王充这里重点说明的是:人们明明知道那些箭靶上的画像是假的,为什么还要“礼贵”它们呢?就是因为它们是“示意取名”的表意之象,由于已赋予这种“意象”以特殊的含义,因此它们就成了人们“礼贵”的对象。
为了说明“意象”的象征的原理,王充又举了一个更为常见的例子,即第二段话所说的“宗庙之‘主’”。宗庙中的“神主牌”,原来不过是一块一尺二寸高的木牌,由于上面写上了先祖的名字和神位,这样“立意于象”的缘故,所以,孝子虽知神主牌是假的,也在先祖的牌位前十分感动,这就是“意象”的特殊效果啊。看来,王充是有意突出他所创立的“意象”概念,才这样反复说明的。而且,王充提出的这种“意象”,明显具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脱离作者后而显现于人们眼前的一种艺术形象,不同于刘勰所说的作为艺术构思结果的,尚存在于作者胸中的内心之象。说它是艺术形象,一是因为它从属于“饰以礼乐”的古代诗性文化的一部分;二是因为它是人对动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把握和重塑,是一种绘画的结果。第二,它是一种“表意之象”,“立意于象”是它的塑造原理。它是为表达某种观点和意思而创造的形象,并为表达某种观点和意思(即义理)服务,所以,它应当是艺术形象的一个特殊类型。第三,它是采用象征手法塑造的形象,因此又可以称为“象征意象”。所谓象征,也是一种广义的比喻,它与一般比喻的区别是:比喻的喻矢与喻的同时出现,而象征里只有喻矢,喻的是什么,全靠人们去猜测。如“熊麋之象”究竟象征什么,是由特定的文化传统及其语境暗示的。由于王充提出的“意象”概念显示了这样三个特点,因此它更像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学术术语,不像《汉书·李广传》中的“意象”,出现得那样偶然和随意;同时与刘勰的“意象”概念也完全不同。[4]顾老师这些见解,把王充的“观念意象”解释得很清楚,正如他说的“与刘勰的‘意象’概念也完全不同。”在我看来,虽然王充的“意象”论也是针对艺术来说的,但它是作品实现了的意象,属于艺术形象中的“象征形象”,的确与刘勰《神思》篇中所提出的胸中并未在作品中实现的“意象”是有严格区别的,一个在作品中,一个停留在胸中,不可同日而语,要严格区别开来。因此,它不是刘勰胸中“意象”说的来源。
真正追溯起来,是《庄子》一书中的寓言,即《庄子·达生》所讲的一个故事:
梓庆削木为鐻。鐻成,见者惊犹鬼神。鲁侯见而问焉,曰:“子何术以为焉?”对曰:“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斋以静心。斋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斋五日,而不敢怀非誉巧拙;斋七日,辄然忘吾有四枝(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成见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5]
。
这故事的意思是:有位叫“庆”的木工,他用木料做成一种叫“鐻钟”的乐器。他的乐器做成之后,看见的人以为鬼斧神工,十分精美。鲁侯见了问他:“你是采用什么技术做成的呢?”木工庆回答说:“臣下是个工人,哪里会有什么技术呢?可是,有一点本人特别重视。我做这种乐器的时候,不敢耗费精神。斋戒三天,不敢怀着受赏而获爵禄的心思,斋戒五天,不敢想毁誉巧拙的评价,斋戒七天,不再想我有四肢形体。在此时,我忘记了朝廷,技巧专一而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然后,进入山林,遍观树木的质料,看到形态极合的,一个在胸中形成的鐻钟似乎宛然呈现在面前,然后采取木料,细细加工。这样以我的‘自然’来合树木的‘自然’,我的作品被大家疑为鬼斧神工,大概就是这样吧。”
这里“鐻钟”,已经被疑“惊犹鬼神”,当然是艺术品。但故事的重点是木工庆制作“鐻钟”的过程。这是一个艺术构思的过程。梓庆通过心斋,排除一切干扰,“以天合天”,“鐻钟”的意象先在胸中形成,达到了似乎见到“鐻钟”的样子,然后按照这种内心意象“鐻钟”的模式动手去做。这个故事完全可以概括为“胸有成鐻”。整个故事没有提到“意象”这个词,但“胸有成鐻”的思想显然蕴含其中。我觉得熟悉古典的刘勰,最初就是根据《庄子》的故事领悟到的,从而在《神思》篇提出胸中“意象”的理论。所以我认为刘勰的“意象”应追溯到《庄子》那里。这一理论看不出与王充的“意象”有什么特别的关联。
此外,从理论上给予刘勰启发的,可能就是《周易》的“卦象”理论,中国古代理论能够说清楚如何将思想感情表现在语言文章上的首推《周易》,《周易·系辞上》谈到卦象时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故谓之象。”所以《周易》要提出“立象以尽意”。这是最早的“象”论,属于哲学,并没有转到文学上面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王弼解释《周易》时曾说:“夫象者,出意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这就把言—象—意三者的关系关联起来,并予以清楚的说明。但这还是属于哲学方面的论述,并没有把它引入文学论上面。刘勰肯定对《周易》十分熟悉。对于王弼的理论更是印象深刻。所以他第一次真正地把“象”论引入文学理论,就是《神思》篇中的“窥意象而运斤”。这样这个在想象极致中出现于胸中的有情有景的意象,上接“情”,下接“言”,形成了情—象—言的完整的文学构思和表达的链条。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刘勰的“意象”还是心中构思过程,是形诸文辞的“意象”,当然,这个胸中“意象”,已经是主观的“意”与虚构的“象”的融合,与文本中的艺术形象有相似之处,但又不能把它与文本中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艺术形象等同起来。因为这一胸中“意象”,似乎可以窥见,但仍然是活动着的、变化着的、动荡着的,随时可以作出变更,还未形诸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