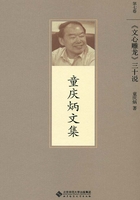
二、“窥意象而运斤”的基本意涵及其价值
接着,我们来考察刘勰《神思》篇的基本意涵和相关问题。《神思》篇中说:
……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枢机”(与下句的“关键”意思一致),指事物的关键。关键通了,事物面貌就显露出来。要是关键堵塞了,那么精神涣散,事物的面貌就藏匿起来。这都是过渡性的话,下文则是达到“窥意象而运斤”,或形成意象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要求主体的心灵纯净专一,不要受外物的干扰,达到“虚静”境界。刘勰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陶钧”原指瓦器或制瓦器的圆转器,这里引申为“酝酿”的意思,就是说酝酿文思,可贵的是作者的心灵要进入“虚静”状态,这里的“虚静”不是指空无所有,它相当于荀子所说的“虚壹而静”,即专注、入神、空明、纯净的状态。其实做任何事情都要这种状态,但进行文艺创作尤其需要这种“虚静”状态。这种进入“虚静”状态,按照刘勰的理解,需要“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疏瀹”“澡雪”最早见于《庄子·知北游》:“老聃曰:汝齐(斋)疏瀹,澡雪而精神”,“五藏”是说人体的心、肺、肝、脾、肾。中医典籍《灵枢·九针论》:“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精志也。”“疏瀹五藏”,即从生理上疏通五藏;“澡雪精神”,“澡”洗涤,“雪”,洁白,“澡雪精神”,即从人的精神上纯净自己,从生理到精神的世界,都要做到极度的无功利,排除一切“污秽”的思想,那么“虚静”状态就会出现。但是,“虚静”状态又不是人顷刻之间的心理的调整,是一个长期修养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做到四点:(1)“积学以储宝”,长期积累,丰厚学识。(2)“酌理以富才”,斟酌事理,丰富才能。(3)“研阅以穷照”,“研阅”是指从精神的角度钻研所阅历的生活,这样对生活才能有透彻的理解。(4)“驯致以绎(怿)辞”,“驯”,顺也;“致”,情致,思致;即顺着情致或思致而寻找文辞。有了以上四个条件,人的心就会深通玄妙的道理,就可调动声律文字来下笔了。此时,作者不要再东张西望,而是窥看着胸中出现的“意象”来运笔写文了。这才是创作中“御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即创作成功的关键。上述“积学以储宝”四条件的累积是“虚静”境界的原因,而“虚静”境界又是孕育胸中意象的原因,这里有着这种层层的因果关系,都是长期修养的结果。所以《神思》篇说:“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思契,不必劳情也。”因为是长期修养之功,不必临时费力,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刘勰所说的“窥意象而运斤”的基本意涵,是指艺术想象中的具有审美性的意象和意象体系在胸中涌动等待形诸笔墨的那种艺术形象的出现,而其关键在“虚静”境界的生成。
胸中“意象”这因果关系的生成,是一个长期修养的过程,是自然的过程,不是临时调动心理机能那刹那间的事。我反复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国“意象”生成的理论与西方的有关理论在文化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布洛所谓的“距离”说,似乎也是讲审美的瞬间,包括创作的瞬间,要排除外物的干扰,远离功利得失。布洛在《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说》一文中,曾以举例的形式来展开他的“心理距离”说的论述。他说,假设海上起了大雾,这对于坐在某艘客轮上赶路的人来说,都是一件极为伤脑筋的事情,除了怕延误行程之外,还有那可预料到的危险,如轮船触礁之类所引起的恐惧。船只的胡乱飘动,发出的警报,打乱了旅客的心神,焦急之情、紧张之感悠然产生,“一切都使得这场大雾变成了海上的大恐怖”。但布洛接着说,“海上的雾也能够成为浓郁的趣味和欢乐的源泉”,那就是把“注意力”转向“客观地”形成的周围的种种风物——“围绕着你的是那仿佛由半透明色的乳汁做成的看不透的帷幕(意象——引者),它使周围的一切轮廓模糊而变了形,形成一些奇形怪状的形象……”总之,大雾一时使周围美景如画,“有如强烈的亮光一闪而过,照得那些本来是最平常的、最熟悉的物体在人们的眼前突然变得光彩夺目”。他最后说,“这是一种看法上的差异,是由于距离从中作梗而造成的,这种距离就介于我们自身与我们感受之间”。他甚至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距离乃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6]实质上,布洛这里讲的距离,既不是时间的距离(过去很久的事),也不是空间的距离(人们此时就在轮船上),而是一种“心理距离”,更直白地说,就是“注意力”的临时转移。他提出的这个理论的实质也在“一开始就是由于使现象超脱了我们个人需要和目的的牵涉而造成的”,即摆脱了人们的功利要求而出现的。布洛的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没有根据的,怎么能在顷刻之间由于“注意力”的临时转移,就能把“大恐怖”变成观看美景呢?这完全不可能。试想,邻居的房子起火了,眼看也要烧到自己家,而此时你却能注意力临时转移,去“欣赏”那红色火焰鲜艳的美丽的跳动,而把危险放在一边,谁做得到呢?布洛的理论完全是离开人们实践的无根之谈,是不足为凭的。如果真有什么“心理距离”,那也是长期修炼的结果,绝不可能是临时注意力转变的产物。所以西方的所谓以摆脱功利目的为关键的“距离”,是不切实际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的以“虚静”境界达到的“意象”,与西方以注意力转移所看到的“意象”,是不一样的。这是文化的差异所致。中国古老文化讲究人的长期修养和锻炼,认为这样才能达到目标。刘勰说的“积学”、“藏器”、“蓄素”等,都有长期积累的意思。西方文化有讲究长期锻炼和实践的方面,但更常讲究临时性的心理调整,认为许多事情是瞬间的努力就可以达成的。对于中西方这种区别,我们必须有深刻的理解。
刘勰的胸中“意象”说,对于中国诗论、艺术论都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汉代和汉代以前的诗学,基本思想就是“诗言志”。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感物”而产生“情志”,然后“情志”以文辞表现出来。刘勰的《情采》篇,强调“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纬编织然后诗成,似乎不要其他东西了。这都是汉代关于诗学理论“感物吟志”的思想的另一种复制而已。所以历来谈到诗,都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些理论不能说不对,但可以说都不够完善。《神思》篇中的“窥意象而运斤”中的胸中“意象”,可以说真正地反映了诗歌创作的实际,“构象”论的加入,把“兴情”—“意象”—“言志”理解为创作的不可缺少的三阶段,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创作论。这样,钟嵘《诗品序》中的“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7]这些真实的说法,才有落脚点,离开这些意象,诗歌只是空洞地喊叫,这能说真的抒发感情吗?所以,从“感物言志”理论,发展为“感物”—“意象”—“言志”理论,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完整化过程,从此诗学发展进入坦途,这是极为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