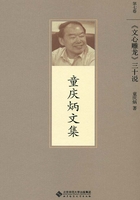
二、“体有六义”中的“体”
在中华古典文化语境中,“体”或“文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今人遇到“体”或“文体”,就把它理解成文章体裁,即所谓的“文类”。这种说法是以今律古,把文体概念简单化,因而是不恰当的。实际上,无论古今,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文体”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千万不可与体裁混为一谈。“五经”之重要,不但在于它讲了天、地、人及其关系,揭示了世界存在的规律,同时也提出了“为文”中运用和创造“体”的道理。
笔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文学文体,那时候可依凭的资料较少,主要依凭的就是魏晋以来曹丕、陆机、刘勰、挚虞等人的片段论述,此外还有几本《法语语体学》《英语语体学》等,研究不深入,但我经过数年的研究,撰写并出版了《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其中提出的对“文体”的界说是这样的:“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上述文体定义实际上可分为两层来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2]我的意思是把文体放在“体”的形成过程中来把握。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只把文体理解为“体裁”和“风格”,这种理解过于简单。体裁作为一种客观的语言结构样态,如何一下子会“跳”到具体个性特征的“风格”上面去呢?我当时就提出在体裁与风格之间,还要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语体”。所以我认为体裁→语体→风格,这是文体由浅层次升华到深层次的过程。文体是一个系统,写作需要体裁,一定的体裁需要使用一定的语体,某种语体在一个作家的笔下达到成熟或极致,这就是文体了。风格不是单纯的语言形式,它折射出人的个性、文化、历史、时代境况。那时,我很看重《文心雕龙·体性》篇,特别是《体性》篇中的“因内符外”的思想,认为文体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
1996年我到韩国一所大学讲学,在那里读到了台湾徐复观教授的《中国文学论集》,其中第一篇题目叫《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徐复观对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不满,对郭绍虞、刘大杰不满,如关于《原道》篇的“道”的解释,黄侃、范文澜把“道”解释为“自然”,徐复观认为这明显违背《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所传达出来的思想信息,是错误的。关于对《文心雕龙》文体的解释,郭绍虞、刘大杰仅仅把文体解释为风格问题,他也认为是错误的。他认为《文心雕龙》研究中有两个“死结”,一个是众多研究者在“道”的问题上跟着黄侃走;一个是研究文体论的作者在《文心雕龙》的体系问题、文体问题上都跟郭绍虞、刘大杰走。其后,我给研究生开设“文心雕龙研究”课程,也介绍过徐复观的观点。徐复观认为,《文心雕龙》“全书”实际上都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文体。他和我一样,不把文体简单地归为单一的“体裁”,他把文体问题放到文章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去考察,认为文体的内涵很丰富,认为中国古代的文体是指文章的“艺术性的形相”,它的要素包括三项:体裁→体要→体貌(又说有的文章没有体要),这是一个由低元次到高元次的“升华过程”。他认为文体是六朝时期文学自觉的标志,也是写作特别讲究的规则,但到了唐代古文运动之后,文体的观念日益趋向模糊,到了明代的《文章辨体序说》(吴纳)、《文体明辨序说》(徐师曾)等就又误把体裁当成是文体了。[3]这次拿起笔要写这篇文章,才从有关的资料中发现,在徐复观的上述文章发表不久,就有台湾学者龚鹏程发表同名文章。龚先生的文章只强调文体就是语言结构,是客观的规定,根本没有那些“体裁”、“体要”、“体貌”及其关系,严厉批评徐复观的观点全部错误。文章甚至说,“徐氏的论点根本错误”,“文字理解错了,观念理解错了,对《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结构和体系都理解错了,对六朝文论的整体掌握更是处处多谬。这样的研究,还不改弦更张吗”?(见台湾《中央日报》副刊十二月十一、十二、十三日)龚鹏程的意思是现代学者把刘勰的“文体”理解为体裁,是完全正确的;而徐复观把刘勰的“文体”理解为“三次元”
的文体是错误的。徐氏说文体非文类,龚氏说文体即文类。后又有台湾学者颜昆阳发表《论文心雕龙“辩证性的文体观念架构”——兼辨徐复观、龚鹏程〈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的长文,把《文心雕龙》文体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之后,大陆学者也加入了这场讨论,我所看到的有姚爱斌的《论徐复观〈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的学理缺失》、李建中的《龙学的困境——由“〈文心雕龙〉文体论”论争引发的方法论反思》。徐复观的文章的确有错误。如说文体的最基本的内容,即“艺术的形相性”;如说文体分成三方面的意义,呈“三次元”的升华系列:体裁→体要→体貌;如说因中国文学分成《诗经》和《楚辞》两个系统,所以有的(《诗经》系列)要求体要,而《楚辞》系列就不一定要体要;等等。这些说法的确无法从《文心雕龙》文本中寻找到根据,是徐复观自己编撰出来的说法,经不起推敲。看来,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问题的确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拙文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开始撰写的,可以说,此文是我研究《文心雕龙》文体观念的一个端绪而已。
那么,《宗经》篇的“体有六义”中的“体”是指什么呢?我们首先听听刘勰本人是怎样说的。刘勰在对“五经”的内容做了概括和评价之后,继续说: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论、说、辞、序四种体裁都从《周易》开始;诏、策、章、奏四种体裁,都发端于《尚书》,赋、颂、歌、赞四种体裁则由《诗经》那里开始的;铭、诔、箴、祝这四种体裁,都以《礼记》为发端,纪、传、铭、檄四种体裁都以《春秋》为根基;这些经书的内容都极为崇高,为文章树立了榜样,其涉及的范围也极为广阔,为文章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的疆域。这就是那个时期虽百家争鸣,写了各种文章,不管如何飞腾活跃,始终都不能超出经书的范围的原因。刘勰在这里列举了20种体裁,认为都是以“五经”为根基、为基础、为发端。我们为什么肯定刘勰这里所说的20种文章体式,就指文体中的体裁呢?这是因为他在这里只是把体裁的名称指出来,即刘勰《序志》篇“释名以章义”的“释名”,未涉及体之义、体之要、体之性、体之貌等。如下文讲到“体有六义”,这才关系到“体要”和“体貌”问题。又如《体性》篇说到“体性”,写道“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这“体性”也不是单纯的体裁问题了。
刘勰在写完上面所引的那章之后,紧接着就提出了我们所关切的论题。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
这段文章的意思是:如果能效法五经来写文章,那么学习文体的体要、体貌就是一个重要问题。“五经”文体中的体要、体貌有哪些呢?有六个含义:第一是要情感真实而不虚假;第二是风趣纯正而不杂乱;第三是事实可信而不荒诞;第四是义理正确而不歪曲;第五是体例精约而不繁杂;第六是文辞表现而不过分。扬雄用雕琢玉器作比喻,说明了“五经”含有文采。文章依靠德行来确立,德行依靠文章来流传。孔子用“文、行、忠、信”来教育学生,而把文放在第一位,正像德行与文采相互衬托,前后两者互相促进。后世的人学习德行,树立名声,没有不以圣人为师的,但在利用文辞写作的,就很少学习“五经”的写法。
这里的“体有六义”,一些研究者把“体”理解成文章[4],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文心雕龙》里面指称文章的词一般都用“文”而不用“体”,如引文中“文以行立,行以文传”,这里就直接把文章指称为“文”,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刘勰行文中一旦用“体”这个词,就可能指与文体有关的原则,如“体裁”、“体性”、“体貌”、“体势”、“体用”、“体要”、“体统”、“体义”、“体例”、“文体”等;或用作动词,如“体情”、“体貌”、“体物”等。刘勰的《宗经》篇,先说体裁20种,然后再说“体要”、“体貌”六个含义。我们怎么判定“体有六义”说的“体”就是“体要”和“体貌”呢?首先,从“文之枢纽”五篇看,《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所讲的“文原”,即是说文章从何而来的问题。《原道》篇有一句很重要:“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意思是,道依靠圣人的文章展示出来,而圣人展示文章则为了明道。在这里,从“道”到“文”有一个重要的中介环节,这就是圣人撰写的文章。所以刘勰在《原道》篇之后,安排了《征圣》篇,《征圣》篇亦讲了圣人的伟大,也大体上概括了圣人写文章的原则:“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用最概括的词语来说明圣人文章所达到的效果。圣人能全面观察日月天地自然,探究万物自然的生成和变化的玄机,所以文章能成为典范,思想与事实完全符合。他们的文章有时用简要的语言来表达意旨,有时又用繁复博大的言辞来表现感情;有时用直接的言辞来确立文章的体式,有时又用含蓄的意义来蕴藏功用。所以《春秋》一书用每一个字都很讲究分寸,蕴含褒贬。《礼记》中规定,根据孝者和死者的亲疏不同,而穿轻重不同的丧服。总的说,刘勰的这段话只是大体上概括了圣人文章的好处,至于圣人如何写文章?或圣人如何根据文体的哪些要义来写文章?则未能详述,他把这个任务留到《宗经》篇去论述。
其次,“体要”一词是在《征圣》篇提出来的,刘勰说:“《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词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词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这段话的意思是:《易·系辞下》讲,辨明各种事物,给出正确而适当的说明,使文辞有决断,词意也就完备充实。《尚书·毕命》篇讲,文辞应崇尚体要,不要一味追求奇异。所以。我们知道正确的言辞是为了明辨意义,体要则自然成为文辞。这样安排文辞,文辞也就不会有喜好奇异的不当之处,明辨意义也就会用果断的文辞来表现。文章的意义虽然曲折深隐,也不会伤害它的表现;文辞委婉隐约,也不会伤害文章的体要。这样,文章的体要与委婉的文辞可以统一,严肃的文辞与文章的精义也可以并行不悖。刘勰在这里四次提出了“体要”这个词,可见他对文章文体中的体要的重视程度,但他在这里只是论述了文辞与体要的关系,对于体要本身没有更多的说明,那么这重要的说明也就留到《宗经》篇的“体有六义”去解释了。《原道》《征圣》《宗经》三篇都在说明“文原”,因此说明问题有分工,《原道》篇说明“文原于道”,《征圣》篇说明“道沿圣以垂文”,《宗经》篇则最后落实到宗法经文。这三篇文章在展现“文之枢纽”上,一篇比一篇更具体,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序列,也说明了“体有六义”中的“体”,不是一般指文章,也不是单指体裁,还指体要和体貌,差不多是指整个的“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