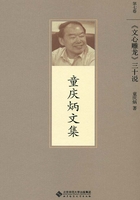
一、“宗经”是“为文之用心”的关键
刘勰《文心雕龙》把开始的五篇称为“文之枢纽”。实际上,“文之枢纽”又可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文原”,包括三篇,即《原道》《征圣》和《宗经》,力图论述文章的源头;第二个层面是“文变”,包括两篇,即《正纬》《辨骚》,力图说明文章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而第一个层面的逻辑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根本目的是追寻“为文之用心”,他指出“道”之所在,论证以圣人为师,最后都要落实到“为文之用心”上面。最能具体地体认“道”和学习圣人的路径就是宗法“五经”。所以《宗经》篇的重要意义从“为文之用心”的角度看,超越了《原道》和《征圣》两篇,它是“为文之用心”的关键所在。因此,《宗经》一开篇,刘勰就把“五经”抬得很高,说:“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把“经”说成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完全忽略文章随时而“变”的性质,似乎说明文“道”与文“教”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源头,这肯定是绝对化的。幸亏有后面的《正纬》和《辨骚》来说明文章的变化,对前文加以补充。开头八个字“三极彝训,其书言经”值得细细体味。所谓“三极”即“原道”篇的“三才”,“三才”即天、地和人,进一步说“道”延伸出了天文、地文和人文,是谁发现了这“道”,发现这“天道”、“地道”和“人文”呢?是圣人。圣人如何把他们发现和把握的“道”体现于“为文”中呢?这就要看他们所著的,或所编撰的“五经”——《易》《书》《礼》《诗》《春秋》了,因为“五经”是为文的榜样。
《宗经》对于“为文之用心”之所以重要,除了它体认了“道”,赞美了“圣”之外,重要的还在于“五经”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用《征圣》篇的话来说,是“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是“衔华而配实”。
《宗经》篇在总体评价了“五经”的价值后,点明了各书的性质、内容和特点。“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故哲人之骊渊也。”[1]刘勰认为,《易经》是专门谈论天地自然规律的,讲得精深微妙,可以应用于实际生活。所以《周易·系辞下》中说:意旨深远,文辞富有文采,事理讲得恰当和深奥。孔子读这部书的时候,三次翻断了系竹编的皮绳,它不能不说是哲人哲理深奥的宝藏。这是刘勰理解中的《易》。所谓“谈天”,就是揭示自然的秘密,所谓“致用”就是运用自然的规律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所以刘勰对《易》以“旨远辞文,言中事隐”加以评价,这是很恰当的。“《书》实记言,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刘勰认为《尚书》是记录言论的,只是它的字义的解释有难度,不易理解,但若能通习《尔雅》,它的意义就可了解了。子夏赞叹《尚书》,认为它论事明畅,就像日月那样明亮,内容清晰,就像星星那样有运行的轨迹。刘勰认为《尚书》虽然言论深奥,但若真的理解了,就像日月星辰那样明亮来照耀人们的生活。“《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这意思是,《诗经》是用来表达人的情志的,也很深奥,它分为“风”、“雅”等不同类型的诗篇,并运用“比”、“兴”不同的表现方法,文辞华美,比喻婉转曲折,诵读起来有温柔敦厚之感,所以它最能沟通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刘勰对《诗经》的理解,主要在《明诗》篇,这里只是刘勰对《诗经》大体的看法,风雅颂,赋比兴,温柔敦厚,表现人的内心的情感等这几个要点,都说到了。“《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缀片言,莫非宝也。”意思是说,《礼》是用来树立体统的,它根据事务来建立规范,章程条例非常周密,实行起来,功效显著,随意选用其中的只言片语,没有不是瑰宝的。春秋时期,以礼治国,礼是用来维系人的思想和社会秩序的,礼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刘勰对《礼记》给予如此高度的评价,也是可以理解的。“《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人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意思是说,《春秋》辨别是非,用一个字就显示出来了,这部书中记载,有五块陨石落到宋国,有六只鹢鸟退着飞越宋国都城,是以详细的文字构成文辞,又如雉门及两观发生火灾的记载,是以排列的先后来显出旨意。它的那种婉转曲折、含蓄隐蔽的写法,的确使它记载的事情包含着深刻的用意。《尚书》的行文看起来奇异深奥,但只要寻找出它的理路,那么还是明白晓畅的,《春秋》似乎反过来,文字表面好懂,但要探求它的含义,则又深奥难懂。这说明圣人文章的情致不同,文辞与内容也是不同的。这是刘勰对《春秋》的看法。刘勰分别五本经书,一一阐明了它们的内容和文辞特点,不仅如此,刘勰又认为“五经”又有共同的特点:“至根柢盘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意思是,“五经”就像那大树,根柢盘曲深厚,枝叶高大繁茂,文辞简约,意义丰赡,所举的事例浅近而寓意深远,真的是历久弥新,后辈的学者加以吸收不会晚,前辈的学者学习运用,也难以超越。“五经”开启的路径,就像那泰山的云气影响天下都下雨,河海的水让千里的土地都得到灌溉。刘勰这里所说,不但概括了“五经”的共同特点,而且也说明了它的体制影响到各类文体的产生,这就是最后“太山遍雨,河润千里”指涉的“文源五经”的意思了。
为什么刘勰对“五经”给出了这样高的评价呢?这可能与他的儒家思想有关。在他看来,第一,“五经”几乎是中华文明的开端,《易经》主要关系到自然规律的揭示,而《礼经》(和丧失的《乐经》)则是维系社会秩序的保障,《尚书》虽然是断简残篇,但其社会理论是端正人的意识的宝藏,《春秋》则是历史记载,历史是我们的根。刘勰可能认为,要是大家都学习“五经”,就像鼎有了三足,一足是了解自然,一足是认识社会,一足是增强人的修养。这样,人要是学习了“五经”,就会像鼎有三足一样稳稳地站在地上,成为君子,成为真正的人。第二,“五经”又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根据,其内涵深入人的心灵深处,其文辞又深刻地表达了义理,是为文的榜样。《宗经》开篇就说,“五经”“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有了这些合乎理想的篇章,就可以此为发端,开辟出新的文“体”(这里指体裁),如下文所说的论、说、辞、序、诏、策、章、奏、赋、颂、歌、赞、铭、诔、箴、祝、纪、传、铭、檄等等,不断地衍化下去,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刘勰的这种理解,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所谓“为文之用心”,首先要找到它的源头,在刘勰看来,这就是“五经”。就今天而言,许多人都在讲“国学”,其实“国学”的精髓就是“五经”,离开“五经”来谈“国学”,可以说是无根之论,尽管我们今天不必把“五经”看成一字不易的、观点绝对正确的著作,应有批判地吸收,有扬弃地接受。这段话不仅高度评价了“五经”,而且还为后文提出“文体”的问题做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