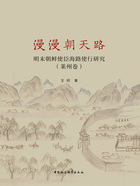
绪论
与明代大部分时间选择途经辽东的陆路路线不同,明初(洪武、建文年间,1369—1402)和明末(天启、崇祯年间,1621—1636),朝鲜使臣曾短暂地使用海路使行中国。虽然明初朝鲜使臣通过海路前往南京数十次,但仅有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少数使臣留下了使行记录。这些使行记录并不是记录使行沿途见闻或史实的纪行类文本,而是使臣感物寄兴的朝天诗。明末朝鲜使臣亦通过海路往返朝鲜与明朝。截至目前的研究,共有20余位明末朝鲜使臣留下了超过40种使行文献。明末使行文献中,除包含纪行诗外,还有采用日记体形式,记录使行沿途所经历的具体事件或见闻的纪行文,以及详细记录使行途经地相关情况的类方志体文章。此外,有的明末使行文献还收录了使行过程中使臣撰写的公文或书信。故明末使行文献更为详细地记述了朝鲜使臣开展使行活动的历史场域、同中国文人友好交流互动的情况、当时途经地的社会状况、风俗和风景名胜等多方面的内容。
明末海路使行路线具体指两条海路,即登州路线与觉华岛路线。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二年(1629),朝鲜使臣乘船从朝鲜半岛平安道西海岸出发,经朝鲜半岛西北、辽东半岛南部的诸海岛,在到达辽东半岛旅顺口后,折向东南,横渡渤海,经庙岛群岛,在登州港登陆,此即明末海路使行之登州路线。崇祯元年四月,颇受崇祯皇帝信任的袁崇焕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1]崇祯二年,袁崇焕担心椴岛东江镇都督毛文龙“居外,久必作乱”[2],罗列毛文龙十二条斩罪,将其处决。[3]同时,袁崇焕又担忧朝鲜与倭寇勾结并擅自通过登州海路进行贸易,因此奏请将登州路线改为(宁远卫)觉华岛路线。[4]相较于登州路线,觉华岛路线“水路之远,倍于登州,而且水浅舟大,常多致败”[5],伴随袁崇焕的失势,朝鲜“屡请复故”[6]。由于觉华岛路线凶险异常,崇祯三年八月,陈慰、奏请兼进贺使郑斗源(书状官李志贱)与冬至兼圣节使高用厚(书状官罗善素)在未经明朝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利用登州海路,到达登州。郑斗源和高用厚请求时任登莱巡抚的孙元化上疏朝廷允许将使行路线再次变更为登州路线。[7]接受朝鲜使臣请求的孙元化派遣护送官员陪同使臣前往北京,并上疏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以“水路既有成命,改途嫌于自便”[8]的理由,驳回了孙元化和朝鲜使臣的请求。此后至崇祯九年(1636)六月,即冬至、圣节兼千秋进贺使金堉(书状官李晚荣)使行明朝,朝鲜使臣只能通过凶险的觉华岛路线使行明朝。
本书仅选择朝鲜明末海路使行中的登州路线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其一,觉华岛路线并无太多可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考察的内容。朝鲜使臣利用觉华岛路线是直接从朝鲜半岛经海路到达北京附近的宁远卫觉华岛,未有较长的陆路行程。其二,登州路线途经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传承地——山东,明末使行文献可供解读的内容较为丰富。朝鲜使臣亦为朝鲜士大夫阶层的优秀代表,自幼对儒家文化耳濡目染。中国儒家经典、地理志书、正史典籍的东传,让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朝鲜使臣对中国历史人物、典故、名胜古迹等中华文化的优秀内核心生向往,使行沿途留下了数量众多的诗文和记述内容。基于此,本书选取明末海路使行文献中,记载进出登州港的有关文献为研究范围。但与本书的前篇《漫漫朝天路——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登州卷)》相比,本书的研究范围排除了个别使行文献。崇祯二年,进贺、谢恩兼辨诬[9]使李忔[10]在来程中使用觉华岛路线,在乘船归国途中,遭遇台风,前往登州以避风暴。在登州休整后,其一行自登州出发,经渤海返回朝鲜。因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仅较为简单地记录了船只到达和驶离登州的情况,并无本书研究范围——山东莱州府区间的相关记载,故将其排除在研究文本外。崇祯二年九月赍咨使崔有海原本计划前往觉华岛,与袁崇焕共商双方出兵征讨后金之事。在来程途中,崔有海一行遭遇台风,不得已之下,前往登州避风。在到达登州后,又因袁崇焕失势,崔有海的使行任务落空。在登州等待一段时间后,崔有海自登州乘船归国,故本书亦将崔有海之《东槎录》排除在研究文本外。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较前篇《漫漫朝天路——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研究(登州卷)》,本书将崔应虚的《朝天日记》纳入研究文本范围,这应是该《朝天日记》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天启元年谢恩、冬至兼圣节使臣团书状官安璥的《驾海朝天录》为明末海路使行文献之嚆矢。但伴随与安璥同行的使臣团正使崔应虚[11]《朝天日记》的发现,或许现在应将《驾海朝天录》与《朝天日记》一并看成最初的明末海路使行文献。2018年,韩国文化遗产厅下属的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对韩国忠清南道、忠清北道、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庆尚南道、庆尚北道等地存世的“朝鲜时期(文人)个人日记”进行调查。在此次调查中,共发现相关文献172件。同年,国立文化遗产研究所出版了影印版《朝鲜时期个人日记》第四卷,崔应虚《朝天日记》便因收录于此卷中,而被世人所知。《朝天日记》的重见天日对于明末海路使行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天启元年(朝鲜光海君十三年,1621),为感谢明朝派遣登极诏使,告知朝鲜明光宗即皇帝位一事,朝鲜派遣谢恩使臣团出使明朝。据崔应虚《朝天日记》记载,[12]天启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谢恩使臣团正使李庆涵[13]、副使崔应虚、书状官安璥一行在朝鲜慕华馆举行“拜表”仪式后,自朝鲜都城汉阳(亦称汉城,今韩国首尔)出发。四月十二日,在朝鲜平安道博川(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郡),李庆涵以“年老不可由水路而行”[14]为由,未能以正使身份使行明朝。此后,崔应虚“以副使,擢刑曹判书为上使”[15],即以正使身份出使明朝。此外,《朝鲜王朝实录》中亦有“谢恩使崔应虚状启曰”[16]的记载。这说明因原定正使李庆涵因各种原因,[17]未能乘船使行明朝,而原副使崔应虚作为正使出使明朝。
崔应虚的《朝天日记》采用日记体,记录了天启元年九个月的使行活动。崔应虚一行,在天启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离开朝鲜都城汉阳。五月二十日,崔应虚一行在安州(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市)乘船,与明朝登极诏使刘鸿训等人一同出发。六月十九日,崔应虚一行到达登州。十月九日,在完成使行任务后,崔应虚一行乘船从登州乘船归国,十一月五日,达到朝鲜平安道铁山(今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二十一日到达始发地。《朝天日记》记载了使行期间的每日天气、途经地、留宿场所、具体的使行活动等内容。与《驾海朝天录》相似,《朝天日记》虽然亦是纪行文,但记述较为简略,且并未收录崔应虚所作的纪行诗。韩国忠清南道青阳郡木面松岩里慕德祠[18]收藏有手抄本的《朝天日记》,为存世孤本。《朝天日记》共96页,每页10列,每列20个字。第1页至第85页为使行记录,剩余部分为六世孙所写的崔应虚家状[19]等文献。
本书以18位朝鲜使臣的28种使行文献(包括《航海朝天图》等使行绘图)为直接研究对象,制作了表0-1《明末海路(登州路线)使行文献及版本目录》。本书拟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出发,综合文献考证与田野调查,采访当地居民或地方史志研究专家,确定明末朝鲜使臣的使行途经地名,考证相关地名的沿革,结合使行文献(纪行文、纪行诗)对沿途名胜、朝鲜使臣同中国文人或当地居民的交流与互动等的记述分析,重构朝鲜使臣视域中的中国文化空间。
为达成上述研究目的,本书综合采用如下研究方法。第一,以表0-1中的文献为范围,明确使行文献中有关明末莱州府境域的内容,并提取相关地名或地理标识名称。通过此步骤虽然可以初步确定朝鲜使臣在莱州府境内的大致路线,但因主客观原因,会出现不同的使行文献对同一途经地名不同记载的情况,抑或是某段路程中,使臣短暂停留在不同地点等情况。第二,将使行文献中记述的途经地名比对各地的古、现代方志以及韩国古代史料(如《通文馆志》等)中的相关记载,考证各途经地的沿革。虽然通过此步骤可以更为准确地还原使行路线,但是无法确定使行文献中提及的地名或地理标识名称的情况亦不在少数。第三,通过实地考察,详细了解途经地的地理现状,考察朝鲜使臣提及的历史古迹和自然风景,采访当地的文史研究人员及居民,并据此确定文献中存疑的内容,补充文献中缺失的内容,还原并重构朝鲜使臣的使行路线。并以此为依据,制作表8-1《明末朝鲜使臣海路使行莱州府境内途经地名变化》。第四,按照使行文献记载的经由地顺序,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依次分析朝鲜使臣留下的相关记述(诗文、纪行文本、绘画等),把握明末朝鲜使臣与中国文人的诗歌唱和等文化交流情况,探究朝鲜使臣的内心世界以及对中国社会或中国文化的认知。
表0-1 明末海路(登州路线)使行文献及版本目录

续表

续表

续表

[1] 参见《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28页a。
[2] 《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0,仁祖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本书中《朝鲜王朝实录》的相关记载参照韩国国史委员会构建的“《朝鲜王朝实录》DB”(http://sillok.history.go.kr)。
[3] 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0,仁祖七年六月三十日;《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焕》,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35页。
[4] 参见《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0,仁祖七年闰四月二十一日;《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元月二十七日;《明史》卷320《外国传一》,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30页b。崇祯二年二月,明朝向当时停留在北京的冬至兼圣节使宋克仁下达了使行路线变更诏令。
[5] 《朝鲜王朝实录·仁祖实录》卷22,仁祖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6] 《明史》卷320《外国传一》,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30页b。
[7] 参见[朝鲜]韩致奫《海东绎史》卷36《交聘志·朝贡四》,朝鲜古书刊行会明治四十四年刊本;《明史》卷320《外国传一》,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30页b。
[8] 《明史》卷320《外国传一》,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第30页b。对重改贡道,朝鲜似未放弃,《海东绎史》中亦有“至崇祯五年壬申,奏请再从登州路”的记载。
[9] “辨诬使”通“辩诬使”,据《朝鲜王朝实录》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朝鲜官方记载皆为“辨诬使”,为还原史实,本书亦使用“辨诬”及“辨诬使”二词。
[10] 因积劳成疾,使行过程中病逝于北京。李忔《雪汀先生朝天日记》中自北京返程部分为其随行官员续写。
[11] 崔应虚(1572—1636),字拱辰,庆州(今韩国庆尚北道庆州市)人,1603年及第,历任礼曹左郎、兵曹左郎、京畿道使、司宪府掌令、承政院承知、水原副使等职。本书中朝鲜使臣及相关朝鲜人物信息参见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自建的“韩国历代人物综合信息系统( )”数据库。数据库网址:http://people.aks.ac.kr/index.aks。
)”数据库。数据库网址:http://people.aks.ac.kr/index.aks。
[12] 参见[朝鲜]崔应虚《朝天日记》,韩国忠清南道青阳郡慕德祠藏本。
[13] 李庆涵(1553—1627),字养源,号晚沙,韩山(今韩国忠清南道舒川郡)人。1585年,式年(三年一次)文科及第。1593年,历任正言、持平、世子侍讲院弼善。1594年,任掌令(隶属司宪府,正四品)一职。1603年起,历任星州牧使、光州牧使、户曹参判、庆尚道观察使。因反对文臣李恒福废母之事,被贬归乡。1623年,任汉城府右尹。
[14] [朝鲜]崔应虚:《朝天日记》,韩国忠清南道青阳郡慕德祠藏本,第6页b。
[15] [朝鲜]崔应虚:《朝天日记》,韩国忠清南道青阳郡慕德祠藏本,第47页b。
[16] 《朝鲜王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6,光海君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17] 因明末海路是在明初海路间断两百余年后重新使用,航海安全难以保障。且因渤海,特别是辽东半岛至庙岛群岛间,海洋深度较大,多台风,气候条件恶劣,海路使行吉凶难测,故彼时朝鲜文臣“皆规避,多行赂得免”。李庆涵具体因何未能成行,因缺乏相关史料记载,无法进行较为可信的考证。
[18] 慕德祠是1914年为纪念朝鲜时期的学者、义兵将领崔益铉(1833—1907)的抗日斗争及抗争精神而设立的祠堂。祠堂内有影堂、古宅、中华堂、藏书阁、春秋阁、文物展示馆等建筑。崔益铉,字赞谦,号勉庵,抱川(今韩国京畿道抱川市)人。九岁起先后师从金琦铉、李恒老等朝鲜末期知名学者,学习性理学。1855年,科举及第。历任承文院副正字、司宪府持平、司谏院正言、新昌县监、成均馆直讲、司宪府掌令、敦宁府道政、承政院同副承旨、户曹参判、户曹判书、京畿道观察使等职。1906年,面对日本的入侵,崔益铉以七十四岁的高龄组织义兵英勇反抗。
[19] 古时指记述有关个人履历、三代、乡贯、年貌等的表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