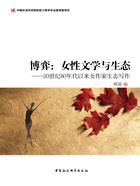
一 现代性置女性于反思与批判处境
在上述背景下,女作家从女性视角与生态文明高度来反思与批判现代性文化,也重新反思原始生态文明。迈克尔·伍德在《沉默之子》中对当代小说的看法是:“小说成了一种忧伤但慷慨的模式:关于丧失它教给了我们许多。”女作家将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境地,从根本上思索女性精神旨归的问题,继续80年代的女性生存处境的思考,但显然又有本质的差异。新世纪的女性,开始回归传统,结果是一些女性能够找回,一些却在迷失。表现在写作上,一些女作家固守着原来的守望与徘徊,一些女作家则竭尽所能在本土化路向上发掘传统文化、民间文化与宗教思想,从中汲取有效养分,以生态写作实践呼应着西方生态理论,呈现为女性生态书写的多重可能性与写作限度的并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张洁、铁凝、王安忆、张抗抗、迟子建等,就在勘探着女性写作的新路径;而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竹林的《生活之路》,遇罗锦的《冬天的童话》,乔雪竹的《郝依拉宝格达山的传说》《北国红豆也相思》等,却以历史的偶然,撞击到了生态书写,传达出对乡土生活的眷恋。曹文轩在《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中曾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出现了1919年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自然崇拜。”而90年代乃至新世纪,涌现出了诸如素素、白玉芳(满族)、空特乐(鄂伦春族)、萨娜(达斡尔族)、梅卓(藏族)、叶广芩(满族)等女作家,生态书写越来越成为众多女作家的尝试,以自己的方式在誊写着有关女性生态的故事。
一些生态文本带给我们以一种清新,一种视野,一种智慧,一种忧伤。
张抗抗的中篇小说《沙暴》是较早从人与动物的生态关系来进行动物叙事的。故事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到内蒙古草原插队时大肆捕猎老鹰,结果导致老鼠猖獗成灾,毁了整个大草原。到了1980年,在市场利益的诱惑下,他们中又有人到草原上去猎鹰,最终导致沙化严重,给北京带来了严重的沙尘暴。方敏的三部中篇小说《大迁徙》《大拼搏》《大毁灭》展示了红蟹、褐马鸡、旅鼠等卑微弱小生命的自在状态。《大迁徙》写的是印度洋的一个蟹岛上,有成万上亿的小红蟹,每到雨季就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来一次大迁徙。《大拼搏》写的是濒临灭绝的褐马鸡,为了生存与各种自然灾害和天敌顽强拼搏的悲壮故事。《大毁灭》则写北极圈中的旅鼠由于繁殖力极强,在短短的几十天中,即能由六只繁衍到一万只,因而无法觅食生存,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们便只能成亿成亿地集体朝向大海,走向死亡。而她的长篇小说《大绝唱》,讲述了生存在天山脚下的九曲河湾河狸的种群,过着自在的生活,但是男人长腿和女人胖子带着他们的一个女儿和儿子,找到了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接着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使得河狸丧失了较好的栖息地,并在最后遭受到生命的屠戮。还有方敏的《熊猫史诗》,唐敏的《心中的鹰》,叶广芩的小说《老虎大福》叙写一个地区的某一个物种被人类灭绝的悲剧。叶广芩在《黑鱼千岁》中,讲述了人与自然对抗的故事,显示了人在自然面前的无力。蒋子丹从先锋的荒诞到写实的动物书写,以《动物档案》和《一只蚂蚁领着我走》逼近自然与人类纠葛,围绕人与动物的关系展开的有关人类社会生态文明、动物伦理等问题的深入思考,明显具有社会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的学术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女作家的书写由物及人,由自然及社会,由生命及精神。黄蓓佳《所有的》,横跨几个大的历史时段——“文革”、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及当下经济大潮,作家在一个大的时间跨度上对女性生命状态与人性本质进行双重解读,有关爱情、权利、生命禁忌等也都在作家考察范围之内,将圣洁的生命理想带到凡尘,以智慧之光投射世俗人生,获得生命沉落的缘由,并试图予以拯救。素素散文集《独语东北》以大气磅礴的气势去寻觅属于原乡记忆中的东北沃土上曾经有过的历史痕迹与脉动,开始了具有原始真味的寻找,从都市向乡野推进,从历史到现实,对东北多民族生息迁移与文化精神理性进行了有意味的追索。
应该说,女性写作并不乏可供生态批评审视的作品,女作家从生态学视角,而不只是拘泥生态学科领域的理论视角,立足本土,秉承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文化精髓,突破本土的视野走向世界。反思人类与自然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的信仰、伦理和审美生存的诗学特征,最终建构人、人类文化与自然、自然环境和谐关系的新人文精神,最终目的是探寻和揭示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与文化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