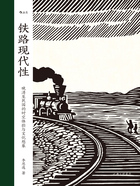
导论
以铁路为方法,言说现代性
人体器官往往根据人们对它们扩大或缩小的需要,或萎缩,或增强。自从有了铁路之后,免误火车的必要性使我们学会了重视每一分钟,而在古罗马时代,不仅天文知识粗浅,而且生活也不那么紧张,人们不仅没有分钟的概念,甚至连固定的小时的概念也不明确。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4:索多姆和戈摩尔》
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
——老舍,《断魂枪》
不得人心的火车,就此不分昼夜地骚扰这个小镇,火车自管来了,自管去了,吼呀,叫呀,敲打呀,强逼着人认命地习惯它。
——朱西甯,《铁浆》
吴淞铁路全长14.5千米,是中国第一条营业性铁路。其上海至江湾段于1876年6月30日正式通车,吴淞铁路有限公司于翌日邀请当地华人免费试坐,并于《申报》上刊登了中国第一份铁路时刻表。由于铁路的铺设一开始是英商以投机、欺瞒的手法悄悄进行,不仅有违中英双方合约,更直接挑战了当时清政府拒绝发展铁路的立场。时任上海道台的冯焌光感到受骗后反应十分激烈,在谈判时态度强硬、寸步不让,直斥英方违背万国公法,是“违我朝廷素愿,而明欺我朝廷也”[1]。他甚至发出极端言论,称若火车开行,自己将卧于铁轨之中任车轧死,让英使威妥玛、梅辉立等人深感不可理喻,视为疯人。[2]最终经过多方干预和反复交涉,吴淞铁路通车运行十六个月后被清政府以二十八万五千两白银买回,后由两江总督沈葆桢下令拆除、废置。
需要指出的是,冯焌光、沈葆桢等人并非愚昧无知、反对现代科技与文明的庸人,相反,他们都对铁路能给中国带来的效益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反对铁路的理由,除了外国修建侵害主权外,更多是基于一种我们已感陌生的认识论:为什么要那么快呢?有效益我们就一定要去争取吗?况且,铁路带来的垄断性收益最终都是归于政府,机器技术夺走了贩夫走卒赖以生存的饭碗,国家与民争利,有什么光彩可言呢?有钱不赚,难怪会被洋人当作傻子和疯子。我们当然可以基于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视角,悲叹晚清知识分子腐朽的道德观阻碍了中国的富强之路。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当前的后移民研究,盛赞圣雄甘地对纺织机器的拒斥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而随着经济崛起,中国政府反过来向欧美国家推销高铁时,那些来自发达地区人们的疑虑仍和冯焌光们保持了几乎一致的论调:我们现在的生活难道不好吗?有必要那么快吗?那些被高铁影响的底层民众、破坏的环境该怎么弥补呢?
长期以来,铁路、火车作为现代技术文明最耀眼的产物,自然也就被我们当作现代性的象征。但吴淞铁路的故事却告诉我们,铁路与现代性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铁路并非一开始就被所有人都当作进步,且带有必然性的历史取向——这是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另一方面,曾经看似愚昧、落后的反铁路姿态,在语境变换之后倒有可能成为更加“现代”的反思资源。
本书的出发点源于我个人长期浸染文化研究所形成的一种偏见:一切看似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东西都是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逐步形成,伴随着各种细节的想象性建构。不论是铁路还是现代性,我们都没有自以为的那样了解它们。如果铁路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技术产物,那么一切与之有关的文学书写、文化产品乃至心智与经验是否都要被统摄于这些宏大术语之下?如果铁路现代性仅仅是一种建构的话语与意识形态,我们又该如何处理现代性之中真实而切身的物质对象,以及时空中的身体经验呢?“铁路”和“现代性”二者之间除了直接的映射关系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形式的关联与互动?铁路为现代性提供的叙述空间、修辞手法、建构过程在中西语境中存在哪些异同之处?随着对这些问题思考的逐渐深入,我意识到铁路不仅是现代性的产物或象征,更可以是言说现代性的一种思路和方法。不过在展开具体论证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参考一下当前的铁路研究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