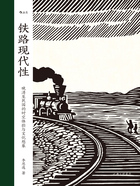
从“火车/火轮车”到“‘火’车”
铁路和火车均是中国语境中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可它们的名称却有着不同的待遇。相较于作为德语借译词的“铁路”,马西尼将“火车/火轮车”视作本土自生的新词,仅仅是因为没有在作为参照系的西方语言中找到相似的对应。跨语际翻译实践试图将语言论述、知识概念还原为历史事件,将翻译过程处理为制造对等关系的喻说以此来消解中/西、传统/现代的对立,可它的言说工具——比如物的语言指称,本身就立足于对不同等级秩序的默许基础上。语言符号与现实世界之分离,使得意义与指称、语言与对象的关系成了比存在、主体等更为基本的哲学问题,“漂浮的能指”建立起自成体系的王国。可研究者所处的位置,又令我们不得不尽力嵌合两个不同的世界:不论是努力返回历史现场还是在思辨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都是为了让我们关于语言符号的研究与现实世界重新关联,继而产生意义。事实上,语言概念从来不只是符号层面的问题,也不只是符号背后历史结构、意识形态的运作;它直接感受着经验的变迁,与具体的物与技术打着交道。要想明白“火车”这一语言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诞生确立,不是要将焦点放在人们对于相关技术原理的认识发展,而是要去参考火车衍生出的各种意象,以及它们如何嵌入日常经验之中。
马西尼对于“火车”一词的探讨依据的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又称高理文)于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其将“火车”一词解释为“唯以火力旋轮”。[19]根据该书第一次印刷版本《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记载:“其外更有火车,不用马匹,内以火力旋绕,日可行千余里。”[20]不论是“以火力旋轮”还是“内以火力旋绕”,都是从火车运行的动力原因方面加以解释,“火力”很难说属于科学知识性的范畴,更像是混杂了外来技术和新经验而融入了晚清帝国关于现代之物的想象中。同样,林则徐将火车称为“火烟车”,并不是缘于火车烟囱排出的烟气这一形象,而是其意识到火车运行是“均用火烟激机运动,不资人力”[21],所以这里的“火烟”其实指的是“蒸汽”。郭实腊在《贸易通志》中提出:“天地间空中运动流转之物,唯风水火三者,今风力水利皆无可恃,唯有火力可借 。”为什么不能用火轮以代风轮、水轮呢?“于是以火蒸水”,凭借“炎热郁蒸之气”,“施之以轮,不使自转”。[22]遂用火轮机之法,造火轮船、火轮车。丁拱辰在1843年刊行的《西洋火轮车火轮船图说》中也是强调这种机器“俱不假人力,唯用水火牛马运转”;而火轮车和火轮船“其形虽异,其机则一”。[23]徐继畬也是如此梳理了从火轮机的发明到火轮船再到火轮车的这一先后递进顺序。[24]王韬在1890年刊行的《漫游随录》中记载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赴欧所见,介绍了他所理解的西方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等“实学”。在他的分类体系中,火车和“火学”“气学”都没什么关系——前者研究“金木之类何以生火、灭火”,后者考察“各气之轻重”;反而是由“化学、重学”而“知水火之力,因而创火机,制轮船火车,以省人力,日行千里”。[25]所以是由“火力”而有了“火机”,最终创造出“火车”。由此可见,“火车/火轮车”的“火”与“轮”本应该是指通过烧煤生火产生蒸汽动能的蒸汽机。但晚清中国人却是用“火力”“火轮”来解释火车轮船的运行,故有学者认为这是出于他们对蒸汽原理的误解,以致无法想象何以蒸汽能够产生如此的能量。[26]而用与风轮、水轮并举的火轮指代蒸汽机,也体现了一种对传统中国认识论中风水火的附会。晚清的格物/格致之学,不同于日后单一、普遍西化的“现代科学”,其本身就是在传统文化资源、中国既有哲学认识论层面与西方的、新进的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学说之间的互认与摸索,从而形成一种不中不西,既非传统也不现代,同时混杂多元的知识分类体系。[27]也有学者认为晚清的格致之学本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非西方”的现代科学,却因为战争、政治的原因,无法承载起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之中国的建立,使得自身现代身份被全盘否定,最终“现代化”变成了纯粹的“西化”。[28]在这里,我并不想评判格致和科学孰优孰劣,也不想探讨格致是否有成为一种另类科学的可能。令人感兴趣的是,格致学的混杂与多元、糅合传统本体论想象与西方科学技术的知识,恰恰印证了晚清帝国关于现代性经验的复杂与异质。我们同样应注意到,即使不同于科学建制体系,作为一种知识话语的格致学其内部也存在权力层级和盛衰轮替,比如以火力、火轮为重心的火学之淡出。可能是意识到用火力、火轮形容蒸汽机的运转不够准确,在丁韪良《格物入门》所区分的水、气、火、电、力、化、算七大学类中,有关火轮机、火轮船、火轮车的部分是放在“气学”下面,而“火学”研究的则是冷热、光学一类的问题。其在“卷二气学”一章中着重强调所谓火力是以“蒸汽转运火轮”,火轮因“蒸汽之稠稀”而有高度机、低度机之分,“嘉庆五年间,有人始造气机轮车,遂用火力以代马”。[29]傅兰雅编撰的《格致汇编》也刊登了《气机要说》和《气机命名说》等文章,前者采用“气之力”“气机”代替“火力”“火轮机”;后者则直接解释,当初轮船初进中国时,“见者因内燃以火、外转以轮,即呼曰火轮船。其机沿曰火轮机”。“今按此器,乃以水气运机,当名曰汽机轮船,或省曰汽机船,再省曰轮船。机则名曰水气机,省曰气机。”[30]薛福成为1890年出版的《格致汇编》所作的序言中,已然不见“火学”的踪影,只剩下重学、化学、气学、光学、电学、几何学六大类,其中“气学”即是“以火化水,使积力而生动者”。[31]
可见格致学知识体系内部确实呈现出一股以气代火的趋势,气学成了更为规范准确描述火轮车运作原理的话语。如果说这一变化体现了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由误解走向正确,那么按照先前研究者的普遍设想,相应的翻译术语、事物命名也应该有所体现——至少变得更为准确。可如今火轮机、火轮船的叫法都已成为过去,为何火车仍然是叫“火车”呢?阿梅龙(Iwo Amelung)有关晚清中国人对西方力学的接纳之研究或许能为我们带来些启发。他关注翻译西方力学(Mechanics)的术语概念如何从“重学”演变为“力学”的过程,强调像“重学”(与“火学”类似)这些晚清的科普词汇虽然自身缺乏必要的科学性基础,却为将来新知识体系的确立铺平了道路。更重要的是,他指出:“19世纪传入中国的‘重的研究’和‘力的研究’事实上与西方科学中的力学并不完全相同。力学的抽象概念和名称都被具体化了,它们都被视为有具体内容的名词,这就导致了其原初内容的压缩或扩展。”[32]换句话说,我们不应将它们当作同一事物、同一知识的移植与复制,而是在中西不同的语境中有着各异的聚合方式。像“火轮”“火学”这些词,虽然缺乏所谓的科学内涵,也逐渐被知识话语体系淘汰,却对于现代之物的命名有着强烈的影响。此外,就像现代科学技术与日常生活经验存在隔阂一样,我们也不能纯粹用格致学的分类变化印证晚清中国人对火车、火轮、火的认识与理解。况且考虑到格致学的实际接受情况,像《格致汇编》的发行量最高也只有两千左右的读者。[33]如前所述,物的原理、技术知识与身体作为人与物的经验中介总是呈现出一种分裂,事物的本质(如果有)处在其所传递的信息之外。换句话说,物向人显现的意象总是优先于人对物的认识理解。接触火车的晚清人士,不乏有人也许并不在意“火轮”(蒸汽机)与车轮的区分;也许对火车带来的新奇、震惊甚至创伤性的“火”之感受,要远胜于格致学试图普及的火力、蒸汽;也许对“火车”的接受只是出于习惯后的泰然任之,并不必然关乎自身知识水平的提高以及集体文明程度的增长。
比如《格物入门》中回答“物之下坠生热,何以验之”的问题,就举例为“火轮车陡然停止,轮下必生火焰,皆其验也”。[34]王韬记录自己1868年参观火轮车时,有英人向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火车之行,轮铁迅捷,辙生火焰,昔时车每被焚。有阿士贝者,创造凉油,使车行久而轮不热,遂获厚利,富甲一乡。”[35]单从故事来看,该英人讲的很可能是1866年发明蒸汽机润滑油的美国医生约翰·艾理斯(John Ellis),其恰好在两年后王韬赴英的这一年创立著名的华孚兰机油公司(Valvoline)批量生产润滑油致富。王韬却把润滑油想成防止车轮生火的“凉油”,遂构想出一幅“轮铁迅捷,辙生火焰”的画面。可见“火轮”与其指涉的对象蒸汽机已然在王韬的认识想象中互不干涉,并且取得了新的意象。王韬至少也是亲眼见过、乘过火轮车的知识分子,而在道听途说的顽固派大臣那里“火”之意象就更夸张了。比如余联沅上奏反对修建铁路,就声称:“抑臣又闻之,外洋火轮车行走剽疾,电发飙驰,其中机器之蹶张,火焰之猛烈,非人力所能施,并有非人意所能料者。”[36]吴淞铁路开通以后,《申报》刊载了一首《咏火轮车》的竹枝词,其中开篇就是“轮随铁路与周旋,飞往吴淞客亦仙。他省不知机器巧,艳传陆地可行船”。[37]这里的“轮”自然也是指铁路上旋转的车轮,而“车轮生火”也随着吴淞铁路的引入在中国语境中成了事实。《申报》记载“火车遇阻”一事报道称,前日吴淞至江湾的火车正在行驶途中,突然被男女老少等八九百人拦路截停,问其原因,原来是前日机器车中的火星飞到了附近农民的茅屋上,导致房屋被毁。管车的洋人赶紧好言相劝,并承诺会派人前去查看,众人方才散去。然而没走几步,人群中有人喊“何为轻纵?”,众人复又蜂拥回来,企图拉住火车。“后觉机器力大,人不能敌,遂各释手”,火车才又重新开行。[38]这实在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农民们不仅直接遭受了火车造成的火灾,还在与机器的正面交锋中败下阵来,只是因为数百人的身体之力仍旧敌不过火车这一新鲜事物的力量。试想,如果换作轿子、马车,哪怕是小一点的汽车,也一定能不被“轻纵”的。火车就是这样真切地用它的“火”与“力”改变了人们的居住环境、生活习惯,乃至内在的观念世界——“机器力大,人不能敌”既是火车给晚清中国人身体记忆打上的深刻烙印,也开启了现代之物的自然化过程——即使不愿,也只能无可奈何、默默接受了。而晚清火车事故引发的火灾更是屡屡出现。单是津塘线,在光绪十五年便发生过两列对行火车相撞起火的事故,多人在火灾中丧生;光绪十七年,一列火车因为烟囱迸出的火星引燃车上装载的棉花包,导致车轮被毁、人员伤亡。[39]《点石斋画报》更是将光绪十七年这一起火车事故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加以报道,并声称这是“火车开行以来仅见之事也,故志之”。[40]
火车变“火”车的灾难性事故到了民国时期仍有发生。比如1924年1月18日,济南开往青岛的二次旅客快车因车内旅客吸烟起火,烧毁客车三辆,公事车一辆,旅客死十人,伤四十五人。[41]不过与晚清不同的是,民国的这种火车事故已是发生在铁路现代性建立起的框架之内,火车变“火”车不仅是事故,也开始成为故事,披上了隐喻的外衣,担负起象征功能,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中——这就是老舍创作于1939年的短篇小说《“火”车》。不过在进入这一文本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考察一下铁路与火车是如何生产,或如何协助生产出更为广泛的新词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