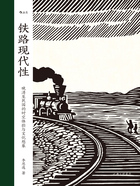
“铁路”的由来
意大利汉学家马西尼(Federico Masini)通过对19世纪汉语外来词的考察,指出“火车/火轮车”是当时“本土自生的新词”,而“铁路”则是德语“Eisenbahn”的“借译词”。[10]其所依据的文本材料是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Gützlaff)于1840年所著的《贸易通志》。据魏源《海国图志》中对《贸易通志》的摘录:“且火机所施不独舟也,又有火轮车,车旁插铁管煮水,压蒸动轮,其后竖缚数十车,皆被火车拉动,每一时走四十余里,无马无驴,如翼自飞。欲施此车,先平其险路,铺以铁辙,无坑坎,无纡曲,然后轮行无滞。道光十年,英吉利国都两大城间,造辙路九十余里,费银四百万元,其费甚巨,故非京都繁盛之地不能用。”“西洋贸易力求简易轻便之术:一曰运渠,一曰铁路。”[11]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得出“铁路”是从德语词汇借译来的这一结论固然不错,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就此画上句号——相反,从物的生命历史入手,问题才刚刚开始。[12]知道“铁路”这一汉语复合词是对“Eisenbahn”的仿译并不能推断出晚清中国人在接触铁路时就径直采用该词来指称相关对象。铁路并不是当时火车运行轨道唯一的名称。不仅是“铁路”和“Eisenbahn”具有不同的意向性样式,我们也无法保证在晚清被中国人逐渐广泛接受的“铁路”一词和当初普鲁士传教士创制的词语有着相同的内涵及意指。同理,我们也无法确认晚清词汇中的“铁路”与我们今天语言中的“铁路”有着一致的意向性样式。尽管我们仍旧使用着同一词语,却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段里、具体的经验中接触着已经变化了的事物。如果说这一借译词的确立隐喻了某种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比如中国/西方、传统/现代,那也仅仅是对身处现代之中的现代性研究者(往往是中国的研究者)才具有意义。身处现代性发生之际的晚清中国人——这也是一幅后设的图画,并不与我们分享同一种有关西方/中国、传统/现代的对立想象;与其寻找新词译介和科学认识、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不如干脆承认这更像是人与物、身体与机器偶然相遇的派生产物。
早在林则徐1839年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中,铁路还是尚未成形、不知如何表述的缥缈意象;只知道“火烟车”所行之路必须“穿凿山岭,砌成坦途”,而且“如值大寒河冻”,“火烟车”也可以在冰面上行驶。[13]也许在林则徐等人的想象中,“铁路”大约是和冰面一样,光滑平坦、不能有山岭丘壑之类的障碍。不过在西学流入的介绍书籍、译介历史中,铁路很早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名字——轣辘路。比如新加坡人息力1835年所撰的《英国论略》中,称“又造轣辘路,用火车往来,一时可行百有八十里”。[14]所谓“轣辘”,一指有着圆形转轮、缫丝用的繀车,例如王念孙疏证,“《方言》:繀车,赵魏之间谓之轣辘车……‘轣辘’与‘历鹿’同”;二指车轮转动的声音,金元好问《送吴子英之官东桥且为解嘲》诗云“柴车历鹿送君东,万古书生蹭蹬中”,元尹廷高《车中作古乐府》诗云“车轣辘,车轣辘,驴牛逐逐双轮声”;而有时则直接借指车子或车行驶的轨道,宋欧阳修《蝶恋花》词之十七云“紫陌闲随金轣辘,马蹄踏遍春郊绿”。宋苏轼《次韵舒教授寄李公择诗》云“松下纵横余屐齿,门前轣辘想君车”。用“轣辘路”指称铁路也许只是为了强调火车所行之路的与众不同,却因为对过去经验的继承,融入了圆轮的图像和转动的声音。为了更加突出铁路与过去常见之路的与众不同,郭实腊《万国地理全图集》(1838)和祎理哲《地球图说》(1848)将其改称为“铁轣辘之路”。[15]至此,材质——铁、图像——圆轮、声音——车轮转动,三者较为完整地构筑了铁路在晚清中国语言中的显现方式。然而“铁轣辘之路”很快就被“铁路”取代,比如郭实腊随后撰写的《贸易通志》(1840)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1849)。这一改变是出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还是为了和德语“Eisenbahn”形成更好的对应?那么“铁轣辘”难道不也是一种对应的可能选项吗?况且,从“铁轣辘之路”到“铁路”并没有显示出对铁路描述信息量的增加,或是反映出人们对铁路认识水平的提高。《瀛环志略》更是直接将“铁路”等同于“用铁建造的路”,比如“造火轮车,而熔铁为路以速其行……内地通衢,多用铁汁冶成以利火轮车之行”。[16]“铁”似乎成了铁路的本质,“铁路”也变成了一种“属加种差”的真实定义法——我们并不知晓徐继畬在使用“铁路”一词时是否懂得这是从德语仿译过来的词。为了更清楚说明铁路的样式,或者更像是为了消除铁路就是“铁造之路”的印象,丁韪良1868年编译的《格物入门》就指出铁道之式首先是要“于车辙两边,各置大木,须极坚固。大木之上,钉以凸出铁条”。[17]《申报》在吴淞铁路落成之前刊登了一篇普及火车铁路的文章,其中也特别提到“考铁路之制,非以铁铺路也。乃以铁为槽,接长其形如倒写之人字形路”。[18]确实,如果仅考虑技术原理、资讯传递的准确性,“铁路”算不上是一个优秀的命名选项;可倘若将其合法性来源归于原本的德语词,又未免陷入一种对名词出现优先权的盲从之中。或许以“铁”为路的意象对晚清中国人的刺激太强烈,将此新奇之处作为辨识这种新事物的特征也未必不合情理。从“铁轣辘之路”到“铁路”真正引起改变的既不是认识论水平也不是语言学规范,而是新经验对旧经验的覆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转化。“轣辘”的消失也许对晚清人来说并不成为问题,作为日常经验之内的事物本来就无须区分“轣辘”与“路”,值得强调的当然是通过技术创造出的新物——“铁路”。可对于已经变换了参照系,步入现代之中的我们而言,“轣辘”成了只能在古代诗文、图画中寻找到的事物,其意向性的所指与所谓的传统、过去连在一起:经验遭到了覆盖与转化,语言指称也出现了断裂。如果我们并不认为人们可以自觉地选择某种语言概念,同时也不想用一种抽象的名词,或是隐藏幕后的整体力量来解释这种现象,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设想:并不是人们在为事物命名,而是铁路这种现代之物以其向晚清中国人独有的显现方式选择了自己的名字。作为语言概念的“铁路”与现代之物的铁路所呈现出的一种分裂,恰恰说明我们不应在“阶梯进步”式的启蒙想象和“直线型”的认识设定中去研究这些名词概念。这一点在“火车”这个所谓的自源新词中有更强烈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