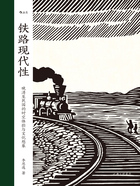
第一章
沿着语言概念的轨迹:铁路的命名故事
物的名字
为什么晚清的中国人要用“铁路”“火车”指称这种来自异域的新事物呢?是西学东渐过程中对外来语的翻译?是一种对新事物、新经验的命名?还是人与语言的历史纠葛中一次偶然的相互成全?不论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还是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理解都始于反思所谓的命名问题:他们宣称语言符号联结的不是事物与名称而是概念与音响形象;抑或命名只是对各种语言游戏的片面误解,这样一个事物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名字其实是偶然的、约定俗成的。[1]这意味着作为物的“火车”与汉语中的“火车”、英语中的“train”、德语中的“der Zug”、日语中的“汽車(きしゃ)”没有必然的本质联系,而且本来也可以被叫作“水船”“椅子”“phallus”等。那么约定俗成又意味着什么?这看似充满魔力可以解释一切的回答却也流露出某种苍白无力——它的实质含义无非是“人们就是这么用的”。如果你想继续追问下去,维特根斯坦会告诉你问错了问题。因为词语在语境中的用法就是它的意义,若以为这背后还存在什么“真正的意义”,其实是想把丰富多彩的语言游戏缩减为某一确定的答案——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冲动。[2]
但思想中的“错误冲动”仍会留下身体经验的痕迹,考虑到像“铁路”“火车”这些新词的出现、确立总是伴随着新式器物与技术在晚清的接受以及中西之间的翻译交流,那么“约定俗成”又可以替换为“文化与历史”。同样的对象,在英文中叫“railway”,在中文里则是“铁路”,这或者是因为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即使意指同一个对象,但意向性(intentionality)样式不同,那么对不同语言、国家的人意味也就不同。[3]或者我们可以将其归因于某些历史条件,比如刘禾(Lydia H. Liu)提出的跨语际实践就是考察翻译新名词在中西意识形态及观念的互动中兴起、代谢、获得合法地位的具体过程。所谓新词语的建构本身就是历史变迁的隐喻,人们借助翻译创造着对等关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喻说。[4]然而这两种思考路径对事物名称的探究均依赖于个体对事例的枚举与归纳,却最终导向了整体性、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宏伟框架——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这种对新词概念、外来翻译的历史化处理是将事物本身从历史和文化中割裂了出去,变成话语的点缀。换言之,物的名称是任意的,重要的是物背后不可见的文化因素,是物的名字暗含着的历史内涵。这种表面与内在的设定和习以为常的“深度模式”,往往使得对命名的探究变成不同意识形态争夺合法性的战场——用一种约定俗成去取代另一种,由此偏离了物本身和它们的名称。[5]
借由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的反思,我们之所以认为像衣服这样的器具、事物肤浅、不值一提,往往是因为符号论式的思维方式预设了内外、深浅这样的关系。我们总以为本质和意义存在于器具表面的背后,事物的内部深处,“我们不得不探求自身深处的内在以求找到自己,但这都只是隐喻罢了。我们的内在深处只有血液和胆汁,而非哲学上的确定性”。[6]
另一方面,对于“铁路”这类新名词的研究也倾向于将其和近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认知水平绑定在一起。特别是那些和自然科学、现代技术相关的术语名称,它们的确立过程总是由繁杂到统一、由随意到规范、由错误到正确——名称的合法化。这也与所对应的物、技术在晚清中国从误解到摸索,再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大规模引进这样一个接受过程相一致。比如黄兴涛提出:“近代中国人思维方式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变化,可能正开始于和被强化于大量带有‘现代性’品格的各种新名词的流行与潜移默化,尤其是双音节以上的词汇和抽象概念的大量引入、创造、广泛传播与社会认同之中。换言之,正是那些人们在不经意之中反复使用的表示近现代新生事物、新思想的新名词、新概念,在社会化的重要维度和实践功能的意义上,将思维方式与基本观念的变迁两者有机地联系了起来。”[7]而王宪群所勾勒的蒸汽技术在晚清社会中之接受过程,就是其先在语言概念上误解,继而在实验和学习中摸索,最终借助制度创新和资本实现大规模的引进。[8]这种认为现代物与技术的语言概念影响人们思想认知的观点,在晚清的传教士翻译家们那里早已出现。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指出,以傅兰雅为代表的晚清传教士们进行的翻译工作,就试图通过建立一套系统、科学的术语命名体系作为启蒙的工具。依靠发明新词汇、确立新术语,并使其标准化、统一化,继而有效地普及科学,提升晚清中国人的知识水平。[9]不过事实上,事物命名的变化、技术术语的演进并不一定和我们对物与技术的科学认识存在必然关联,更不用说是正相关联系。我们对于现代技术的熟练应用和习以为常也并不代表我们对技术有了深入的理解。现代社会中,人们关于物的命名、应用和思考也并不必然是统一的。我们将一个对象命名为“智能手机”并不必然反映我们对于电子技术、通信物件的思想认识水平;同样,手机的使用者即使无法清晰说出它的运作原理,也不影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熟练地使用、享受它。这一模式和晚清中国人对于铁路的命名、认识和接触其实并无太大区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章认为物的指称命名和我们对于其的认识思考并无必然关联,但从不否认技术和器物有能力在新生名词及抽象概念中留下自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