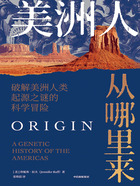
人类学的人种研究遗毒
海伊被无罪释放使得赫尔德利奇卡无所顾忌地研究来自芒西墓地的遗骨。他于次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些遗骸的专著,名为《莱纳佩人或特拉华人以及普通东部印第安人的体质人类学》。[39]
在这本专著中,他首先简要讨论了缺乏这一族群的疾病和病理资料的现状,然后转到真正的重点:测量和比较。
赫尔德利奇卡将这些颅骨分为几种“类型”,并指出大多数颅骨属于“中长头型”,但少数个体为一种附加类型,即“短头型”。这种分类反映了体质人类学家研究过去和现在人类差异的基本架构是“人种”。
人类可被划分为几个类别,并相应地有高下之分,这种观念在早期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可谓根深蒂固。[40]由于人种分类法相当直观,因此很容易随手拿来解释人类的差异:根据其不完善的逻辑,既然我们能够轻易“察觉”人与人之间的差别,那么这些不同之处(无论多么肤浅),似乎正反映出我们这个物种的一些本质性的自然属性,而且从古至今一直如此。科学家把人种分类视为先验真理,并寻找实证方法予以证明(这相当讽刺,他们必须找到假设已经存在的东西)。在体质人类学中,演化和深时[41]观念已经取代了《圣经》的字面意义,但人种分类和贵贱之分仍然存在。
18世纪,瑞典医生和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在他的《自然分类》(1735年)一书中正式把人类作为独立生物体进行了描述。林奈除了开发出生物学家至今仍在使用的生物分类系统外,还根据人类的身体特征、性格气质、文化习俗、行为模式,把人分为四种“类型”:亚美利加人、欧罗巴人、亚细亚人和阿非利加人。[42]每类人种的全体成员都具有一种“自然本性”。根据林奈的说法,亚美利加人是“表演型”(性格外向、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领导者),同时也固执狂热;他们“在自己身上画红线条,受传统约束”。林奈分类方案的层级框架契合了“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或由亚里士多德首次设想的“自然等级”(scala naturae)的概念[43]。
林奈的继承者们竭尽全力,试图回答该理论尚未解决的问题。哪些特征最适合对人类分类?哪种分类模式最有效?
没有人质疑人类是否应该被分为不同类别,或按照人种的所谓先天特质排出高下有何不妥。对早期欧洲科学家来说,很明显,欧罗巴人居于顶端,阿非利加人位于最末。其他人种——包括美洲原住民——则介于两者之间。
测量颅骨尺寸成为一种流行手段,可以很快地将不同民族划分到各个种族类型中去。这套方法被称为“颅骨测量法”。
医生和博物学家约翰·布卢门巴赫(Johann Blumenbach)就是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布卢门巴赫于1752年出生在德国哥达(Gotha),在论文《论人类自然史》(1775年)中,他将人类分为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并试图将这些不同分组与《圣经》中的创造论协调起来。由于《圣经》中并没有提及美洲原住民这个神秘族群,因此,敬畏上帝的欧洲天主教自然哲学家们不得不费尽心思解决这个谜题。在《圣经·旧约全书》中,挪亚一家在大洪水中幸存下来,地球上的所有族群都是他儿子们的后代。“闪”(Shem)是亚洲(蒙古)人种的祖先;“含”(Ham)是非洲(埃塞俄比亚)人种的祖先;“雅弗”(Japheth)是欧洲(高加索)人种的祖先。
许多学者认为美洲原住民可能是闪的后裔,因为他们的体质特征与亚洲人相似。其他人则认为他们甚至可能就不是人类。布卢门巴赫是最早将颅骨测量这一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种分类的科学家。他还是人类同源说的支持者,即上帝只创造了一个单一人种——高加索人种[44],其他不同人种类型则是人迁徙到新环境很多代后,从高加索人种“退化”而来的结果。因此,通过颅骨研究,人们就可以探索人类的历史。
布卢门巴赫将美洲原住民归入蒙古人种,并认为他们是分几拨移民到美洲的亚洲人的后代。
虽然布卢门巴赫并不认为非高加索人种就智力低下,但他的确相信高加索人种凭借他们的颅骨比例,成为“最完美”的种族。他的类型论为后世医学和人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埋下了诸多隐患。

世界颅骨指数(1896年),摘自《大众科学月刊》(Popular Science Monthly)第50卷。
布卢门巴赫理论的主要继承者是费城医生和学者塞缪尔·乔治·莫顿(Samuel George Morton,1799—1851),赫尔德利奇卡称其为“体质人类学之父”。莫顿认为颅骨对研究人种科学特别有用。它们具有双重功效,不仅能显现一个人的种族属性,还能揭示他的智力水平。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颅骨容积一定直接反映智力水平:脑容量越大,人就越聪明。(我们现在知道,这并非事实。)
莫顿以布卢门巴赫的方法论为基础,对颅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种分类研究,认为除了容积外,颅骨形状也是一个重要的种族标志。颅骨指数——颅骨最大宽度与最大长度的比值——应运而生,成为将人分为不同种族的最简单和最流行的手段。所有族群都属于三类人种之一:长头型人种、短头型人种,以及中头型人种。这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于尼格罗人、蒙古人和高加索人。
莫顿推断,计算平均颅骨大小是评估种族间智力差异的最佳方式,并开发了一套测量颅骨容积的系统方法。其主要手段是用芥菜籽(后来又用铅粒)填充颅骨,再记录填充每个颅骨所需的芥菜籽数量。
根据测量结果,莫顿对布卢门巴赫人种分类下的各人种进行了智力排名,高加索人种居首,埃塞俄比亚人种垫底。莫顿关于非高加索人种天然低劣的研究结论被明目张胆地用来为奴隶制辩护,也成了冠冕堂皇地从美洲原住民手里窃取土地的理由。[45]
但莫顿在种族起源问题上与布卢门巴赫的意见相左。莫顿相信多源发生说,将人类之间的差异解释为是每个人种独立产生的,而非挪亚的儿子们(最初是高加索人种)的后裔散布全球后,最终形成的结果。他确信,每个人种的颅骨大小和形状的差异可一直追溯到上古时代,不过大洪水发生的年代距离现代太近,无法解释所有这些差异的形成原因。如果人种特征固定不变的话,那便意味着不同人种实际上是独立物种。
与莫顿同时代的博物学家让·路易斯·鲁道夫·阿加西(Jean Louis Rodolphe Agassiz)概括了多源发生说的另一层重要含义。阿加西假定,不同物种是在不同地区为适应当地气候而创造出来的,因此不会——也不可能——离开它们原来的家园很远。阿加西判断人类也是如此:每类人种都单独产生于自己所在的大陆,迁移只是人类历史上的例外事件,而不是常态。
因此,了解每个人种的起源就可以帮助科学家掌握全人类的历史。莫顿本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起源特别感兴趣。在他最著名的作品《美洲人颅骨》一书中,他对美洲原住民进行了形态学研究,提出美洲原住民的特点是:
肤色棕褐,头发顺直,又长又黑,胡须稀疏。眼睛为黑色,眼窝深陷,眉毛低,颧骨高,大鹰钩鼻子,大嘴巴,厚嘴唇,身材结实。小颅骨,顶结节间隙宽,颅顶突出,枕骨平坦。美洲人的心理特点是不愿修身养性,求知慢,浮躁,报复心强,好战,拒绝航海冒险。[46]
在21世纪的读者看来,这一描述实在离谱,首先当然是内容偏执,此外还把体质和非体质特征莫名其妙地结合起来。今天,科学界普遍接受的人种分类方式主要是基于体质特征:皮肤颜色、头发颜色、眼睛和鼻子的形状。像“不愿修身养性”这样的“术语”对现代读者来说非常奇怪(尽管如果你多接触一些种族主义的观点,你肯定还会遇到关于智商和性格之类的无耻说法)。
但是对于一个有兴趣研究人类学的19世纪医生而言,这种将体质和非体质特征混合分析的做法是认识如何把人类划归为不同种族,以及这些种族是如何分出优劣的最重要的方式。这套方法便成为由包括赫尔德利奇卡在内的一小群学者创立的新学科——美国体质人类学的核心要素。[47]
体质人类学的早期关注点受到了当时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在20世纪上半叶,优生学——一种通过控制生育来“改进”人类的运动——在美国社会方兴未艾。一些——尽管不是全部——体质人类学的早期创始人认为他们的工作对优生学至关重要。[48]
一旦演化论取代了《圣经》中关于人类起源的故事,那么人种分类也要随之改变以适应演化论。于是,“野蛮人种”被视为人类演化早期阶段的代表,研究他们有助于重建人类的“进步”历程。
赫尔德利奇卡和持同一观点的同事假设颅骨形状,特别是颅骨指数,是一个非常稳定、固定不变的先祖标记,并且有助于刻画人种特征。然而,其他颅骨测量学研究却破坏了这一理论。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发现,美国的东欧移民之子与其母国同龄孩子之间的颅骨指数实际上并不相同。[49]这证明了环境对本应固定的特征产生了影响,从而削弱了人种分类在体质人类学研究中的实用性。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体质人类学家和遗传学家助纣为虐,为阿道夫·希特勒实施恐怖的“最终解决方案”[50][51]提供理论依据。直到战后,这种人种分类框架才被这门学科(大体上全盘)抛弃。[52]
黑人医生、解剖学家和体质人类学家威廉·蒙塔古·科布(William Montague Cobb,1904—1990)的研究也同样驳斥了同时代的科学家(包括赫尔德利奇卡)的论点。1929年在霍华德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大约同一时间,美国体质人类学家协会成立),科布开始在俄亥俄州的西储大学(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与T.温盖特·托德(T. Wingate Todd)研究体质人类学。托德的研究表明,在大脑发育方面各人种没有先天差异,并强烈反对体质人类学界部分人士所表现出的种族主义。他在骨骼发育和功能解剖学方面对科布进行了培训。科布后来在霍华德大学建立了一个藏品丰富、高度重视教学和研究的骨骼库(当前由法蒂玛·杰克逊负责管理)。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功能解剖学的文章,同时也研究并发表论文反对人种类型学说。在其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人种与赛跑运动员》一文中,科布批驳了一种流行观点,即非裔美国短跑运动员、跳远运动员和其他运动员与其他种族的运动员相比,由于解剖结构上的差异而具有先天优势。他写道:“从遗传学上讲,我们知道他们的构成并不一样。但所有的尼格罗人冠军都没有一项共同的体质特征(包括肤色),可以确定他们是尼格罗人……事实上,如果所有黑人和白人冠军选手不加区别地站在一起接受检查,除了那些受制于美国舆论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会赞同人种与运动员的能力毫无关系。[53]
尽管体质人类学家中的反种族主义人士付出了巨大努力,但该学科在20世纪初还是为人种分类学说提供了“科学支持”。现在,这种分类牢牢地扎根于公众思维之中,遗毒深远,导致很多针对非裔美国人、原住民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暴力。
许多体质人类学家则利用形态学数据,竭力抓住生物种族这一概念不放手。今天,遗传学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人类差异极其详细的描述,揭示出类型论的浅薄。[54]20世纪早期遗传学研究表明,在线粒体和Y染色体层面上,早期体质人类学家经常使用的人种分类并不符合实际遗传差异模式。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全基因组测序能力,只要能够采集到基因,就可以获得任何人的遗传谱系信息。研究证明:虽然各个族群在遗传上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遵循布卢门巴赫、莫顿或其他人提出的人种类型模式。如果这种说法让你感到吃惊,那只是因为这些概念已经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中固化了。
人类DNA有99.9%是相同的。正是这微小的差别——只有0.1%——与广义上被称为“环境”[55]的东西一起,导致我们的外貌或表型发生了显著改变。大部分遗传差异以一种被称为渐变群(梯度变异)的模式分布,或随地理距离的变化而逐渐变化。仔细想想,这是很有道理的。比之相距甚远的族群,住得较近的族群更有可能相互通婚,产下后代。因此,不同的等位基因,也就是基因样式,按照被遗传学家称为地理隔离的模式逐渐分散开来。一些性状和潜在基因显示出在特定环境中自然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在高海拔地区,自然选择增加了遗传基因变异的区域频率,从而帮助人类克服缺氧。由于人类多次迁徙,几乎每次都引起基因混杂,因此,迁移模式也变得愈发扑朔迷离。与支撑早期体质人类学家研究的类型框架相反,古DNA表明,纵观整个人类历史,没有人在基因层面是“纯粹的”。[56]
自然选择、遗传漂变、变异、基因流所组成的演化力量与我们的迁移史(或反之,在一个地区持续聚居的历史)、文化习俗叠加起来,共同形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类差异模式。到目前为止,遗传和表型上的多样性在生活于非洲的族群中最为丰富。我们人类就是从这块大陆发源而来的。族群所在地距离非洲越远,通常其基因多样性便越少。我们这个物种在迁徙途中留下的基因遗产正反映了人类对新环境的适应。按白人、黑人、亚洲人(或高加索人、尼格罗人和蒙古人)分类并不能准确反映这些复杂的情况。[57]
但是,不能仅仅因为人种并不是科学意义上准确区分人类差异的方法,而否认这个概念的“真实性”。尽管它诞生于特定的文化历史阶段,但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真实存在的,并塑造着我们的生活。[58]美洲原住民及其祖先蒙受的可怕遭遇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