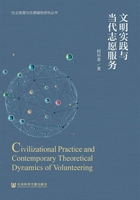
五 小结
本章考察了志愿精神概念的构成和解释的维度。作为一般化的概念,志愿精神是志愿服务的核心构成要素,它表现为规范性与实践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各种慈善理念与团结奉献的亲社会行为具有悠久的历史。志愿精神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价值理念。对志愿精神的历史阐释,需要结合地方性的社会情境与文化传统进行考察。不同历史、文化和语言的情境下一些地方在话语层面虽然缺少志愿服务和志愿精神的提法,但是许多实际的行为和活动已经符合志愿精神的价值内涵,它们结晶化为人类宝贵的精神文明财富。
对志愿精神功能的理解,本章从个体、组织、社区和社会四个维度,结合志愿精神的实践属性进行分析。志愿精神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了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志愿精神的践行有利于推动社会团结与整合。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改善社区生活状况,还提升了志愿者和居民的认同感和幸福感。组织维度的志愿精神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前者对应包括志愿组织在内的非营利部门的社会组织,后者则泛指一般化的现代社会组织。许多商业机构和组织不仅鼓励员工参与志愿服务,还以捐赠和基金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志愿精神。
志愿精神的传承和传递,社会化是主要的途径之一。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社会化内容与需求不一样。许多经验研究揭示,青少年阶段的志愿服务经历,对志愿精神价值理念的学习和接受,甚至会影响成年阶段的志愿服务参与。因而,家庭和学校的志愿服务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此外,对老年人而言,参与志愿服务是实现再社会化的一种方式,不仅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亦构成了老年阶段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
对于志愿服务在当代社会发生的一些新变化与新动向,志愿服务研究领域的学者借鉴并拓展了新现代性、风险社会和个体化社会等理论,考察志愿精神的新内涵与志愿服务的新样态。一方面,在全球化和社会流动加剧的背景下,个体化社会的过程,传统的家庭、社区和基层的联结纽带趋于弱化,以社区为单位的志愿服务组织受到冲击,它面临在年青一代中缺少吸引力的发展困境。另一方面,个体化社会并不是社会的原子化或者将导致社会解组的后果。个体化不仅包括与传统纽带和社会结构的“脱嵌”,还存在与新组织和社会结构“再嵌”的可能。更为重要的是,个体化社会蕴含了“重建”社会团结的希望,利他主义与个体化的调适与整合,不仅使得“利他个体主义”成为可能,亦为新志愿精神和新志愿服务提供了新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化社会视角下的志愿服务研究,新与旧、现代与后现代、集体主义与反身性这类志愿服务的二元划分,更多地被当作阐释性的理论框架。相关研究也表现出较强的反思性,强调志愿服务虽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起的志愿服务会取代传统的志愿服务类型,多元化与混合形态的志愿服务才是更接近现实的情况。因而,传统类型的志愿组织不应该把个体化社会变迁视为一种威胁,挑战的背后还包括发展的新机会。事实上,许多志愿组织的转型调整,以及新志愿组织的出现,通过制定符合新志愿者兴趣与认同的项目,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新志愿者的参与热情。
最后,个体化社会以及相关新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代表了欧洲当代学者的集体智慧,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或者西方社会发展新历史阶段与动态的反映。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志愿服务实践可能会面临一些与欧洲和西方社会不同的情况。本土学者在研究中需要保持足够的反思性和批判性,个体化社会作为理论解释框架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仍需要结合具体的经验事实进行考察分析。
[1] 参见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voluntarism。
[2] 参见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volunteerism。
[3] 斯蒂芬·P.奥斯本对三个和志愿精神相关术语的辨析,认为它们都含有志愿服务行动的内容,但是所指涉的对象却存在区别。voluntaryism对应的是以志愿行动或者志愿原则建立的系统,它代表了一种组织社会的伦理;volunteerism也包括了志愿原则,但它更多的是用来概括社会中个体的行动;voluntarism则用来描述组织与制度层面的志愿行动(Osborne,2002:7-14)。
[4] 参见https://www.unv.org/volunteerism/power-volunteerism。
[5] 2011年的报告提到了志愿精神的新面向,强调当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志愿服务提供了新的实践空间。在《数字时代的志愿服务》一章,将重点讨论这部分的问题。
[6] 报告列举了北欧国家挪威的案例,志愿精神扎根于传统信念与社区实践中,Dugnad在挪威被用来表示家庭、邻里和社区的合作,展开集体的志愿工作。
[7] 参见 https://www.theguardian.com/voluntary-sector-network/2015/jun/01/a-history-of-the-volunteer-how-active-citizenship-became-the-big-society。
[8] 这七项基本原则还包括:人道(humanity)、公正(impartiality)、中立(neutrality)、志愿服务(voluntary service)、统一(unity)和普遍(universality)。
[9] 不仅是家长对青少年的影响,实际上这里还存在反向社会化的可能,青少年的志愿服务实践带动父辈参与志愿服务(参见 McFarland & Thomas,2006)。
[10] 志愿精神在代际的传递,以及对志愿服务参与的影响是学者长期关注的主题。除了传统的生命历程方法和家庭社会化理论,受生物信息技术与基因社会学的影响,对亲社会行为的代际传递的研究,也有学者尝试从基因遗传的视角对志愿服务参与进行考察。相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对研究伦理也有极高的要求(参见 Son & Wilson,2010)。
[11] 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志愿服务的管理和实践方式,但是它也对志愿者的数字素养提出了要求。
[12] 事实上,在对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动机的考察中,利他主义在动机中固然代表了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个人能力的提升以及自我实现也越来越成为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原因。关于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在动机构成中的辩证关系,在参与动机一章中会有详细讨论。
[13] 但是,集体主义的志愿组织在社会变迁背景下面临再生产困境:新移民并没有嵌入地方社区的网络中,也缺少过去那样的组织认同,组织的发展缺少新生力量的加入。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的改善,邻里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相应发生改变的还有对志愿组织的期待与需求。随着社区精英的老去,传统社区网络的维系和再生产遭遇领导困境。尤其是宏观经济的发展,对社区的渗透,冲击了地方社区固有的网络结构与价值规范(参见 Eckstein,2001)。虽然埃克斯坦因考察分析的主要对象是美国情境下以意大利移民为主的志愿组织,但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对社区志愿组织的冲击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14] 国内学者对志愿者参与动机的考察,也以现代和后现代的纪元性时间来概括动机构成与取向的不同,同时亦认为混合型的动机在志愿服务中呈现为一种常态(吴鲁平,2007)。
[15] 志愿组织为适应新社会趋势而做出变化与调适,其潜在的后果还需要结合经验研究来进行考察和评估,一些研究揭示了其矛盾的一面。以加拿大医院志愿者为例,通常它对志愿者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要求,但是大量不同类型和动机志愿者的涌入可能会提高组织运行的成本,对志愿者的管理也要求更严格的管理手段(参见 Handy & Srinivasan,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