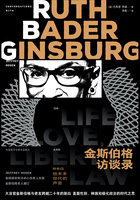
引言
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一段友谊始于一次电梯里的邂逅。那是1991年我第一次见到鲁斯·巴德·金斯伯格,当时我还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下亦简称特区上诉法院)的一名年轻的法官助理,她则是该院的法官。我碰到她时,她正从一个叫“爵士操”的健身班往回赶。她的气质让人敬畏,在我们乘电梯的时候,她一直保持着斯芬克斯式的沉默,不认识她的人可能会误以为她有些冷傲。
我想打破沉默,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问起她最近看过哪些歌剧。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个歌剧迷,但这似乎是个比较稳妥的话题。我们很快就因为对歌剧的共同爱好而建立了联系,并由此开启了一场持续至今的音乐对话。
一年后,我被聘为《新共和》的法律事务编辑。这是另一个幸运时刻:在28岁的年纪,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工作,为一家华盛顿的杂志社撰写有关法律和最高法院的文章,这家杂志社的法务撰稿人包括一些宪法学上的传奇人物,比如勒恩德·汉德[1]、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2]和亚历山大·比克尔[3]。金斯伯格和我开始在通信中谈论起我最初发表在《新共和》上的一些文章和她最近看过的一些歌剧。1992年的总统大选结束后,我给她寄了一篇文章,其中指出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4]对那位即将上任的民主党总统[5]和国会而言已经成了“反对派的领袖”,她圆滑地回复道:“这篇有关我那位大法官朋友的文章很精彩。”几周后,也就是1993年1月21日,她在看了我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跟华盛顿国家歌剧院上演的一部平淡无奇的歌剧《奥泰罗》有关——后回应:
如果你和哪位朋友有空的话,希望你们能来看2月17日周三的《图兰朵》[6]排演。这次演出没有预告,不过座位就在过道前面……今年秋天还有另一部歌剧——《沙皇的新娘》,我宁愿你看的是这个而不是《奥泰罗》。这部歌剧也许能让人们对华盛顿国家歌剧院产生些善意的看法。
我去看了《图兰朵》的排演,并对她赠票给我表达了谢意,此后她去看了开幕演出,而且在2月25日的一封信里跟我分享了她的看法:“《图兰朵》是一部宏大的歌剧。特别是第一幕的合唱,在我昨晚观看的演出中尤为壮观。女高音伊娃在演唱时嗓音非常饱满,卡拉夫在演唱《今夜无人入眠》时的表现比我预想的还要好。[7]很高兴你能有机会在更明亮的光线下和更舒服的座位上观看本地剧团的演出。”
她还在这封信里对我寄去的一篇文章作出了回应,我在该文中称赞了戴维·哈克特·苏特大法官[8],但批评了以他心中的英雄约翰·马歇尔·哈伦二世大法官[9]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哈伦崇拜”,后者是沃伦时代[10]的一位温和保守派法官,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将他视为司法克制[11]的典范。
很欣赏你对苏特大法官的评论,但我认为你对哈伦大法官的赞誉比他应得的要少。我敬爱的老师和朋友杰里·冈瑟[12]就非常尊敬哈伦,因为他几乎总是能充分地向我们说明他的立场,没有伪装,也不会大张旗鼓。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韦尔什诉美国案[13]中撰写的协同意见[14],这些意见在我从事平权辩护的那段日子里给我提供了莫大的助力。
金斯伯格引用1970年的韦尔什案,不但显示了她作为一名辩护律师的战略眼光,也体现了她作为一名法官对哈伦的明晰度的尊重。在那份意见书中,哈伦认为对违宪行为的补救办法无非是扩展或废止:换言之,如果法院判定某一法律因偏袒某一特定群体而违宪,那么它既可以废止相关的歧视性法律,也可以将其受益者扩展至那些遭排斥的群体。金斯伯格在1979年的一篇法律评论文章中就援引了哈伦在韦尔什案中的意见,这篇文章名为《对司法权补救违宪立法的一些思考》,她在其中解释说,在某一性别因偏见性刻板印象而受到排斥的那些案件中,作为辩护律师,她曾数度请求最高法院将社会保障和公共援助都扩展至男女两个性别,而韦尔什案的这份意见让她颇受激励。1韦尔什案也为她赢得的首宗性别平等案——莫里茨诉国税局局长案[15]——提供了策略,该案如今已因2018年上映的电影《性别为本》而名垂青史。在莫里茨案中,她成功地说服了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将以往只有那些要照顾依亲父母[16]的未婚女性才能享受的税收优惠,扩展到了同等处境下的未婚男性。
在这封友好来信的鼓舞下,我在3月15日为金斯伯格法官的60岁生日送上了一束鲜花,三天后,她用一张手写的卡片回复道:“这束鲜花为我花甲之年的首次开庭增色不少,它让我想到了这个周末的春色。”她还说自己刚看了亚纳切克[17]的《狡猾的小狐狸》的一场彩排:“没有邀请你跟我的助理团队去观看3月10日中午在华盛顿国家歌剧院举办的‘小狐狸’的彩排,懊悔万分。向你致以诚挚的谢意,金斯伯格。”
3月20日,拜伦·怀特大法官[18]从最高法院退休。金斯伯格是有可能接替他的几位候选人之一,但她的提名遭到了一些女性团体的反对,她们认为她够不上自由派;因为在罗伊诉韦德案[19]中,她对最高法院所作的堕胎权裁决中的法律推理提出过批评,尽管那项裁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4月下旬,我为《新共和》撰写了一篇题为《名单》的文章,按升序对七位领先的候选人进行了排名,并以金斯伯格作为最终人选。对于比尔·克林顿总统的那份候选人名单,我写道:
在所有候选人当中,金斯伯格是自由派和保守派两方最为尊重的人选。她对罗伊案的审慎立场为克林顿在这场决定性的考验中斩断戈耳狄俄斯之结[20]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在备忘录和会议上,她也是最有可能赢得摇摆不定的大法官们支持的候选人。金斯伯格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她和那些含糊其词的中间派可能过于亲密了。不过尽管她愿意在一些次要的细节上妥协,其核心立场——广泛的法院申诉途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性别平等——仍是以自由主义为原则的典范。金斯伯格受到的提名将是自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受提名以来最受赞誉的提名之一,而后者曾在1960年拒绝将金斯伯格聘为助理,理由是他并不准备聘用一个女人。现在,我们准备好了。2
此前几周,尽管我当时并不知情,但金斯伯格法官的丈夫马蒂·金斯伯格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一场低调的游说活动,他希望能说服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支持金斯伯格。莫伊尼汉最初还举棋不定,后来则开始享受起与同僚——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一较长短的机会;肯尼迪当时支持的是自己家乡的候选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斯蒂芬·杰拉尔德·布雷耶[21],后者坐镇波士顿。莫伊尼汉在1993年6月21日给我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和总统谈话时我肯定已经看了你的社论,而且对此有所考虑。另一方面,到6月8日那一周时,总统无疑已将选择范围缩小到了三名候选人:布雷耶法官、吉尔伯特·梅里特法官[22]和内政部长布鲁斯·巴比特[23]。然后金斯伯格法官突然又出现了。”
莫伊尼汉后来又写了一封未公开的信,并且传真给《新共和》,其中讲述了他此后所扮演的角色。
1993年5月12日,我和总统以及(他的助理)哈罗德·伊克斯和戴维·威廉一起飞往纽约。航程经过三分之二的时候,总统把演讲稿放到一边,转身对我说:我应该提名谁来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我说那肯定只有一个名字,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他说女人们都反对她。我说这也是提名她的另一个理由。她们对她在纽约大学所作的麦迪逊演讲感到愤愤不平(她在演讲中批评了罗伊诉韦德案中的推理),但她无疑是对的。话题结束。
一个月后的6月11日,我在电话里和(白宫通讯主任)戴维·格根谈了一些事,几乎是在谈完了以后,他才问我希望看到谁进入最高法院。我跟他讲了我和总统的谈话。与此同时,我收到了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迈克尔·索文写给总统的一封信的副本,他在信中提到了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院长于最高法院搬入新楼50周年之际在最高法院发表的一次演讲。格里斯沃尔德院长提到了各种各样的活跃于这一时期的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协会成员。他特别注意到了种族平等领域的瑟古德·马歇尔[24]和性别平等领域的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格根问我能不能把那篇演讲稿寄给他。碰巧我的助理埃莉诺·森图姆有个妹妹就在最高法院工作,而且还曾在最高法院的图书馆工作过。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埃莉诺给她妹妹打了个电话,演讲稿在一个小时内就传真过去了……第二天午夜后不久,在看完一场篮球比赛后,总统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支持鲁斯·巴德·金斯伯格。3
1993年6月14日,比尔·克林顿提名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为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法官慷慨地将其归功于我在《新共和》上的那篇文章,她认为是那篇文章帮她冲过了终点线。金斯伯格在她6月18日给我写的信中说:“是你让这个念头扎了根,我会努力让它发展壮大的。”这篇文章其实只是机缘巧合罢了,我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加入了金斯伯格的朋友及其仰慕者的行列,我们为结识她感到荣幸,自发而异口同声地推荐她。
在接下来的25年里,我与金斯伯格大法官保持着亲切却时断时续的通信。她有时会在赞成或不赞成我的某篇文章时给我来信,有时也会给我发来一部特别有趣的歌剧的邀请函。(我们在这方面有个乐此不疲的老哏,那就是她喜爱的任何一场华盛顿国家歌剧院的演出“可能都配不上你的高端标准”。)
比如1993年9月24日,金斯伯格在她首次在最高法院听审前的一周半,就给我发了一份华盛顿国家歌剧院上演的《安娜·博莱纳》[25]的邀请函,并补充道:
如果我对塞缪尔·巴伯[26]的作品有更多了解,我肯定会和你一起去欣赏他的作品。现在演出厅内的状况很好,但还要等几个星期。到11月底,新地毯应该就铺好了,房间应该重新粉刷过了,从当地博物馆借来的艺术品也应该就位了。
我随函附上了一本不太知名的杂志——1993年的《布里尔利学校夏季简报》里的一页,你有空时可以一读。
这本刊物复印了她的女儿简在多年前的高中毕业纪念册中写下的一页,其中宣告了简的“理想:看到她的母亲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到头来可能会:任命她的母亲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翌年,哈里·布莱克门[27]辞去了大法官职务,克林顿总统提名斯蒂芬·布雷耶接任。7月22日,金斯伯格“作为新近的家庭订户(至少是订户的配偶)”给我来信,谈到了她对我最近发表在《新共和》上的两篇文章的想法:一篇是关于布雷耶的,另一篇则与她的法学院导师杰拉尔德·冈瑟新撰写的一本勒恩德·汉德的传记有关。她写道:“杰里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老师,那以后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史蒂夫[28]则既善良又真实。”她接着又说:
汉德很善于用词,我并没有被他那些不怎么让人欣赏的品质分心,包括他不愿考虑让我(或其他任何女性)担任助理。从1959年到1961年,也就是我在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有时我下班比较早,晚上帕尔米耶里法官[29]开车送这位伟人回家时,我就会坐在后座上。我喜欢汉德的朗诵和演唱,尤其是他表演的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剧目[30]。杰里的书正如我所愿,是的,精彩至极。
我的歌剧新闻。7月17日,我们在格林德包恩庄园观看了《唐·乔瓦尼》的演出。[31]这个地方很美,管弦乐队和演唱者也是一流的。只是这部作品(病态的现代版)有失水准。
在信的末尾,她提到了最高法院最近刚作出裁决的两起案件,这两起案件让她尤感共鸣。第一起是伊巴涅斯诉佛罗里达商业和职业监管部案,在该案中,金斯伯格为最高法院的多数方撰写了意见,裁定佛罗里达州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西尔维娅·萨维尔·伊巴涅斯的权利。伊巴涅斯是一名律师和注册执业会计师,尽管她供职的机构没有取得那家落伍的官僚机构——佛罗里达州会计委员会的许可,但她宣称自己是一名注册执业会计师这一点是诚实的。伊巴涅斯让金斯伯格颇受触动,前者从中佛罗里达大学会计讲师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成功地在最高法院的这起案件中为自己作了辩护。伊巴涅斯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唱者,她曾在梵蒂冈和卡梅拉塔合唱团献唱,这一点可能也吸引了金斯伯格。4我很快就了解到,金斯伯格对女性的这些生活细节的关注正是她处理案件的特色,她始终聚焦于现实世界的挑战之上,这些挑战是试图界定自己生活道路的男性和女性个体都在面对的。
第二起案件是拉茨拉夫诉美国案,该案不但展现了金斯伯格对公民自由意志主义的敏感,也显示出她对于法律在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运作方式的关注。沃尔德马·拉茨拉夫欠下了16万美元的赌债,他企图用现金偿还其中的10万美元,因此被控违反了报告法。他声称自己并不知道法律要求他必须向财政部报告所有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因此不应为没有报告而担责。金斯伯格为5比4票的裁决撰写多数意见时对此表示赞同,她认为要证实拉茨拉夫“蓄意违反”报告法,政府必须证明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非法的,而且要有违法的特定故意[32]。代表四名持异议者撰写意见的布莱克门大法官则认为对法律的无知并不能为其辩护。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资深法官皮埃尔·勒瓦尔在给金斯伯格的信中也称赞了这一裁决,他说自己总是会告知陪审团,“蓄意”一词的意思是“出于不良目的而违背或无视法律”。他特别提到自己在前一年受理的一起涉及两姐妹的案件,这两姐妹是哥伦比亚公民,从事房屋清洁工作,生活比较贫困。在数个月的时间里,她们在姐夫那里寄存了总计12万美元的存款。姐妹俩作证说她们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非法的。勒瓦尔认为她们并无非法目的,因此判她们无罪。和金斯伯格一样,勒瓦尔关注的也是宪法裁决给人——那些努力维持着生计的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带来的实际影响。
1997年,《纽约时报杂志》邀我为最高法院的“自由主义新面孔”——金斯伯格大法官写一篇传略。我去信请她接受采访时,她委婉地表示了拒绝。她写道:“和斯佳丽一样,我明天再考虑吧。”[33]接着她又发来一张手写的便签:“亲爱的杰夫[34],回复《纽约时报杂志》,请不要做这次采访。看看文件袋里的东西。现在就直接拒绝吧,我会在2010年接受你的独家采访。多谢了。金斯伯格。”随附的蓝色文件袋里有一些写给记者琼·比什库皮奇和法学教授亨特·克拉克的信,信中拒绝了他们进行深度访谈的请求,理由就像金斯伯格在1995年对克拉克所说的那样:“我认为现在就把我当成传记的合适题材……还为时过早。这只是我开始这份奇妙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可以料想我笔下有很多重大的工作尚未出现……2003年或许可以考虑开始讲述我的生活。此外还存在超负荷的问题……我必须小心地节省时间,去完成法庭繁重的工作,同时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要写《纽约时报杂志》的这篇文章,金斯伯格也为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她给了我完成这篇文章开场所需要的权限,但又不至于要她来接受采访。她邀请我去她的办公室,让我随便参观,想看多久就看多久。到了约定的那一天,金斯伯格在简短地问候了我几句之后就直接消失了。以下是我对那次不同寻常的经历所作的记录。
发现只剩我一个人之后,我略带尴尬地查看了她的书架。有很多民事诉讼方面的书;但也有数量惊人的关于当代女权主义的通俗读物,包括黛博拉·坦纳的《朝9晚5谈话录》,以及安妮塔·希尔和艾玛·乔丹的《美国的种族、性别与权力》。还有一块专供普契尼[35]的圣地,上面贴着20世纪初的新艺术派海报。不久,金斯伯格大法官的秘书走了进来。她接到了大法官从车里打来的电话,说让我特别留意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她的女婿和年幼的外孙。大法官想让我知道,这就是她对未来的梦想。
我当时以为这句话不过是天伦之乐一类的陈词滥调;但后来我意识到,金斯伯格大法官可能是微妙地表达了自己对性别角色转变的看法。我想起她进入最高法院后不久,就像新晋大法官们传统上所做的那样,也在接受最高法院的通讯刊物《待审案件表》的采访时作了自我介绍。最高法院公共信息官托尼·豪斯问她,为什么她会同意给自己的一名法官助理戴维·波斯特安排弹性的日程。金斯伯格回答说,波斯特申请助理职位时,白天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这样他太太才能保住一份要求极高的经济学家的工作。“我想,‘这就是我梦中的世界该有的样子’,”金斯伯格激动地说,“当父亲在照顾孩子方面肩负起同等的责任时,女人才能真正获得解放。”5
《纽约时报杂志》的那篇传略有两个疏忽引发了关注。第一个疏忽与文中描述的我和金斯伯格大法官此前在华盛顿国家歌剧院的一次对话有关,当时正是莫扎特的一部作品《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演出的幕间休息时间。这部歌剧讲的是两个男人为他们的女友是否忠贞不渝打赌。他们乔装打扮,最终发现女人们并不忠诚。[36]为了增添女权主义色彩,导演建议让这两个女人无意中听到这场赌局,然后干脆假装不忠。我向金斯伯格大法官提到这不符合18世纪的性别双重标准,而且这在剧名的一个传统翻译中就有所反映:《永远不要相信一个女人》(Never Trust a Woman)。金斯伯格回应说,意大利语的剧名用的是第三人称复数。她认为翻译成《他们都如此》(They Are All Like That)会更加准确。因此没有理由认为莫扎特及其词作者洛伦佐·达彭特[37]都认为女人比男人更值得或更不值得信任。
尽管将金斯伯格对莫扎特的热爱与她对性别平等的承诺相联结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尝试,但事实证明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文章发表后,金斯伯格从全国各地的音乐爱好者寄给她的大量信件中挑了一封寄给我,信中提到意大利语中“tutte”(所有女人)的词性是阴性,不同于阳性的“tutti”(所有男人)。就像哈佛大学的一位音乐学家给金斯伯格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与英语不同,意大利语中第三人称复数的末尾是有性别区分的……所以更准确的翻译应该就是‘女人皆如此’。”她幽默地称这封信是“我最好的一件意大利藏品”。
第二个疏忽完全是我的责任。民族主义保守派评论员帕特·布坎南[38]在1996年总统竞选期间曾抨击金斯伯格是一名司法能动主义者[39],而在同年3月4日,金斯伯格给我和一位法学教授——也是她的前同事发来的回复都是:“我很庆幸自己这么‘保守’,你肯定会对帕特·布坎南把我放进他那份‘黑’名单的前列感到好笑。我知道这都要归功于金斯伯格这个姓氏。不过我还是很荣幸能加入到这些好伙伴之中。”
在这篇文章中,我指出布坎南是本末倒置:从金斯伯格投票推翻的少量联邦法律来看,她就是最高法院里最克制的大法官。由于缺乏想象力,我在文中预测金斯伯格还将继续把自己界定为一名主张司法最低限度主义[40]的大法官,一名司法祭司,而不是一名司法先知:“作为一名大法官,金斯伯格的这些品质很有可能使她永远都无法成为一名有远见的领导者——她的最低限度主义、她的法理学和个人克制,以及她对于避免宪法冲突而非加剧这类冲突的强调——可能会让她在这所充满分歧的最高法院中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首席大法官。”
事实证明我的预测是短视的。有机会任命下一任首席大法官的不是克林顿,而是小布什,这是布什诉戈尔案的结果,金斯伯格对其裁决表示遗憾。在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41]和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42]被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43]和塞缪尔·阿利托大法官[44]取代之后,最高法院开始右转;当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大法官[45]于2010年退休时,金斯伯格成了资深的自由派大法官。在担当起这一新角色之后,她即将转型为那个“声名狼藉的RBG[46]”。和好友斯卡利亚大法官一样,她也成了一位富有远见的异见派领袖。
当金斯伯格在1993年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她曾被视为法官中的法官,一位司法最低限度主义者,因其对司法职能的克制态度而广受保守派的称颂(同时也受到了一些自由派的质疑)。在接下来的26年里,她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激励人心的美国偶像之一,而且如今也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宪法改革人物之一。作为一名法律记者、法学教授,以及费城国家宪法中心的新任负责人,我有幸观察到了这一转变,同时也在一系列的公开访谈和对话中向她询问了这一转变。这些访谈有很多是当众进行的。在接下来的对话中,金斯伯格始终不改本色——坦率、镇定、凝神、专心倾听,在回忆事实、法律论点、案件及其背后的人间故事的细节时则让人大感惊讶。最重要的是,她总是深沉睿智,三思而后言(她所有的朋友和法官助理都学会了在问答之间的长时间停顿中安静地坐着,因为她正在这停顿之中不断整理自己的思绪)。对于她在担任大法官期间发生了转变的说法,她并不同意,并坚称最高法院已变得更加保守,而她在最高法院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在成为资深的自由派大法官之后,她对某些多数意见和很多异议的分派都负有责任。尽管如此,20世纪70年代的“火热的女权主义者”(她自己是这样说的)和杰出战略家,改变了我们对性别平等之宪法理解的金斯伯格,已转变为一名20世纪80、90年代克制的司法最低限度主义者,决意在一般情况下让立法机构和舆论演进而非法院来推动社会变革。最近十年,她又结合了两样特质:一方面是她在辩护律师生涯里对自由平等的战略远见和奋斗激情,另一方面则是一种有原则的决心,那就是在民选议员的选择抵触宪法时,要捍卫法院在审查其选择方面有限却关键的作用。
以下的谈话记录经过了压缩和重新整理,以便按主题来组织,并由金斯伯格大法官亲手编辑,以确保内容的清晰和准确,不过大法官的每一句振奋人心的话都完全出自她本人。
注解:
[1] 比林斯·勒恩德·汉德,美国法官、法学家,他的话曾被法学学者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量引用,著有《自由的精神》等。(本书脚注如无特别标注即为译注。)
[2] 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奥地利裔美国律师、教授、法学家,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939—1962),提倡司法克制。
[3] 亚历山大·莫迪凯·比克尔,美国宪法专家、法学教授。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宪法评论家之一,主张司法克制。
[4] 安东尼·格雷戈里·斯卡利亚,美国律师、法学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986—2016)。他曾在美国法律界掀起了一场原旨主义和文本主义的运动,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
[5] 此处的总统即比尔·克林顿。
[6]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讲述了一段西方人想象中的中国传奇故事。
[7] 卡拉夫(Calaf)是剧中的鞑靼王子,在答对公主图兰朵的三个谜语并历经考验后成功迎娶了公主。《今夜无人入眠》是该剧中最著名的一段咏叹调。
[8] 戴维·哈克特·苏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990—2009),他是由共和党总统老布什在仓促间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
[9] 约翰·马歇尔·哈伦二世,美国法学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955—1971),通常被视为保守派。
[10] 即厄尔·沃伦担任美国首席大法官的时期(1953—1969)。
[11] 司法克制认为法院应是寻求救济的最后手段,与司法能动主义相对。
[12] 杰里·冈瑟即杰拉尔德·冈瑟,美国德裔宪法学者,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曾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杰里(Gerry)是其昵称。
[13] 韦尔什诉美国案(下文中亦称“韦尔什案”),1964年,美国青年艾略特·韦尔什以违背自己的良心为由拒服兵役,后由此获刑。1970年,最高法院接到上诉后作出了支持韦尔什的裁决,布莱克大法官的裁决意见认为因良知而拒服兵役者的身份可适用于“那些因根深蒂固的道德、伦理或宗教信仰而在良心上不愿让自己成为战争工具的人”,并从此扩展了因信仰而免服兵役的范围。
[14] 如果判决投票中多数方的某些大法官同意判决结论,但不同意论证的理由,或者想就具体论据发表个人观点,就可以撰写协同意见加以说明。
[15] 下文中亦称“莫里茨案”。——编注
[16] 依亲父母(dependent parents),需要子女赡养的父母。
[17] 莱奥什·亚纳切克,捷克作曲家。
[18] 拜伦·雷蒙德·怀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962—1993),曾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
[19] 下文中亦称“罗伊案”。——编注
[20] 戈耳狄俄斯之结(Gordian knot),传说中难以解开的绳结,解开者将成为亚细亚之王,后被亚历山大大帝一剑斩断。
[21] 斯蒂芬·杰拉尔德·布雷耶,美国律师、法官,1994年被克林顿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自由派。
[22] 吉尔伯特·斯特劳德·梅里特,美国律师、法学家,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23] 布鲁斯·爱德华·巴比特,美国律师、政治家,1978年至1987年任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1993年至2001年任美国内政部长。
[24] 瑟古德·马歇尔,第一位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967—1991)的非洲裔美国人,一生致力于种族平等事业。
[25] 《安娜·博莱纳》是意大利作曲家多尼采蒂以都铎王朝为背景创作的三部歌剧之一,讲述了英王亨利八世与安娜·博莱纳和珍·西摩这两位王后之间的情感纠葛。
[26] 塞缪尔·巴伯,美国作曲家。
[27] 哈里·安德鲁·布莱克门,美国律师、法学家,1970年至1994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他是罗伊诉韦德案的意见撰写者,该意见废止了州和联邦政府的堕胎限制令。
[28] 史蒂夫,斯蒂芬的昵称。
[29] 埃德蒙·路易斯·帕尔米耶里,美国纽约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金斯伯格曾担任他的助理。
[30] 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剧目,即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吉尔伯特和作曲家阿瑟·沙利文合作的剧目。
[31] 《唐·乔瓦尼》,莫扎特歌剧作品,讲述西班牙贵族唐·乔瓦尼在仆人莱波雷洛的帮助下四处惹是生非,诱惑各国妇女,最终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格林德包恩庄园为英国歌剧艺术重镇,每年度举办格林德包恩歌剧节。——译注加编注
[32] 特定故意,又译确定故意,指实施一种会遭指控的明确违法行为的意图。
[33] 出自小说《飘》结尾处斯佳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所说的一句话。
[34] 杰弗里的昵称。——编注
[35] 贾科莫·普契尼,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代表作有《波希米亚人》《托斯卡》和《蝴蝶夫人》等。
[36] 在原作中,这两个男人谎称要到前线作战,实则转身就伪装成异国绅士,向彼此的未婚妻示爱,以测试她们对爱情的忠诚度。
[37] 洛伦佐·达彭特,意大利裔美国人,18世纪及19世纪著名歌剧填词家、诗人。他因和作曲家莫扎特合作完成了三部著名意大利语歌剧而知名,包括《费加罗的婚礼》《唐·乔瓦尼》和《女人皆如此》。
[38] 帕特·J.布坎南,美国保守派政治评论家、政治家。布坎南曾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杰拉尔德·福特和罗纳德·里根的高级顾问。他在1992年、1996年和1999年曾谋求提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39] 司法能动主义主张法院在释宪时无须考虑立法者的立法意图,倾向于弱化遵循先例的原则。
[40] 司法最低限度主义认为稳定的联邦宪法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强调司法解释对先例的尊重,主张给出的司法解释应当在较窄的范围内适用,且应与先例的解释之间保持较小的差异。——译注加编注
[41] 威廉·哈布斯·伦奎斯特,美国律师、法官,曾任美国首席大法官(1986—2005),保守派,晚年立场趋于温和。
[42] 桑德拉·戴·奥康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1981—2006),温和保守派。
[43] 约翰·格洛弗·罗伯茨,2005年就任第17任美国首席大法官,保守派。
[44] 塞缪尔·安东尼·阿利托,2006年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坚定的保守派。
[45] 约翰·保罗·史蒂文斯,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1975—2010),温和自由派。
[46] RBG是金斯伯格名字的三个首字母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