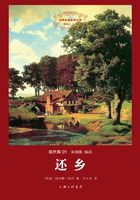
第14章 爱情让精明汉用计
老派红土贩现在不常看见了。自从威塞克斯通了火车以后,当地羊倌赶绵羊赴庙会时大量使用的那种鲜明颜料,已另有来路,农民不必依靠这些红魔[76]一般的行商了。即使有一些人保留下来,从前那种特有的诗意生活也渐渐不复存在了:当初做这种营生的,都定期到挖红土的土坑运原料,除非天寒地冻,他们成年累月在野外露营,在成百上千的农场游历,生活虽然漂泊不定,却能随时随地掏出鼓鼓的腰包而确保体面。
红土无论落到什么东西上面,都要撒播那鲜明的颜色;无论是谁,只要接触半个钟头,就一定要像该隐[77]似的,身上烙上明白醒目的记号。小孩子初见红土贩,就是毕生难忘的大事变。在幼小的心灵里,这样一个浑身血红的人物,就是他们从想象力启动那一天起所做的一切噩梦的升华。祖祖辈辈,威塞克斯的母亲们用来吓唬小孩的套话,就是“红土贩捉你来了!”本世纪初,他一度被拿破仑取而代之,但时过境迁,拿破仑这个人物陈腐失效以后,从前那句老话又恢复了原先的突出地位。不过现在,红土贩也追随拿破仑沦入了过气鬼怪的国度,已有了近代的发明取而代之。
红土贩的生活和吉卜赛人一样,却都看不起吉卜赛人。他们的生意和编筐编席的手艺人差不多一样兴隆,但和那些人却没有来往。他们的出身、教养比牛羊贩子要好,但牛羊贩子在路上和他们频频相逢的时候,却只对他们点头致意。他们的货物比货郎沿街叫卖的东西值钱,但是货郎却不以为然,看见他们的大车目不斜视地走过。他们的颜色看上去非常不自然,旋转木马的老板和展览蜡像的人,相比之下倒成了绅士;但他们却认为这种人身份低下,不肯接近。红土贩不断地出现在路上各色行人之中,却和那些人不搭界。那种营生本来就可能孤立他们,而人们看到的他们,也往往处于隔绝状态。
人们有时候说,红土贩都是罪犯,自己行为不端,却让别人顶了罪去受苦:虽然逃过了法律的制裁,却逃不过良心的谴责,所以从事这种营生,终身忏悔。要不然,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呢?在本个案中,这个问题倒切中了要害。当天下午走进埃格敦荒原的红土贩,就是大材小用而形成怪样基底的一例,本来干此行,丑陋的根基也能顶用的。这位红土贩唯一令人生畏的地方在于全身赤色。要是洗脱去那一点,他就是乡下男人里面一个常见的可爱典型。目光敏锐的人倒会觉得,一定是他对原来的身份不感兴趣,所以才把它放弃了(部分属实)。并且看过他以后,人们一定会试作一猜,他的性格主体是脾气柔和,才思敏捷之极,却不设城府。
他补着袜子,心里有事,脸就绷得紧紧的。后来表情温和下来,那天下午他在马路上赶车时的伤感柔情又出现了。不久,他手里就停住了针,把袜子放下,站起来,从篷车角落里的钩子上取下一个皮袋来。皮袋里装有许多东西,还有一个牛皮纸包。纸包的折痕都磨损得像铰链一般,可以断定,纸包一定是小心打开又包起许多许多次了。他在车里唯一的坐具,挤牛奶用的三腿小凳上坐下,烛光下把纸包端详了一会儿,才从里面拿出一封旧信展开。信上的字本来写在白纸上,由于处境特殊却染上了淡红色,黑色的笔画就好比冬天树篱的枝桠,衬托在红彤彤的夕阳里。信的日期是两年以前,落款是“托马辛·约布赖特”。信上写道——
亲爱的迪格利·维恩:
那天我从旁德克罗斯回家,你追上来向我提出了那个问题。我听了惊惶失措,恐怕当时没能让你确切了解我的意思。当然,我阿姨要是没来接我,我当场就可以把话说清楚的,但当时没有机会谈嘛。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忐忑不安,虽然你知道我不想惹你难过,但恐怕非惹你难过不可了,现在要把那时好像说过的话收回去了。迪格利,我不能嫁你,不能让你拿我当心上人看待。实在不行啊,迪格利。希望你听了之后不要介怀,心里不要痛苦。想到你会难过,我很悲伤,因为我很喜欢你;在我心里,除了表兄克林以外,就是你了。我们不能结婚的原因很多,一封短信难以说完。你跟着我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你会向我提那件事,因为我向来不把你当作情人。你不能因为你说话时我笑而骂我;你以为我笑你傻,那就错了。我是因为那个想法太奇怪才笑的,并不是笑你。我不让你向我求爱,个人的主要理由是,我心里并没有感觉,那种答应和你好,打算做你的太太的女人应有的感觉。并不是像你想到的那样,我另有意中人;因为我并没鼓励过任何人来追,而且一辈子都没鼓励过人。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我阿姨。就算我愿意嫁你,她也不会同意的。她固然很喜欢你,但她却要我看得比小牛奶场主高一点,嫁一个专业人员。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秉笔直书,心里就存了芥蒂;不过我觉得你会设法再和我见面的,咱们两个还是不见面的好。我将永远把你看作是好人,关心你的幸福。我让简·奥查德的小女仆把这封信带给你。
你的忠实朋友,托马辛·约布赖特
牛奶场主维恩先生收
这封信是多年前一个秋天的早上送来的,红土贩再没和托马辛见过面,直到今天。期间,他改变身份,干起了卖红土营生,比原来离她越发远了;不过他的实际境遇仍很宽裕。其实,考虑到他的支出只占收入的四分之一,他算是富翁了。
求婚遭拒,就和无窝可归的蜜蜂一样,自然要去游荡了;维恩玩世不恭之余所从事的生意,在许多方面都是投其所好。但是漂泊间旧情难忘,他常来埃格敦方向,只是始终没冒昧造访吸引他到那里的她。能待在托马辛住的荒原上,靠近她,而不被她看见,在他看来,就是他剩下的唯一带来快乐的小母羊[78]了。
接着是那天发生的事。红土贩仍一往情深,没想到紧要关头碰巧能帮上她的忙,便兴奋不已,他随之立下誓愿,要为她的事情主动效劳,而不再像以前那样,敬而远之,独自叹息。事到如今,他对怀尔狄夫是否用心老实,是不可能不生疑窦的。不过,托马辛的希望显然集中在怀尔狄夫身上,维恩也就把自己的遗憾放下,决定帮助托马辛,让她以自己选定的方式幸福美满。这一种方式当然是天底下最痛苦的了,令他感到很尴尬;但是红土贩的爱是无私奉献的爱。
他维护托马辛的利益而采取的第一个主动措施,是在第二天晚上约莫七点钟的时候,行动根据的是从那悲伤小孩得到的消息。听说游苔莎和怀尔狄夫在秘密相会,他就立刻断定,怀尔狄夫对于婚事粗心大意,她是某种缘由。他并没想到,游苔莎向情人示爱的信号,本是被弃的美人听见外公带回的情报后产生的柔情效应。他本能地把游苔莎看成是破坏托马辛幸福的主谋,却没想到,她本是旧情复燃性质的障碍。
白天里,他心急火燎地打听托马辛的病情,但没有去做不速之客,尤其是在现在这种难熬的时候。他主要在忙着搬家,车马和货物全都移到了原落脚点的东面;在那块荒原地,他精心选择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点,看他的意思,好像这次要在那里长久驻扎。接着,他步行照原路返回一段,天色已经黑下来了,便往左转,来到离雨冢不到二十码的一个土坑边上,站在冬青树丛后面。
他本打算在那儿看约会的,却一无所获。那天晚上,除了他自己,并没人走近那地方。
红土贩白费了气力,却并不气馁。他设身处地,体会坦塔罗斯[79]的遭遇,仿佛觉得,一定数量的失望是心愿实现的天然序曲,没有序曲,反而要引起警觉了。
第二天晚上,他又在老时间老地点出现,但期待中的幽会者游苔莎和怀尔狄夫并未出现。
后来,他接连四个晚上又照样去等,都没成功。但又是一个晚上,离他们前次相会刚好隔一个礼拜,他却看见一个女子模样的人,在山脊上飘然前行,同时一个青年的影子从山谷里走上山来。两人在围绕雨冢的小壕沟里见了面,壕沟是古代不列颠人掘土造墓时挖的。
红土贩怀疑,这下又要对托马辛不利了,不免急火攻心,便忽地心生一计。他迅速出了树丛,匍匐前进,尽量爬得靠近些,但在可以不被发觉的地方,却发现由于横向风的原故,那对幽会情人说的话听不见。
荒原上,许多地方都摊满了大块的泥炭,他的身旁,泥炭有的侧立,有的翻转躺着,待费尔韦在入冬以前运走。红土贩趴到地上,拖过两块泥炭,一块盖住头部和肩膀,一块盖住背脊和两腿。这样就是大白天,也很难被看见;泥炭的石南一面朝上,贴在身上,看着和长在地上一样。于是,他又向前爬,背上的泥炭也跟着爬。天色已是黄昏,就是没有东西遮盖,大概也不会被发现,现在加上掩护,更像钻地道一般。就这样,他爬到了离他们两个很近的地方。
“要跟我商量这件事?”游苔莎圆润的声音急匆匆的,传到他的耳朵里,“跟我商量?说这样的话就是侮辱我呀,我再也受不了了!”说到这里,她哭了起来,“我已经爱上了你,并且也已经表白爱你,可心里后悔啊;你居然还能跑到我这儿,冷冰冰地说,要跟我商量娶托马辛是不是更好一些。是更好——当然更好。娶她就是了:她的社会地位比我更接近你!”
“好啦,好啦,那很好,”怀尔狄夫不容分说,“不过我们要面对现实。事情弄到这步田地,不管怎么怪我都行,反正托马辛现在的处境,比你要糟得多。我不过直言相告,我是进退两难啊。”
“你不该对我说的!你肯定清楚,这样做只会折磨我嘛?戴蒙,你的所作所为可不好,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呢。凭我这样曾经心高万丈的小姐,看上你是多么大的善意,你却不珍惜这种礼遇。不过,这都是托马辛的错,是她把你抢走的,所以现在吃苦是活该。她现时在哪儿待着?我可不在乎的,连我自己待在什么地方还都不在乎呢。啊,要是我死了,那她该多么开心!我问你,她在什么地方?”
“托马辛在她阿姨家,躲在卧室里,谁也不见。”怀尔狄夫不动声色地说。
“就是现在,我觉得你也并不怎么关心她,”游苔莎忽然快乐起来说,“不然的话,你谈起她来就不会这样冷淡了。你对她谈起我来,也这样冷淡吗?啊,我想是吧!你当初为什么把我甩了?我想我是永远也不会饶恕你的,只有一种情况才例外:每次把我甩了以后,你就回心转意,觉得对不起我。”
“我从来也没想把你甩了啊。”
“那样我也并不感激你。一切顺顺利利的,我反而讨厌。其实,我倒喜欢你时不时把我甩开一下。情人太老实,爱情就成了最沉闷的东西了。哎哟,话说出来难听,不过这是真话!”她纵情一笑,“一想到那种爱情,我马上就觉得没情绪。不要净给我温顺的爱情,否则就请走开好啦!”
“但愿托马辛不是一个极好的小妇人。那样,我就可以对你忠心耿耿,不至于伤害好人了,”怀尔狄夫说,“不管怎么说,我是罪人,我连你们两位的小指头都配不上。”
“不过,你千万不要出于正义感而为她牺牲自己,”游苔莎急忙回答说,“如果你并不爱她,那就不要再理她,长远看这样最仁慈。那永远是最佳办法。嘿,我这样说话未免有失女人的身份。你离开我以后,我老在为对你说了不该说的话,生自己的气。”
怀尔狄夫并没回答,在石南丛中间踱了一两步。无言之际,只听上风头不远处传来了一棵削去树梢的山楂树的声响,微风在那坚强的硬枝中间刮过,仿佛筛子过滤一般,听起来就像黑夜正咬着牙唱挽歌。
游苔莎不无伤感地继续说:“上次见面以后,我曾想到过一二,你也许并不是因为爱我才不跟她结婚。告诉我吧,戴蒙,我会挺住的。我跟这件事就毫无关系?”
“你非逼我说吗?”
“是的,我一定要弄个明白。我觉得我对自己的能耐过于自信了。”
“好吧,直接的原因是许可证不能在那地方用,没等到我去调换,她就跑了。直到那时,你跟这件事并无瓜葛。后来,她阿姨对我说话的口气,我根本不喜欢。”
“对啦,对啦,我无关紧要——无关紧要啊。你不过跟我玩玩而已。天哪,我游苔莎·维尔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把你看得这样高!”
“没有的话,不必这样冲动嘛。……游苔莎,记得夏天里,天凉快下去以后,咱俩在这灌木丛中徜徉,山影把咱们隐蔽在山坳里,简直隐身不见了!”
游苔莎仍闷闷不语,待了一会儿才说:“记得,那时还因为你居然敢仰望我而取笑你哪!但是后来,你让我为此而大受其罪。”
“不错,你对我够凶的了,后来我觉得我找到了比你更漂亮的。游苔莎,找到这样的人,真是福气。”
“你现在还以为你找到了更漂亮的人吗?”
“有时候是那样,有时候又不是。天平秤盘不偏不倚,只要一根羽毛,就可以倾斜。”
“不过,你对我跟你见面不见面,到底在乎不在乎?”游苔莎慢慢地问。
“多少也在乎一点,不至于坐立不安,”男青年懒洋洋地说,“不在乎,一切都过去了。原以为只有一朵花,现在却找到了两朵。也许还有三朵、四朵,无数朵,都跟第一朵一样好。……我的命运真怪。谁想得到,这一切会让我碰上呢。”
游苔莎按捺住火气,是爱火是怒火都有可能,她单刀直入:“你现在还爱不爱我?”
“谁能说得清?”
“告诉我,我一定要弄清楚的!”
“也爱,也不爱,”他调皮地说,“也就是说,我要看时令和季节的。你一下子太高,一下子太懒,一下子太忧郁,一下子又太深沉,一下子我不知道怎么样——只知道,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我世上的唯一了,亲爱的。不过你是可爱的小姐,值得结识,和你相会还很不错,我敢说还是一样地甜美——差不多一样。”
游苔莎不言语,她背对他,然后收起威力说:“我要散一散步,就走这边。”
“哦,不跟着你,就更无聊啊。”
“尽管你喜怒无常,变化多端,你也知道不得不跟着的,”她挑衅地答道,“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怎么努力,尽可能把我甩开——反正你永远忘不了我。你要爱我一辈子的。你会急着娶我的!”
“不错,是会那样!”怀尔狄夫说,“游苔莎,我时不时有一些怪念头,现在又来啦。你依然很恨这荒原,这我知道。”
“是的,”游苔莎声音低沉地说,“这是我背的十字架,我的耻辱,总有一天会要了我的命!”
“我也痛恨荒原,”怀尔狄夫说,“你听四周刮的风有多凄凉!”
游苔莎并没有回答。那风声确实是庄严悲凉,无孔不入。混响的音调如泣如诉,作用于他们的感官,附近一带的景物,也就可以用耳朵看到。昏暗的景物还之以音画:长石南的地带从哪里起,到哪里止;荆豆棘在哪个地方长得又高又壮,哪儿新近割过;杉树丛长在哪一方向;长冬青的坑谷离开多远,都可以听出来。所有这些不同的特征,都各有各的声音和腔调,正如各有各的形状和颜色一样。
“上帝呀,太孤寂了!”怀尔狄夫接着说,“山谷和云雾风景如画,对于咱们这样眼里一无所有的人算得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呆在这儿?一块去美国吗?我在威斯康辛州有亲戚。”
“这得考虑考虑。”
“人要不是小鸟,也不是风景画家,在这儿好像无法过得好。怎么样?”
“给我点时间,”她拉着他的手温柔地说,“美国太远了。你和我一块走一走好吗?”
她说完这句话,就离开了古冢的基座,怀尔狄夫跟在后面,红土贩就再也听不见了。
他把泥炭掀到一旁,站起身来。夜空衬托出游苔莎和怀尔狄夫的黑影,慢慢降下去,消失了。他俩好像是蛞蝓般懒散的荒原的一对触角,从头上伸出来,现在又缩了回去。
红土贩尽管年方二十四岁,身材苗条,从这个山谷翻到车马所在的山谷时,步履却并不轻快。他心烦意乱,痛苦不堪。一路上,嘴边吹过的微风,都捎带着他扬言报复的腔调。
他进了篷车,里面生着火。他连蜡烛都没点,一下就坐在那三脚凳上,掂量着刚才所见所闻的种种,那可涉及他仍旧爱慕的人哪。他发出一种声音,既非叹息,又非啜泣,却比叹息啜泣更显出心烦意乱的情绪。
“我的托马辛啊,”他心事重重地低声说,“这可怎么办?对,我去见一见那个游苔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