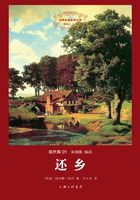
第12章 夜的女王
游苔莎·维尔本是做天神的料;稍稍打点一下,就能在奥林匹斯山[54]上混得很好。她拥有做模范女神的那种激情和本能,也就是说,不大能做好模范的女人。若有可能把地球和人类暂时都交给她掌控,让她随心所欲地操纵纺纱杆、纺锤和剪刀[55],则世上很少会有人察觉治权的变动。我们现在有命运不公,有宠爱集于一身,屈辱不离某处,公道之外先实施宽大,永远进退两难,风云难测,旦夕祸福,即使治权易手,遭际也会一模一样。
她胳膊腿脚丰满,比较富态,面色既非红润,亦非苍白,肌肤就像浮云那样柔软。一看到她的头发,就会想象,整个寒冬积累的阴沉昏暗,都不足以形成那样的乌云笼罩。头发覆盖在她的前额上,好像夜色抹去了西方的晚霞。
她的神经贯通到这些长发的末梢,轻轻抚摩,就能缓和脾气。头发一梳,就立刻沉静起来,好像斯芬克斯[56]一样神妙莫测。在埃格敦荒原的坡崖下走过时,厚密的飘发有时会被荆豆的带刺枝条挂住几绺,枝条就成了某种发刷,而她会回身几步,故意贴着枝条再次经过。
她有非基督教徒的眼睛,富于夜的神秘。厚眼皮和长睫毛半遮着,妨碍了眼波的往复转动;她的下眼皮比英国一般妇女要厚得多。所以她能沉湎于遐想,却看不出在出神:有人认为,她不闭眼睛也能睡觉。假定世间男女的灵魂都是肉眼可见的实体,就能想象游苔莎的灵魂是火焰的颜色。她灵魂里发出的火花,进入她那漆黑的瞳孔里,也给人同样的印象。
她的嘴与其说为说话而生,不如说为颤动而生;与其说为颤动而生,不如说为接吻而生。也许有人还要补充一句,与其说为接吻而生,不如说为撇嘴而生。侧面看,其双唇抿合的曲线,几乎具有几何学的精确性,形成设计艺术上叫做表反曲线或者葱形拱的S形曲线。在阴森肃杀的埃格敦荒原上面,居然能见到这么柔和的唇形,真是奇观。一看便知,这样的嘴唇决不是从石勒苏益格[57]侵入英国的那一群撒克逊海盗遗传下来的,因为他们的嘴巴闭拢时,都像一个松饼分两片合拢一样。有人想象,这样的嘴唇曲线,多半埋在南方[58]地下,藏在遭到冷落的大理石雕塑残像上面。她的双唇曲线非常优美,虽然很厚实,但两个嘴角和铁矛尖一样轮廓分明。只有在她一下子抑郁起来的时候,嘴角的锋芒才会钝化;她年纪轻轻,就过于习惯抑郁,那本是感情的阴暗面之一。
她的风姿,让人忆及波旁蔷薇、红宝石和热带的午夜,等等;她的情绪,使人想起食落拓枣者[59]和《阿达莉》[60]里的进行曲;她的动作,就是海潮的涨落;她的声音,就是悠扬的中提琴。在幽暗的光线里,头发稍微梳理一下,她的外形就可以代表高级女神。脑后一弯新月,头上一顶旧盔,额上勒着散落的露珠作为王冠,凭这些饰物足以让她分别表现阿耳忒弥斯、雅典娜、赫拉[61],她和古典天神的相似度,不逊于许多尊贵的油画里那些栩栩如生的女神。
然而天神的威严、爱情、愤怒、热情,在下界埃格敦,未免有点浪费。她的力量有限;她自己意识到这一局限,发育就产生了偏向。埃格敦就是她的冥土[62],自从来到这儿,那种黑暗的情调,她已经吸收了不少,虽然心里永远格格不入。她的外貌和这种难以抑止的叛逆性十分调和;她的美丽有一种幽黑的光辉,那是她内心被悲伤郁结的热情的真面目。她的眉宇间透出阴曹地府式的正宗尊严,既非矫揉造作,也无拘束的痕迹,因为长年累月它已在她身上生根。
她额上束着一条黑色天鹅绒细发带,挽住那幽黑茂密的头发,参差不齐的乌云盖在额上,给那种威仪平添一种尊贵。里希特尔[63]说过:“除了一条横束额上的细带,没有东西能更好地装饰美丽的脸庞了。”街坊里的姑娘们,有的用彩带把头发束拢,还在别处佩金戴银;但是若有人劝游苔莎·维尔扎彩带,佩金戴银,她就一笑走开。
这样一个女郎为什么住在埃格敦荒原上呢?她出生于当时那个时髦的海滨胜地蓓蕾嘴。她父亲是希腊科菲欧特人,一个很好的乐师,在驻扎蓓蕾嘴的一个团里当军乐队指挥。当时他未来的妻子跟着父亲,一位出身高贵的老舰长,是来蓓蕾嘴旅行的。夫妻俩的相遇、结合,很难说令老人称心,乐队指挥钱袋空空如也,职业也微不足道。不过,这位乐师却尽力而为,不但改姓太太的姓,在英国定居,而且对孩子的教育很费神,费用则由外公出。作为城里的主要乐师,日子倒也过得红火;不过她母亲一死,他就潦倒起来,还酗酒,最后也死了。姑娘就由外公照看。老舰长遇险失事,断了三根肋骨,从此就搬到埃格敦这个通气的山岗住下。老人喜欢上这个地方有两条理由:那所房子几乎不花钱就能得手,房门前能眺望到天边一片蓝色,夹在群山间,相传那就是英吉利海峡。游苔莎对于这一变动耿耿于怀,觉得跟流放一样,不过她不得不在那儿住。
于是,游苔莎的脑子里,新旧观念并存不悖,真是蒹葭倚玉树。她的透视视野里并没有中景,海滨广场上,阳光暖人的午后,军乐队、军官,围着打转的风流少年,种种浪漫回忆,和四周的茫茫荒原一比,就是辉煌的金字,刻在黑黑的招牌上面。在她身上,可以找到闪闪发光的海滨胜地和庄严肃穆的荒原随机撮合而产生的种种离奇效应。如今她看不到日常人生,就更加回味以往见过的东西。
她那种尊贵的仪态来自何方呢?父亲是费阿刻斯[64]岛人,尊贵从阿尔喀诺俄斯[65]家族辗转一脉相传?——或者外公有一位贵族表兄,尊贵来自菲查伦和德·维尔家族[66]?也许那只是天赋——自然法则的巧合。比如说,她离群索居,近年来就杜绝了沾染上不尊贵陋俗的机会。在荒原上与世隔绝,使得粗俗行为近乎不可能。让她庸俗化,还不如去让荒原马、蝙蝠、蛇虫百脚庸俗化容易呢。蓓蕾嘴那边的狭隘生活,倒很可能会使她卑贱不堪的。
没有王国掌管,没有臣民拥戴,却要母仪天下,看上去像女王,唯有做出领土尽失、子民离散的样子来;游苔莎就做得很成功。她虽然住的是老舰长的村舍,却能使人联想到她身居从未见过的庄园。也许是因为她常常游荡的地方,那些开阔的山冈,其规模超过了任何庄园。她的心情,正和周围那些地方的夏景一样,她身体力行了“群居的孤独”[67]这句话——表面上无所事事、空漠寂静,实际上却忙碌而充实。
把情人搞得为爱而痴狂——这就是她的最大愿望。对于她,爱情就是排遣岁月里那种揪心孤寂的唯一兴奋剂。她所渴求的,仿佛不是任何具体情人,而是叫做痴情的抽象观念。
有时,她会面带责备的样子;不过她发作的对象,与其说是普通人,不如说是想象中的某家伙,主要是命运;她隐约悟到,由于命运的作弄,爱情才只能降临滑翔的青春身上——她所得到的那点爱情才要与沙漏中的沙子同步流逝。想着想着,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刻毒意识,容易酝酿出惊世骇俗的草率行动,她准备尽可能因地制宜,攫取一年一月,一时一刻的激情。现在她没有爱情,虽歌唱,却不欢乐;虽拥有,却不得享受;虽风光照人,却不觉得意。孤独加深了她的欲望。在埃格敦荒原上,哪怕最最冷淡小气的亲吻,都标出荒年的高价;能够和她相配的嘴唇,到哪儿找去呢?
她和大多数的女人想法不同,觉得爱情的忠贞方面,为忠心而忠心没意思,倒是爱得难以自拔而忠心才有意思。爱情如炎炎烈火顷刻消灭,也胜过荧荧灯火延续多年。这一点,多数女人亲身经历后才知道,她却全凭先见之明;她已经神游了爱情的国度,点数了它的城楼,察看了它的殿宇;最后得出结论,爱情不过是苦涩的喜悦。然而,她渴望爱情,像在沙漠里的人,对于咸水也感激不尽。
她常常反复祷告,倒没有一定的时刻,而像那自然的信徒一样,什么时候想祷告就祷告。她的祷告内容总是发自内心,老是说:“啊!快把我的心灵从这可怕的抑郁和孤独中拯救出来吧,快快让伟大的爱情从天而降吧,否则我必死无疑了。”
她的最高英雄,是征服者威廉[68]、斯特拉福德伯爵[69]和拿破仑,她读书时学校课本《女子历史》中提到过这些人物。要是她做了母亲,会给儿子们取名叫扫罗或西西拉,而不是叫雅各或大卫[70],后两个人她不喜欢。她在学校里读到以色列和腓力斯人打仗,有好几次帮后者;并且纳闷,彼拉多[71]坦率公正,但是不是也英俊呢。故此,她这个姑娘思想颇激进;而且,考虑到她净跟思想落伍的人相处,她非常有独创性。她那种不服从社会成规的本能,就是这种思想的根源。对于假日,她的态度就像一匹马,自己被放出来吃草,却喜欢看同类在马路上拉车。别人劳作她得闲的时候,她才珍视自己的休息。因此,她恨礼拜天,那天大家都休息;她常常说,礼拜天早晚要断送了她。荒原人处于过礼拜的状态时,大家手插口袋,脚穿擦亮的靴子,连靴带都不系(过礼拜天的特别标记),在他们本周铲的泥炭和砍的柴堆中间闲逛,还挑剔地拿脚去踢那些东西,好像它们用途不明似的:看到这一切,她的心情便沉重得可怕。为了减轻讨厌礼拜天的腻烦,她就一面嘴里哼着乡下人礼拜六晚上唱的谣曲,一面翻箱倒柜地整理外公放旧地图和破烂的柜子。但是礼拜六晚上,她倒常常唱赞美诗;《圣经》也老是在平日念,这样就没有敷衍塞责的压迫感了。
像她这种人生观,一定程度上是所处环境对她天性产生的自然结果。身居荒原却不研究荒原的意义,就仿佛嫁给外国人却不学外语。荒原微妙的美,游苔莎并未领略,所能抓到的,仅仅是荒原的缥缈云雾。荒原的环境,能让知足的女人赋诗,能让受罪的女人虔心礼拜,能叫虔诚的女人写圣歌,甚至能叫轻佻的女人沉思,现在却叫桀骜不驯的女人忧郁不合群。
游苔莎对于辉煌莫名的婚姻,早已不复憧憬了,但她虽然感情奔放,却又不肯降格凑合,所以我们发现她处于离奇的孤立状态。放下了天神那种为所欲为的自尊自大,又没有获得平常人尽力而为的热情,这就表现出高贵豪迈的脾气,在抽象的道理上,本来倒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一种心境,失恋不失意嘛。不过,这尽管在哲理上说得通,对于家国社会却易构成危险。在这个世界里,有作为就是成家,家国社会就是由心和手所构成的婚姻家庭联合体,故这样的心境里险象环生。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位游苔莎——有时她也并非不可爱——正抵达那个豁然开朗的阶段,她觉得天地间没有什么值得一做,既缺乏更好的对象,便将就着把怀尔狄夫理想化,以充实她闲暇无事的生活。怀尔狄夫所以能登堂入室,这是唯一的原因:她本人也不是不知道。有的时候,她的自尊心会抗拒对他的激情,甚至还渴望解套。但是要驱他出门,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一个更强的人现身。
除此而外,她情绪低落,烦闷而苦恼,所以老拿着外公的望远镜和外婆的沙漏,在荒原上漫步,消愁解闷;拿沙漏是因为她看着光阴渐渐过去的物象,从中攫取一种奇怪的乐趣。她不常用计谋,但一旦用起计谋来,她的策划颇像大将统筹全局的战略,而不是所谓妇道人家的小聪明。不过,她不肯直言不讳的时候,也会说像特尔斐[72]神谕那类模棱两可的话。在天堂里,她大概位居埃洛伊兹[73]和克娄巴特拉[74]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