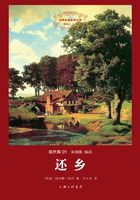
第11章 天空衬托的人影
埃格敦汇聚起来的人群都走了,点篝火处又回归了惯常的孤寂冷清。此刻,一个女子的影子,身上裹得严严实实,从荒原上点小篝火那里,靠近了雨冢。倘若红土贩还在观察,那他就可以认出来,她正是先前那样独特地站在冢上、见了生人来就消失的那个女人。她又爬上了古冢顶上的老地方,熄灭的火堆剩下的红炭,好像白日的尸体,眨着眼睛迎接她。她在那儿站定,身边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夜色,比起下面那片荒原的漆黑,还没有黑透,好像那是轻罪,和十恶不赦的重罪不同。
她身材颀长,身躯端正,一举一动符合淑女规范,这是眼下能看出来的全部特征:她的身体裹了按老式样斜对折的围巾,脑袋也包了大头巾;在此时此地,这样的保护不算多余。她将后背对着西北风,至于究竟为什么回避那个方向,是因为身在高处觉得寒风凛冽呢?还是因为她的兴趣在东南方呢?起先还看不出来。
再说,她为什么要这样纹丝不动地站立,充当四围这片荒原的枢纽呢?也同样不明白。她那异乎寻常的固守,那明显的凄凉孤独,那样对夜色不予理会,至少表明了她是无所畏惧的。这片原野环境恶劣,在古代曾使恺撒[42]每年在秋分之前,就急于摆脱它的阴沉昏暗,而这种状况至今并无改变;那种穷山恶水和阴沉天气,让南方来的旅行者把我们岛国比作荷马笔下的辛梅里安[43]土地,这一切只就外表来看,并不对女人友善。
要是说那个女人正在听风的声音,倒也合情合理;夜色渐深,风也大了起来,很令人注意。确实,那风好像是因景而设,而景物仿佛又是为那时刻而设。风中的部分音调十分特别,此处的风声,无法在他处听到。一阵紧似一阵的西北风,无休止地刮来,前仆后继,每一阵风刮过的时候,其行进的声音可转化作三种音调,其中有低音、中音和高音。整体的风势,在坑洼和山冈上下振荡,产生了齐鸣的套钟里那最低沉的声音。随后能听出来的,是冬青树嗡嗡的男中音。还有一种变细变弱了的声音,比这两种力度小而音调高,却使劲哼作沙哑音调,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那种特殊乡音。它比起另两种来,虽然更细弱,难以直接追踪,却远远要引人入胜。其中有荒原的所谓语言特色。离开荒原,这种声音天底下无缘听到,那个女人之所以神情紧张,而且连续不断地僵着,也许就是由于此些许理由。
十一月里寒风凄切,那个声音贯穿始终,很像九旬老翁的嗓子里残余的废歌曲。它是一种声嘶力竭的耳语,干枯嘶哑,如揉搓纸片。它从耳边拂过,听来非常清晰,听惯了的人,对于发声的细微来源,都能体会到,好像伸手可及。它是细小植物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些植物,并不是柄叶、干果,也不是棘刺、地衣、青苔。
它们是干枯的灰色石南花,夏天里盛开,本来花瓣柔嫩,呈紫色,现在叫米迦勒节[44]的寒雨冲刷得失色,又让十月的太阳晒成死皮了。花儿个体发出的声音非常低微,所以成百成千合起来的声音,刚刚能脱颖而出;坡上坡下亿万的花声,到了女人的耳边,也不过像懒洋洋的宣叙调,时起时伏。但今晚浮动的众声里,却几乎没有一个有能耐令人想到声音的来源。听者心里浮现漫山遍野的一片花,密密麻麻,体会到朔风把每个小喇叭抓住,钻进去,冲洗一遍,再跑出来,完全彻底,仿佛它跟火山口一样大似的。
“圣灵对它们的感应。”此话的意义不由人不注意;感情用事的听者,其拜物教情绪会止于一种更高境界的情绪。毕竟,这不是左边那片山坡的枯花,也不是右边那片山坡的死瓣,也不是前边那片山坡的死花在说话,而是另有一个单一的人格,通过每个花朵,异口同声地说话。
忽然,雨冢上又听到另一种声音,和这种夜的野性雄辩混合一气。它自然而然地变调,融会于别的声音之中,所以分辨不出其始终。悬崖峭壁、灌木丛、石南花打破了沉寂,最后那个女人也开口了;她的话不过是同一篇讲话中的一个词语。那一声,乘风发出,与风浑然一体,又随风飘去。
原来她发出的是一声长叹,显然是针对引她到冢上来的那件心事而发的。长叹里有痉挛性爆发的放任自流,好像女人容许自己发声时,大脑认可了它所无法调节的行动。其中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她并不是生活在无所用心、四肢不勤之中,而是在压抑状态之下苦熬。
低谷深处,客店窗口的微弱灯光经久不灭;再稍过片刻就能证明,她那一声叹息,正是为了此窗,或是窗户里的什么,而不是由于她自己的举动,也不涉及紧挨着的景物。她左手抬起,拿着折叠的望远镜。她把望远镜很快地打开,好像习以为常似的,举到眼前,对准店里的灯光。
她的脸部略有仰起,盖在头上的头巾也微微翻开了。一个面部的侧影,在黑沉沉阴云的衬托下依稀可见;好像是萨福[45]和西登斯夫人[46]从坟里爬了出来,其侧面容貌合为一体,既有两人的影子,却一个也不像。但这不过是表面现象,面部的轮廓只能少许供认人的性格;而面部的变化,才能表示彻底坦白。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要了解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所谓表情的作用,往往超过其余各部位加在一起的努力。因此,黑夜对那个女人,揭示不了什么,夜色笼罩,脸上的活动部分看不见。
她终于停止了窥探的姿态,合上望远镜,转到慢慢熄灭的余烬。那时,已经看不见光线往外四射了,偶尔来一阵异常强劲的风拂过上面,才能吹出一息红火,好像女孩子脸上的红晕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她俯首那一圈寂静的余火上,从木炭里面捡了一根红炭最大的,拿到她先前站立的地方。
她把那段木炭戳向地面,嘴吹着头上的红炭,直到把草皮微微照亮,照出一件小小的东西,原来是一个沙漏,其实她身上带着怀表的。她把炭火不住地吹,发现沙子都漏完了才罢。
“啊!”她好像吃了一惊似的说。
她吹出的炭火忽明忽暗,瞬间照亮了肌肤,但头部仍盖着头巾,仅仅看见一面脸颊和两片无与伦比的嘴唇。她把木炭扔掉,沙漏拿在手里,望远镜夹在腋下,上了路。
顺着山脊隐隐约约有一道脚踩的踪迹,小姐就走在上面。熟悉的人说那是一条路;偶然路过的游人,哪怕在白天,都会不知不觉跨过去;而在荒原游荡惯了的人,就是半夜都不会找不到它。夜色昏沉,连收费大道都难辨得出来,要走这样似路非路的小径,其秘诀在于培养足部感觉,它来自在人迹罕到的地方多年的夜游。对于这种地方上练过的人,就是穿着极厚的靴子也能觉察出来,没受蹂躏的野草,和小径上经过践踏的草茎,踩到脚下并不一样。
那位走这条小径的孤独者,对于枯死的石南花上奏出的风声丝毫未在意。她沿着沟壑行走,往前不远,有一群黑糊糊的动物正在吃草,看见她来都跑开了,她却连头都没回。原来是叫做荒原种的小野马,有二十几匹。丘壑起伏的埃格敦荒原,本是它们自由游荡的地方,不过数目太少,未能给荒僻的地方增色。
步行者当时对什么都不在意,从一件小事上就可看出她心不在焉。一丛黑莓刺把她的裙子勾住了,无法前进。她并没把刺藤扯开,继续赶路,却被刺藤拉住,索性老老实实地站住了。后来她开始摆脱纠缠,是身子反复回旋,才把刺藤松脱开的。原来她陷入了忧郁沉思。
她行走的方向是那个小而不灭的篝火,它曾经引起了雨冢上的人和山谷里怀尔狄夫的注意。微弱的光线,开始照到她的脸,过一会儿就能表明,篝火并不是点在平地上,而是点在一个两道土堤交接的凸角堡上。那土堤外面是一道壕沟,沟里基本上都干了,只有紧靠篝火那一段,还存着一大滩水,四周围满了石南和灯心草。只见那平静的水面上,倒映出篝火的影子来。
后面那两道连起来的土堤上并没有树篱,只有不成行的荆豆,沿着堤顶各处丛生,撑在茎干上面,活像插在木桩上的人头,高悬在城头上,勉强充当篱笆。只要火光一亮,就能照到一个白色桅杆,上面装着帆桁和索缆之类,高耸在乌云密布的夜空中。总而言之,那场景很像一座堡垒,且点起了烽火。
一个人也不见;但有一个白乎乎的东西,时不时从土堤后露出来,旋即不见了。那是一只小小的人手,正在一块一块地往火里添劈柴。不过从观察得知,那手却跟令伯沙撒[47]恐慌的那只手一样,是孤零零的。偶尔有炭火从堤上滚下去,“咝”的一声掉在水里。
水塘的一边有土块垒的台阶,要上土堤顶可以走那儿,女人拾级而上。土堤里面是荒废的马场,虽然有耕种过的迹象,现在石南和蕨草已悄悄侵入,重振旗鼓。再往里可以隐约辨出一座错落有致的住宅,连着庭园和裙房,后边有杉树林子。
那小姐——她轻快矫健地跳上堤,露出青春年少的体格——并没走下土堤往里面去,却顺着土堤,走到点篝火的拐角。那火焰能持久的唯一原因,现在明白了,燃料都是极坚实的木材,劈开了,锯成一段一段的——那是三三两两长在山坡上那些老山楂树疙疙瘩瘩的树干。只见土堤内的角落,还有一堆这样的劈柴没烧过。就在这个角落里,她看见有一个小孩仰起脸来。他时不时慢腾腾地往火里扔一块劈柴,那天晚上,他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桩事,脸上有些倦意。
“你来好极了,游苔莎小姐,”他如释重负,松了一口说,“我不喜欢一个人待着。”
“胡说八道。我走了不远,只是去散一散步。只离开了二十分钟的工夫。”
“好像不止二十分钟,”闷闷不乐的小孩嘟囔着说,“再说,走了好几次。”
“怎么,我本来想,你有篝火玩一定高兴。我给你点了篝火,难道不感激吗?”
“对呀,可是这儿没人和我一起玩。”
“看来我走了以后没人来过吧?”
“除了你外公,没有别人;他到门口找了你一回。我告诉他,你到山上走走,去看别人家的篝火去啦。”
“好孩子。”
“我听好像你外公又出来啦,小姐。”
一个老头从住宅那边,走到火光所及的远处。他就是那天下午在路上追上了红土贩的那个人。他眼巴巴地看着站在土堤上的姑娘,张嘴露出一口整齐完全的牙齿,好像帕罗斯[48]大理石一样洁白。
“游苔莎,什么时候进屋哪?”老头问,“差不多该睡觉了。我已经回家两个钟头啦,累坏了。你未免有些小孩子气,在外头弄篝火这么久,还浪费了那样的柴。我那些宝贵的山楂根儿,都是最难得的好劈柴,我特地留着过圣诞节用的,现在差不多都让你给烧光啦!”
“我答应了强尼点篝火,这下他还不愿意熄灭呢,”游苔莎说,那态度一下子就表露出,她在这儿是说一不二的女王,“您进去睡吧,外公,我很快就来。你喜欢这个篝火,是不是,强尼?”
那孩子疑惑地抬头看着她,小声说:“我不想再玩了呀。”
外公已经转身走了,并没有听见小孩的回答。白发老人刚消失,她就怄气地说:“你个没良心的小东西,敢顶嘴?你要是不把火弄旺了,就别想再点篝火。过来,告诉我你愿意为我效劳,别改口。”
小孩无奈地说:“是,我愿意,小姐。”继续敷衍塞责地拨弄篝火。
“再多待一会儿,就给你一个弯背六便士[49],”游苔莎口气温和下来说,“隔两三分钟就扔一块劈柴进去,不要一下子扔许多。我要在这个岗子上再走一会儿,一定会不断地回来看你。要是你听见有青蛙跳到水塘里,像扔进石块似的扑通一声,一定要跑来告诉我,那是下雨的先兆。”
“是,游苔莎。”
“维尔小姐,先生。”
“维——苔莎小姐。”
“够啦。现在再扔一块劈柴。”
小奴隶照旧继续添着火。他俨然是一个机器人,一言一行任由游苔莎颐指气使;活像传说中大阿尔伯图斯[50]做过的铜人,仅仅给了它说话、移动和供役使的活力。
姑娘再次去散步之前,先在堤上站住,静静地听了一会儿。那地方尽管地势低一些,却完全和雨冢一样孤寂;北面有几棵杉树,所以少受一些风吹雨打。围在住宅外面的那道土堤,保障它免遭堤外那种蛮荒状况的侵袭,土堤是用堤外濠沟里掘起来的方土坯砌起来的,微微拍打过,稍有倾斜;这块地方风高地荒,树篱难长,砌墙材料又没法搞到,所以土堤有不小的防护作用。除此以外,地形颇开阔,俯视整个山谷,直到怀尔狄夫屋后那条河流。它的右上方是雨冢朦胧的山影,遮蔽着天空,去那里要比静女酒店近得多。
游苔莎把荒凉的高坡和低狭的空谷都悉心观察了一番,不由显露出一种不耐烦的姿势来。烦躁的字句不时从嘴里冒出,不过其中却夹杂着叹息,而叹息之间又有突然的静听。她从站着的高处下来,又朝着雨冢漫步,不过这次却没把全部的路程走完。
她重新露了两次面,都间隔几分钟,每次都问——
“小鬼,听见水塘里有咕咚一下没有?”
“没有,游苔莎小姐。”小孩回答。
“好吧,”她终于说,“我很快就进去啦,届时给你弯背六便士,放你回家。”
“谢谢啦!游苔莎小姐。”疲乏的烧火工说,喘气轻松了许多。游苔莎又从火堆旁走开,不过这一次却不是去雨冢。她只沿着土堤,绕到房子前面的边门,站住看风景。
五十码开外,就是两堤相遇的弯角,上面点着篝火:土堤里面,就是那小孩的身影,像先前一样,一次举起一块劈柴往火里投。游苔莎懒洋洋地老远看着他,他有时爬上土堤背角,站在炭火边。晚风把烟火、小孩的头发和背心的衣角,都往一个方向吹起,风停息时,衣角和头发不动了,烟就直上夜空。
游苔莎远远看着,发现那小孩明显一惊;他溜下土堤,朝着白色的栅栏门跑过去。
“怎么啦?”游苔莎问。
“一个青蛙跳到水里去啦。没错,我听见了。”
“那是要下雨了,你还是回家去吧。不害怕吧?”游苔莎说得非常急促,仿佛听见小孩的报告,心跳到了喉咙口一般。
“不害怕,我有了弯背六便士嘛。”
“不错,给你。现在赶紧跑吧——不是那边——走这边庭园好啦。荒原上没有一个小孩有过你这样好玩的篝火。”
小孩显然大喜过望,轻快地步入了茫茫夜色。他一走,游苔莎便把望远镜和沙漏都放在栅栏门边,敏捷地走小门直奔土堤角,篝火的下面。
她就在这里等候,由外围工事掩护着。不大一会儿,只听堤外的水塘里,又扑通的一响。要是小孩还在那儿,他一定会说水里又跳进了一只青蛙;但是让大多数的人来听,那声音却很像一块石头落到水里。游苔莎上了土堤。
“谁?”她屏住了呼吸问。
在山谷低垂的夜空衬托下,一个男人的影子,应声在水塘对面隐约出现。他绕过水塘,跳上土堤,来到她身旁。游苔莎不觉低声一笑,这是姑娘今晚上嘴里发出来的第三种声音。头一种是站在雨冢上发的,表示焦虑;第二种是在山岗上发的,表示不耐烦;现在这第三种表示胜利的喜悦。她一言不发,只喜上眉梢地看着他,仿佛她从混沌之中创造出了一个奇迹。
“我来啦,”那个男人说,他正是怀尔狄夫,“你让我不得安宁。干嘛不让我一个人呆着?一晚上,都在看你那篝火。”这些话不免含着感情色彩,语气却保持平稳,好像为了防止突如其来的极端感情迸发而如履薄冰。
姑娘看到情人意外地克制起来,自己也好像克制着。“当然看得见我的篝火啦,”她故作冷冰冰的态度,平静地说,“荒原人十一月五日都点篝火,我怎么就不该点一个啊?”
“我知道这是为我点的。”
“你怎么知道的?一直没跟你说过话呀,自从你——你选中了她,和她出双入对,就把我完全甩开了,好像我从来就不是你不离不弃的命根子似的!”
“游苔莎!能忘吗?去年秋天,同月同日同地点,你也点了一模一样的篝火作信号,约我来跟你见面。要不是同样的目的,维尔舰长门外干嘛又点起同样的篝火来了?”
“不错,不错——我承认,”游苔莎低声喊着说,说话举止无精打采,骨子里却很热烈,这是她个人所特有的,“别一开口就对我这样说话,戴蒙,你会逼我把本来不愿意出口的话说出来的。我本来对你不指望了,下决心不再把你放在心上了;后来我又听了消息,让我觉得你没变心,所以才跑出来点了篝火。”
“你听见什么消息啦,才这样想?”怀尔狄夫吃惊地问。
“听说你没跟她结成婚!”游苔莎凯旋似的小声说,“我知道这是因为你更爱我,不能跟她结婚。……戴蒙,你狠心把我甩了,我说过永远也不能饶恕你。就是现在,我看也不能完全饶恕你——凡是有点志气的女人,对于这种大事,都不能释怀的。”
“要是早就知道你叫我来,只是为了责备我,我就不来了。”
“我才不在乎呢。既然你并没跟她结婚,又回到我身边来了,那我就饶恕你吧!”
“谁告诉你的,我没跟她结婚?”
“外公。他今天走得很远,回家路上追到一个人,告诉他婚没结成。他猜到可能是你,我知道一定是你。”
“还有别的人知道吗?”
“看来没有吧。我说,戴蒙,现在看出我点信号火的用意了吧?要是我认为你已经娶了那个女的,那就不要想我会点篝火。那么想,就侮辱我的自尊心了。”
怀尔狄夫没说话,他显然那么想过。
“你当真以为我相信你已经结婚了吗?”她很认真地又问了一遍,“那就看错我了。我以性命和心灵担保,我实在无法接受你那样看扁我!戴蒙,你这个人,真的配不上我;我明明知道,还是爱你。没关系,随它去吧——我只有尽力忍受你的鄙薄就是了。……”她见怀尔狄夫还是没有什么表示,就掩饰不住心中的焦灼,补充道,“我问你,你无法把我释怀,还是要最最爱我,是不是真的?”
“是啰,要不然我为什么来了?”他生气地说,“不过既然承蒙你说我配不上你,那我就是对你一片忠心,也没什么大不了了。要说不配,也应该我自己来说,出自你口中就不够开恩了。不过我这个人,生来就倒霉,脾气火暴,一辈子都得受罪,对女人要逆来顺受。我从工程师落魄到店小二,都是因为这。至于还有什么低级行当等着我,我还拭目以待呢。”他仍旧神色忧郁地看着游苔莎。
游苔莎抓住时机,把围巾往后一甩,让火光充分照到脸和脖子上,微笑着问:“你在外面游历这几年,见过比这更好的吗?”
游苔莎那个人,没有把握是不会摆出这种姿态的。他静静地回答说:“没有。”
“就是托马辛的肩膀上也没有吗?”
“托马辛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可爱姑娘。”
“那与此无关,”游苔莎一下就冲动起来,喊着说,“要把她放开;现在要考虑的,只有你我两个人。”接着她把对方看了老半天,才恢复了原先那外冷内热的态度,“是不是我得继续跟你示弱表白呢?本来这是女孩子应该隐瞒的嘛。我现在可以承认:直到两小时前,我还认为你把我抛弃了呢;我心里让那可怕的念头搞得那么郁闷,简直难以言表。”
“对不起,让你那样痛苦。”
“不过我这种郁闷,也许不全是为的你,”游苔莎自矜地添了一句说,“心情郁闷,本是我的天性。我想我生来就这样的。”
“疑心病症。”
“再不然,就是因为搬到这片荒原上。住在蓓蕾嘴的时候,我倒也很快活。那个好时光啊,蓓蕾嘴的日子好哇!不过从此以后,埃格敦也要亮堂起来了。”
“但愿如此,”怀尔狄夫闷闷不乐地说,“亲爱的旧欢,你知道旧情复萌对我有什么后果吧?又要跟从前一样,到雨冢上跟你相会了。”
“你当然要那样。”
“然而我可要声明,今晚到你这之前,本打算这次说再见以后,就永不见面了。”
“说这个,我才不感谢你呢。”她说着别过身体,无名火像地热一般扩散到全身,“想去雨冢的话请便,但你休想看到我;你尽可以呼唤,但我不会听[51];你尽可以诱惑我,但我再也不会对你一心一意了。”
“你从前也说过这话的,亲爱的;不过像你那种性格,要说话算话,恐怕不容易吧。像我这种性格,想要那样,也办不到。”
“这就是我费尽心机得到的快乐了,”她辛酸地低声说,“我为什么要把你叫回来呢?戴蒙,我心里有时会打怪仗的。你伤害了我,等我平静下来,就想道:‘难不成我拥抱了一片普通的云雾?’[52]你是一条变色龙,现在你的颜色变得最坏了。回家吧,别让我恨你!”
怀尔狄夫只对着雨冢出神,到了从一数到二十的工夫,才显得一切都无所谓的样子说:“好吧,回家就回家。你还打算和我见面吗?”
“除非你向我承认,你是因为更爱我,才没举行婚礼。”
“我想这种策略不怎么样的吧,”怀尔狄夫微笑着说,“你自己的能耐究竟有多大,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你要告诉我!”
“你心知肚明。”
“她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我不想对你谈她的事。我还没和她结婚,你召唤我,我奉命而来。这还不够吗?”
“我只是无聊,才点了这篝火。就像隐多珥的女巫招引撒母耳[53]那样,我想把你引来,对你炫耀能耐,心里想这样挺刺激的。下决心把你引来,你果然来了!这已经证明我很有能耐了。来是一英里半,回家又是一英里半——为我走三英里地的黑道儿。这难道还没证明我有能耐吗?”
怀尔狄夫朝她直摇头:“我太了解你了,我的游苔莎,太了解你了。你的口气,我无所不知;你那滚烫的胸怀,要了命也玩不出这样冷酷的把戏来。黄昏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女人,在雨冢上朝我的房子观察。我想是我先把你引出来,然后才是你把我引出来的吧。”
怀尔狄夫此刻显然是旧情复燃了;只见他凑过去,脸好像要去贴游苔莎的脸颊。
“不要,”游苔莎说,倔犟地往渐熄的篝火对面跑,“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么吻吻你的手行吗?”
“不可以。”
“那么拉拉你的手吧?”
“也不行。”
“那么一概免了,我向你道晚安吧。再见,再见。”
游苔莎并没回答;怀尔狄夫跳舞领班一样欠了一下身,像来时那样在水塘对面消失了。
游苔莎长叹了一声;这并不是少女柔弱的叹息,而像是一阵冷战,全身都撼动了。有的时候,她的理智之光瞬间照射到她的情人身上,揭示了情人的缺陷,她就要打这样的冷战。但它稍纵即逝,她又照样爱下去。她明知对方只是跟她闹着玩,然而她照样爱下去。她把没有烧光的柴火拨散,立刻进了屋,没有点灯就到了卧室。在表示她摸黑脱衣的窸窣声中,不时传来沉重的喘息;十分钟以后,她进入了梦乡,同样的战颤偶尔还撼动了她的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