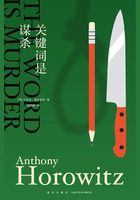
第3章 葬礼安排
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是那种天光近乎泛白,暖意融融的日子;刚过十一点,黛安娜·考珀穿过富勒姆路,走进了一家殡仪馆。
黛安娜身材娇小,气质干练。她的眼神、修剪过的发型,还有走路的姿势,无一不透露着一股坚定。如果你大老远看见她走来,你的第一反应会是退到一边,给她让路。然而,她并不惹人讨厌。她已是花甲之年,长着一张颇有亲和力的圆脸,一身名牌服饰,灰白风衣微敞,露出里面的粉红色针织衫和灰色裙子。她脖子上戴着一条沉甸甸的宝石项链,这条项链也许价格不菲,手上那几枚钻戒无疑货真价实。在富勒姆和南肯辛顿大街上,时常能看见像她这样的女人,正在前往美术馆或午餐赴约的路上。
那家殡仪馆名叫“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开在排屋的尽头,门脸和建筑一侧用古雅的字体漆着招牌,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来,都能注意到它。为了防止两处招牌的字连上,正门上方挂了一个维多利亚风格的钟表,指针已经不走了,停在约莫晚上十一点五十九分的位置,差一分钟就到子夜。招牌下方,同样漆了两行小字,道出殡仪馆的历史——独立殡葬业务承接:家族企业,始于一八二〇年。临街的一面有三扇窗户,其中两扇挂着窗帘,最后那扇橱窗内摆着一本摊开的书本雕塑,由大理石雕刻而成,上面镌刻着一句名言:悲伤降临时,从不形单影只,而是气势汹汹。[1]店铺的所有木材,无论是窗框、门脸,还是大门,都漆成了深蓝色,接近黑色。
考珀太太推开大门,旧式的弹簧装置触发,一声清脆的门铃声响起。门口就是一片小小的接待区,里面摆着两张沙发、一张矮桌和几层书架,书籍散发着无人问津的悲伤气质。一截楼梯通向其他楼层,前面是一条狭长的走廊。
眨眼的工夫,一个女人露面了。她身材结实,顺着她粗壮的双腿可以看到一双黑色的皮鞋,她正向楼下走来,脸上挂着礼貌亲切的微笑。那微笑昭示着她处理的生意虽然棘手、令人痛苦,但她会用专业的态度冷静而高效地办好。她叫艾琳·劳斯,是丧葬承接人罗伯特·康沃利斯的私人助理,同时也担任接待员。
“早上好,您需要帮忙吗?”她问道。
“对。我想安排一场葬礼。”
“您是代表死者前来吗?”她用的是“死”这个字,很直白。不是“过世”,也不是“已故”。直言不讳是她的一个职业习惯,接受大限已至的事实,反而能让死者的亲朋好友减轻一些悲痛。
“不是,”考珀太太回答说,“是替我自己。”
“我明白了。”艾琳·劳斯眼睛都没眨一下。她为什么要惊讶呢?人们亲自为自己安排葬礼的情形并不少见。“您有预约吗?”她问道。
“没有,我不知道需要预约。”
“我去看看康沃利斯先生是否有空,请稍坐片刻。您想喝茶还是咖啡?”
“不了,谢谢。”
戴安娜·考珀坐下来。艾琳·劳斯的身影消失在走廊深处,几分钟后,她再次出现,跟在一个男人的身后,男人的形象完美地符合人们对殡仪馆馆长的印象,仿佛是在扮演这一角色。当然,还有那身标志性的着装:深色西装搭配暮气沉沉的领带。他的站姿似乎在暗示,他为必须出现在这里而感到抱歉。他的双手交叠,像是在深表遗憾。他的脸皱巴巴的,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在秃顶边缘试探的稀疏头发和仿佛试验失败的络腮胡更添几分凄惨。他戴着一副有色眼镜,镜架滑到了鼻梁上,不只是框住眼睛,还遮住了它们。他看起来四十岁左右,脸上挂着微笑。
“早上好,”他说,“我叫罗伯特·康沃利斯。您希望与我们讨论一下葬礼的安排吗?”
“是的。”
“有人给您提供咖啡或茶水了吗?请这边走。”
新来的客人被领着穿过走廊,来到尽头的一个房间,这里和接待区一样装修得很不起眼。唯一的区别是,书架上摆的不是书,而是文件夹和小册子。如果打开它们,你会看见不同式样的棺材、灵车(传统的或马拉的)图片,还有价目表。如果您倾心火葬的话,两排架子上还陈列着骨灰盒。两把扶手椅面对面摆放在一起,旁边各有一张小桌子。康沃利斯坐在其中一把扶手椅上,取出一支万宝龙钢笔,放在记事本上。
“葬礼是为你自己准备的?”他开门见山地说。
“是的。”考珀太太的语速忽然变得轻快起来,想要直奔主题,“细节我已经考虑过了,您应该没有意见吧。”
“恰恰相反,客户的个人要求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如今,提前规划好的葬礼——您也可以称之为定制葬礼或是主题葬礼,几乎可以说是我们的主要业务。满足客户的需求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在这里讨论结束后,假设您接受我们的条款,我们将为您提供一张完整的发票和约定条款的明细。您的亲朋好友只需要前来参加葬礼就行,什么都不用操心。根据我们的经验,我可以向您保证,当他们得知一切事宜已完全按照您的意愿安排妥当时会倍感安慰的。”
考珀太太点点头。“好极了。好吧,让我们开始吧,可以吗?”她调整了一下呼吸,“我想要在纸板棺材里下葬。”
康沃利斯正要记录第一条内容,却停下了笔,笔尖悬在纸的上方。“如果您在考虑环保葬礼,我会建议您使用再生木材,甚至可以选择龙爪柳枝,而不是纸板。有些情况下,纸板……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他谨慎地措辞,给自己的表达留下各种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柳藤的价格不会更高,却更具性价比。”
“好吧。我想被安葬在布朗普顿公墓,挨着我丈夫的墓。”
“您最近送走他的?”
“十二年前吧。我们有自己的墓地,所以不会有问题。这是我列好的仪式清单……”她打开手提包,取出一张纸,放在桌子上。
殡仪馆馆长瞥了一眼。“我看到您对此做了精心的准备,”他说,“要我说的话,您对葬礼仪式的安排经过了深思熟虑,既有宗教氛围,又能体现人道主义关怀。”
“嗯,念一章《诗篇》,还要放披头士乐队的歌。一首诗,几段古典音乐,再加上几篇悼词。我不希望葬礼持续太长时间。”
“我们可以控制好时间……”
***
戴安娜·考珀安排好了自己的葬礼,而不久之后,它就派上了用场。就在当天,大约六小时后,她被人谋杀了。
此前我从没听说过她,也几乎对她的死亡经过一无所知。我可能留意过报纸头条新闻的标题——《男星之母遭人谋杀》——但是照片和报道的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那位更有名的儿子身上。他最近刚刚主演了一部新播出的美国电视剧。上文中我描述的对话内容仅仅是个大概。因为,当然了,我不在现场。但是我确实去过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并与罗伯特·康沃利斯和他的助手(也是他的表亲)艾琳·劳斯详细交谈过。如果你沿着富勒姆街走,轻易就能找到那家殡仪馆。房间完全符合我的描述。其余的大部分细节均来自证人证词和警方卷宗。
我们知道考珀太太何时进入殡仪馆,因为街上的视频监控和她当天上午出门后乘坐的那辆公交车视频监控记录了她的行踪。她的怪癖之一就是总爱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尽管雇一位司机接送她,对她而言本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她离开殡仪馆,步行至南肯辛顿地铁站,乘坐皮卡迪利线前往格林公园。她在穆拉诺咖啡厅和一个朋友吃了早午餐,那是一家高消费的餐厅,位于圣詹姆斯街,福南梅森[2]附近。接着,她从那里打车前往南岸的莎士比亚环形剧院。她不是去看戏的。她是董事会的成员,当天是去剧场二层开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将近五点。她六点零五分回到家,碰巧赶上下雨,但她随身带了把伞,并将伞放在了家门口的仿维多利亚风格置物架上。
三十分钟后,有人勒死了她。
她住在不列颠尼亚路的一栋联排别墅里,离著名的“世界尽头”切尔西区不远,就她的遭遇来看,几乎一语成谶。街上没有道路监控设备,所以无法得知作案时段是否有可疑人物进出。附近的别墅都无人居住,其中一栋房产的主人是一家本部驻迪拜的财团。通常房子会出租,但在案发时是空置状态。另一栋别墅是一位退休律师和妻子的住宅,可案发时他们正在法国南部。所以没人听到什么动静。
她的尸体是两天后才被人发现的。发现人是安德莉亚·卡卢瓦涅克。她是一名斯洛伐克裔的清洁工,每周为考珀太太打扫两次卫生。星期三一早来上班的时候,她发现戴安娜·考珀面朝下倒在客厅地板上,脖子上缠着一截红绳(是用来系窗帘的绳子)。验尸报告里用一贯冷漠的口吻记录着尸体表征,详细描述了颈部钝器所致的伤痕、舌骨骨折和结膜充血。安德莉亚看到的场面更加惨烈。她已经在这栋房子里工作了两年,对她的雇主也慢慢产生了感情。考珀太太一向待她宽厚,经常抽空和她一起喝咖啡。星期三,她照旧来打扫卫生,打开大门,猝不及防地看到了一具尸体,而且那具尸体已经躺了一段时间了。她可以看见那张脸变成了绛紫色,眼神空洞地盯着某处,舌头怪异地伸出来,是平时长度的两倍。她的一只胳膊伸展着,戴着钻石戒指的手指刚巧指向她,仿佛在谴责她一样。中央供暖系统一直在运转,尸体已经开始散发气味。
据她提供的证词来看,安德莉亚没有尖叫,也没有吐。她安静地走出别墅,用手机报了警。直到警察赶来,她才再次进入别墅。
一开始,警察认为戴安娜·考珀的死与入室盗窃有关。一些物品(包括首饰和一台笔记本电脑)被人拿走了。许多房间被人翻过,物品散落一地。可是,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显然,考珀太太为袭击者开了门,尽管我们还不清楚她是否认识这个人。她没有提防,被人从身后勒死。她几乎没做什么抵抗。房间里没有留下指纹,提取不出DNA,没有留下任何线索,这表明作案人事前经过周密的计划。他趁考珀太太不备,从客厅的天鹅绒窗帘旁边的钩托上取下红绳,潜伏到她身后,将红绳猛地绕过她的脑袋,用力勒紧脖子。只需一分钟左右,她就断气了。
然而,随后警方发现她死前曾去过康沃利斯父子殡仪馆,终于意识到事情没有他们想得那么简单。试想,某人刚为自己安排了葬礼,就在同一天被人谋杀了。这绝不是巧合,一定有所关联。她会不会事先已经知道自己会不久于人世?会不会有人在她进出殡仪馆的时候撞见了她,然后出于某种动机,临时起意采取了行动?有谁知道她去过那里呢?
这绝对是一桩谜案,需要一位专业人士来侦破。可是,这桩案子与我毫无瓜葛。
然而,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改变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