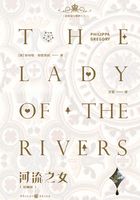
1433年夏
伦敦 威斯敏斯特宫
小国王让我很失望。我以前从未见过国王,因为自己所在的卢森堡郡不直属王室管辖,父亲是一位伯爵,我们一直听从历代勃艮第公爵们的命令——他们也算是法国贵族中最富贵最有权势之人了。最后一位法国国王据说很可怜,发了疯,早在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去世了,我没能见到他。所以我才非常期待见到这位英国的少年国王。我希望见到一位和他的伟人父亲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年轻人。归根到底,我的丈夫这么鞠躬尽瘁,为的就是能让他安全地坐拥法国疆土。我们两人都效忠于他。我期待着见到一位伟大的人;一位介乎于少年和神之间的存在。
凡事不尽如人意。我第一次看见他时是在我们进伦敦城的路上,那时我们正穿过城门,被唱诗班的歌声和市民的欢呼环绕。我丈夫已经是伦敦人民的老朋友了,我则是他们喜闻乐见的新鲜面孔。男人们大声夸我年轻貌美,女人们冲我抛来飞吻。伦敦商人们靠着与法国的英属领土做买卖过活,我丈夫又因守卫那些土地而闻名。商人们纷纷偕妻子和家中老小走到街上祝福我们,还从高处的窗子打出旗帜。伦敦市长为我们准备了诗歌和露天剧,有一幕中,一位美丽的人鱼许诺带来健康、繁茂和永流不息的幸福之泉。我的公爵大人握住我的手向众人鞠躬敬意,在他们喊叫我的名字和高呼祝福之语的时候满脸自豪。
“伦敦人喜欢漂亮女孩。”他对我说,“如果你美貌常驻,我就能一直受他们的爱戴。”
国王的侍从们在威斯敏斯特宫门口欢迎我们的到来,接着带我们穿过迷宫般的王室花园、重重内房、走廊庭院,最后来到国王的私人房间。一扇门打开,紧接着又是一扇,再后面的房间里满是身着华服之人,终于,年轻的国王出现了,从王座中起身上前问候他的大伯,就像一个小小的吓人玩偶从一层套一层的盒子里跳了出来。
他又瘦又矮——这便是我的第一印象——而且很苍白,像整天缩在屋里的学者,我知道他们带他外出训练,每天骑马,甚至要与人比武,但对手的枪尖上会绑一个安全垫。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病了,因为他那几近透明的皮肤和缓慢的步伐让我觉得他不堪重负。突然间,我惊恐万分地在光芒之中看见他变成一个玻璃器具似的东西,如此纤薄,如此透明,好像一旦摔到石头地上就会粉身碎骨。
我惊喘出声,我丈夫瞥向我,接着就转向他的国王侄儿,鞠躬后伸手一把抱住了他。“哦!小心!”我悄声说,害怕他可能伤到那孩子,伍德维尔机灵地迈过来抓住我的右手,似乎要领我上前谒见国王。
“怎么了?”他小声地急切问我,“你不舒服吗,夫人?”
我丈夫两手按在那男孩的肩上,正凝视那张苍白的脸,凝望那浅灰色的眼睛。我几乎能感受到他的手劲之大、我感到他的抓握太过用力了。“他那么虚弱,”我小声说,然后找到了确切的形容,“他那么脆弱,像个用冰雪,用玻璃制成的王子。”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伍德维尔小声喝道,用力掐了我的手。我被他的语气和突如其来的疼痛吓了一大跳,停下来看他,突然间神清志明,发现廷上男男女女都围着我们,盯着我、公爵和国王,伍德维尔带我上前,让我屈膝行礼,他果断的举措让我明白自己不能再乱说话了。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国王轻触我的手臂,让我起身。他恭谨有礼,因为我是他的叔母——尽管我只有十七岁,他也只有十二岁。我们二人都年轻无邪,身处在这满是道貌岸然的成年人的宫廷之中。他表示对我的欢迎,声音轻而细微,是尚未变成男人的声调。国王在我的左右脸颊分别落下一吻,嘴唇很冷,恰如我初见到他时所想象的薄冰一样,他握住我的手也细瘦不堪,我几乎能感觉到皮肤下的指骨,仿如一根根细小冰柱。
他邀请我们共进晚餐,转身让我入内,走在人们的最前头。一个衣着华贵的女人重重地踏步后退,好像很不情愿给我让道。我看了一眼年轻的国王。
“那是我的另一位叔母,伊琳诺,格洛斯特公爵夫人。”他操着小男孩特有的高音说道,“她的丈夫是我最爱的叔叔,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
我向她行礼,她也向我回礼。在她身后我看见一张英俊的脸,那是我丈夫的弟弟格洛斯特公爵。他和我丈夫将手搂住对方肩膀深深相拥,可当我丈夫转向他的嫂子伊琳诺时,我看见他一脸严苛。
“我希望我们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国王用他那还不到变声期的高音说,“我认为一家人应该上下齐心。王室家族应该永远齐心一致,你们不这样觉得吗?我们应该相亲相爱,和谐共处。”
“当然如此。”我说道,就算以前没见过女人的敌意和嫉妒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也在格洛斯特公爵夫人那张美丽娇纵的脸上清楚见识了一番。她头戴高耸的头巾,像个女巨人,成了在场最高的女人。她穿着深蓝礼服,饰以白貂皮,这可是世间最名贵的皮毛。她的颈间戴着一圈蓝宝石,而双眼比宝石更蓝。公爵夫人冲我微笑,笑得露出一口白牙,但脸上毫无和善之意。
国王让我坐在他的右手边上,我的公爵大人则坐在左边。紧挨着我的是格洛斯特公爵,他的妻子则坐在对面、我丈夫身边。我们面朝宽敞的餐厅,就好像是厅中人们的织锦画和赏玩之物:身着灿烂耀眼的礼服斗篷,戴着闪闪发光的珠宝首饰。他们盯着我们看,就好像我们是代表着礼教的一个个假人。我们俯视着他们,如同天神俯瞰凡夫俗子。上菜之时,我们把最好的菜肴传给亲信,似乎要提醒他们连吃饭时也不忘按我们的吩咐行事。
晚宴过后是舞会时间,格洛斯特公爵飞快地领我走进舞池。我们每跳一段之后就停下一会儿给其他人让地儿。“你是这样迷人,”公爵对我说,“他们跟我说约翰娶了一位大美人,我那时还不信呢。我在法国为祖国打拼那么多年,怎么会从没见过你呢?”
我笑而不语。真相应该是,当我丈夫在无穷的战火中为英国守卫在法国的领土奔忙之时,这个无用的弟弟却和海恩诺特的伯爵夫人嘉桂琳私奔了,还为了他一己私利发起战争,要把她的土地占为己有。他挥霍无度,差点连整个人生都搭了进去。他那颗朝三暮四的心最后落到她的侍女,也就是这位伊琳诺身上。他带着她又一次私奔了。总而言之,这男人行事全凭自己的欲望,毫无责任感。这男人与我丈夫是如此迥异,我简直无法相信他俩都是英国国王亨利四世之子。
“如果我曾见过你,我是绝对不会回到英国的。”舞步中的一个旋转使我们彼此贴近,他趁机对我耳语。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也不喜欢他看我的那副样子。
“如果我曾见过你,我将永远不离你左右。”他说。
我望向丈夫,可他正在和国王说话,没有看见我。
“你会对我微笑吗?”我丈夫的弟弟这样问我,“就现在?还是说你害怕把我的心也偷走了?”
我没有笑,一脸严肃,心想他怎么敢对他的嫂子这样讲话,如此厚颜无耻,好像坚信我无法回绝一样。他握住我的腰的方式既令人反感,又十分美妙,这好歹是舞蹈动作的一部分;可他将我拉近,温暖的掌心按在我的背上,大腿摩擦着我的身体,这就与跳舞无关了。
“我哥哥作为丈夫可曾取悦到你?”他悄声细语,温热的呼吸吐在我光裸的脖颈上。我稍微向后倾去,却被他抓紧拉得更近。“他可有抚摸你,就像年轻女孩们喜欢的那样——既轻又快?”他笑了,“我说对没有,雅格塔?你是不是喜欢被这样抚摸?既轻又快?”
我推开他,眼前是旋转的色彩,耳边是热闹的音乐。理查德·伍德维尔出现在身旁并拉住我的手,拉我跑进跳舞的人群中心,带我转了一个又一个圈。“请原谅!”他回头向公爵喊道,“我弄错了吗?我在法国待了太久啦,还以为这是交换舞伴的时间呢。”
“不是,你出手太早了,不过也没关系。”公爵说道,拉起被伍德维尔鲁莽地抛下的舞伴的手,加入舞蹈的行列。伍德维尔和我则在圆圈中心迈着细小的舞步,接着将手抬高形成拱门,让别的人从中跳舞穿过,人们再次交换舞伴,我边跳舞边远离汉弗莱公爵。

“你觉得国王怎么样?”那天夜里,我丈夫来到我的卧室问我。床已经为他铺好了,枕头堆得高高的。他进屋时精疲力尽地叹了口气,我注意到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脸疲惫而苍白。
“非常年轻。”
他短促地笑了一声:“你倒是一位老夫人呢。”
“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我说,“而且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些虚弱。”我没告诉丈夫自己的感觉,当时我感觉到的是一个脆弱如玻璃,寒冷如薄冰的男孩。
他皱眉。“我相信他足够健康,不过我也同意你说的,他比同龄人更瘦小。他的父亲……”他没再说下去,“好吧,现在再说他父亲是什么样、小时候又是什么样也毫无意义。不过天知道我的哥哥亨利小时候有多身强力壮。无论如何,已经没时间悔恨嗟叹了,这男孩必须继承他父亲的遗志。他必须成长成一位伟大的人。你对我的另一个兄弟印象如何?”
我忍住没有脱口而出。“我觉得我这辈子从没遇过像他这样的人。”我拘谨地说。
他短促一笑:“我希望他没有用你不喜欢的方式对你说什么。”
“没有,他的礼仪无可挑剔。”
“他觉得自己能拥有世间任何女子。汉弗莱在法国向海恩诺特的嘉桂琳求爱时险些把我们给毁了。他最后看上了她的侍女简直就是救了我一命,虽然他还是带侍女私奔回了英国。”
“是伊琳诺夫人吗?”
“是的,老天啊,多可怕的丑闻啊!所有人都说是她用春药和巫术引诱了他!而嘉桂琳则声称他们已经成婚,被孤身一人遗弃在海恩诺特!典型的汉弗莱式作风,可是谢天谢地他抛下她回到了英国,在这里他不会造成什么恶果,就算有,至少比较小。”
“那么伊琳诺呢?”我问,“他现在的妻子是怎么想的?”
“她曾是他妻子的侍女,接着成了他的情妇,现在又成了他的妻子,所以,谁知道她心中在想些什么呢?”我丈夫评论道,“不过她绝不是我的朋友。我是长兄,因此也是王位继承人。如果亨利国王出了什么事——上帝保佑——我就会接替他戴上英法两国的王冠。汉弗莱在我之后,排行第二。有时候她看我的眼神好像希望我早死。她会祈祷你生不出儿子,我们的儿子会让王位离她更远。你能用你的预知告诉我,她会施法吗?她是否精于此道?她会不会诅咒我?”
我想起那个戴着耀眼的蓝宝石、拥有耀眼的微笑和冷酷双眼的女人:“我在她身上看见了骄傲、虚荣和野心勃勃,别的我什么也不能保证。”
“这就已经够糟糕了。”公爵大人急促地说,“她随时都可以雇到真的会施法的人。我应该监视她,你觉得呢?”
我仔细揣摩这位光彩照人的女人和她那轻言细语的英俊丈夫。“是的。”我说,心想这里的宫廷距离我在洒满阳光的法国城堡的孩童时光是那样遥远,“是的,如果我是你,一定会监视她。我会同时监视他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