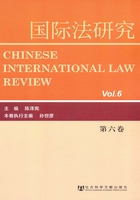
四 “迟延同意管辖”原则的发展与完善问题
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中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诉讼管辖程序,即所谓“迟延同意管辖”或“迟延同意的法院”(forum prorogatum)。迟延同意管辖是指在争端当事双方事先没有明文约定或同意的情况下,争端一方对另一方提起诉讼,如果另一方以某种方式予以同意或应诉的话,法院就具有了对该特定案件的管辖权。如果对方国家拒绝给予同意,法院的管辖权最终还是无法形成。迟延同意管辖原本是罗马法中的一个概念和制度,意指通过当事方同意而将一个事件提交给一个并不是通常对其具有管辖权的法官处理。其对应的英文是prorogated jurisdiction。[26]中文中有的还译为“应诉管辖权”“当事方同意的法院”等。[27]
在国际法上,所有国际性法院或法庭的管辖权原则上都是基于有关国家同意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管辖权都是当事方同意的管辖权。但是,国际法院的迟延同意管辖权有其特定的含义,这种同意的时间或方式与一般意义上同意的时间和方式有所不同,它是一种迟延的或在起诉过程中从有关国家行为中推定出来的所谓默示的同意。例如,在一个案件中,国际法院对当事双方具有属人管辖权,却没有属事管辖权。如果当事双方在诉讼过程中要求法院对有关额外问题进行审理,那么法院就可以适用迟延同意管辖原则对有关问题进行审理。另外一种情况是,一方单方面提起诉讼后,由于被告国不同意其属事管辖权,或其属人管辖权也不确定,或二者兼而有之,法院因此没有管辖权。但如果被告随后又以某种行为或方式同意法院进行管辖,那么法院就可以正式立案受理该案件。如在常设国际法院1924年审理的希腊诉英国的有关马夫若玛提斯巴勒斯坦租界权一案(the Mavrommatis case)中,针对英国提出的一项初步反对意见,法院认为当事双方向法院提交的书面材料和所进行的口头程序已经构成一种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暗含特别协定(an implied special agreement),因此确定了对该案的管辖权。[28]
一般认为,国际法院(以及国际常设法院)迟延同意管辖权理论的确立缘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法院规约和规则中都允许单边提起诉讼,被告国的同意并不需要与诉讼请求书同时提交到法院;第二,被告国的同意并不需要明文表达;第三,规约和规则都没有具体表明诉讼何时应以特别协定提起以及何时应由单边申请提起。对于规约和规则中这种审慎的忽略或遗漏,国际常设法院在早期的判例中曾将其解释为法院的管辖权并不附属于遵守某些特定的形式,如事先缔结特别协定(1928年上西里西亚案)。也就是说,国家对于法院管辖权的同意既可以是规约和规则中明确规定了的三种书面同意形式,也可以是从有关当事国的行为(或两个单独而连续的行为)中推定出来的同意或默示同意(tacit consent)。[29]
在国际常设法院期间,迟延同意管辖权制度虽然已经在理论上得到了确立,司法实践中却只是偶尔适用。联合国国际法院成立后,法院受理的第一个案件——1946年的科孚海峡案,即被认为适用了迟延同意管辖权原则。但该案中英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将案件提交给国际法院审理,更多的还是由于安理会通过决议建议两国将争端提交给国际法院的结果。此后,又有几个根据迟延管辖权原则提起的单边诉讼案件,如1952年希腊诉英国的安巴提罗斯案(the Ambatielos case)和英国诉伊朗石油公司案,以及1954年的货币黄金案和美国诉保加利亚和苏联的航空器和机组人员案等。在这些案件中,原告国都主张法院有管辖权或邀请对方接受法院管辖。法院在收到这些申请后,书记官长根据法院规约和当时的规则,也和其他案件一样必须及时通知有关被告国并将申请列入案件清单。但在有关被告明确宣称不愿接受法院管辖权后,法院要进行审议,并发布指示将案件从目录清单中撤销。类似案件还有1955年空难案、两个关于南极洲的案件等。[30]这样不但给有关国家带来一些无谓的诉累,同时对正常的国际司法行政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直到1978年,法院规则进行了修订,其第38条第5款才首次对有关单边提起诉讼的程序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该款的规定是:“当请求国提出以被告国尚未表示的同意为法院管辖权的依据,请求书应转交被告国。但该请求书不应登入总目录,除非并直到被告国同意法院对该案具有管辖权。”
仔细阅读和分析该款规定,我们可以作如下两方面的理解:首先,这是一个新的规定。尽管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以前都有过这方面的案例,但仍属于司法实践,现在则有了关于迟延同意管辖权的明文规定,因此是一个发展和突破。其次,该规定实际上也对一些纯粹任意或毫无根据的诉讼进行了限制,规定如果没有被告国的同意,书记官长除了将申请书转交给被告国外,不得采取进一步行动,如将其列入案件的目录清单,从而也不至于损害良好的司法行政规则。[31]可谓用心良苦,实际上具有一箭双雕的作用。从积极方面而言,在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或不愿意以任何正式书面形式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情况下,这种机制显然是有利于国际法院建立一种更加宽泛有效的管辖权制度的。
尽管有了明文规定,但这种基于当事方迟延同意的管辖权很长时间并没有得到适用。1996年,时任国际法院院长贝贾维在其给联合国大会六委(法律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他打算鼓励联合国会员国更多地利用国际法院的服务,并特别推介了国际法院的迟延同意管辖权。他认为法院可以基于当事国在争端出现后表达的同意来行使管辖权,这体现了法院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更加正式的接受法院管辖权方式的补充,当然并不是替代。然而这种方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32]
似乎巧合的是,刚进入21世纪,国际法院的迟延同意管辖权却相继有了两次比较典型的适用。这两个案件分别是2002年刚果共和国诉法国的“若干在法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案”和2006年吉布提诉法国的“若干刑事协助事项案”。它们都是原告国根据1978年修改后的《法院规则》第38条第5款以单方诉讼请求书的形式提起诉讼的。法院受理这两个案件的程序基本上也是相同的,其审理结果则有所不同。
具体就刚果诉法国一案而言,刚果共和国在其2002年12月9日的请求书中明确提出,希望依照《法院规则》第38条第5款,“以法兰西共和国必将表明的同意”作为法院管辖权的根据。法院即根据此款的规定,将刚果共和国的请求书转交法国政府,而且并未采取任何程序行动。书记官处于2003年4月11日收到法兰西共和国的信函,该信函宣称该国“已同意法院的管辖权,以按照第38条第5款受理本件请求书”。此项同意使得本案可登入法院案件总表并且开始程序行动。法国在其信函中补充说,它对法院管辖权的同意仅严格限于适用于“刚果共和国所拟具的要求”,而且“刚果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书内所提及的法兰西共和国和刚果人民共和国于1974年1月1日签署的《合作条约》第2条不构成本案中法院管辖权的根据”。随后法院对该案有关指示临时措施的请求进行了开庭审理。当事双方就案件的实体问题也都在法院规定的时限内提出各自的诉状和辩诉状。经过多年反复提交书状的程序后,2010年11月5日,刚果代理人致函法院,提出根据《法院规则》第89条,刚果政府“撤回诉讼请求书”,并请法院“正式发布命令,记录中止诉讼,并指示从总表上去除该案”。法院即将来函副本转给法国政府,并同时告知法国政府,按照《法院规则》第89条第2款关于时限的规定,现已设定2010年11月12日为法国可表明是否反对中止诉讼的时限。2010年11月8日,法国代理人来函告知法院,法国政府“不反对刚果共和国中止诉讼”。2010年11月16日,法院正式记录了刚果诉讼的中止,命令从总表上去除该案。
同样,在吉布提诉法国的案件中,吉布提也是根据《法院规则》第38条第5款单方面提起诉讼,并在其2006年1月9日诉讼请求书中表示“确信法国政府会同意接受法院的管辖以解决本争端”。于是,法院根据该规定将吉布提的诉讼请求书转交给了法国。法国政府于2006年7月25日致函法院,表示其同意法院根据《法院规则》第38条第5款,并仅仅是以此条款为根据对该案行使管辖权。法国的同意使得法院能够将案件列入案件总表并启动诉讼程序。法院于2006年11月15日发布命令指示了吉布提提交诉状和法国提交辩诉状的期限,并于2008年1月21日至29日开庭审理了此案。2008年6月4日正式作出了判决。这也是国际法院第一次根据《法院规则》第38条第5款对一个有关争端进行实体审理和作出判决。[33]
国际法院的上述案例在国际社会尚没有产生太多反响,在国际法学界特别是国际法院内部却给予了比较积极的评价和肯定。如2002年国际法院正式受理刚果诉法国一案后即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迟延同意管辖原则在国际法院的成功回归,而这一原则对于旨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者和旨在寻求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主义者都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34]而在2008年吉布提诉法国的“若干刑事协助事项案”判决后,时任国际法院院长希金斯法官也及时予以肯定,并指出这意味着国际法院的迟延同意管辖原则已经从长期以来被认为只是教科书中的“一个死文字”(a dead letter)变成了鲜活的案例。[35]其他一些参与审理了上述两个案件的法官包括现任的小和田恒院长也在不同场合对该原则予以肯定和推崇。如2010年12月23日,小和田恒法官在中国西北政法大学的学术报告中专门提到刚果诉法国的案件,并指出其作为国际法院所具有的4种管辖权形式之一,尽管不常被使用,但也是很重要的。[36]
综上而论,国际法院的迟延管辖权在国际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无疑都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这种管辖权的依据虽然在形式上似乎突破了《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的有关规定,但它仍然是建立在国家同意原则基础之上的,而这种灵活的、非正式的同意形式实际上更有利于国家维护和行使其主权和选择利用国际法院作为一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37]从国际司法行政和国际社会法治化的发展要求而言,国际法院的迟延同意管辖原则显然也是有利于加强和拓宽法院的诉讼管辖权,提高其受案率和裁判效率的。迟延同意管辖原则的确立,特别是1978年修订后的《法院规则》第38条第5款规定使得法院不至于从一开始就拒绝一个具有出庭权国家的诉讼申请,这样更有利于国际法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形成一种良好的司法管理制度,从而进一步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的法治建设。当然,从国际法院已有的司法实践来看,有关当事国和国际法院内部对于迟延管辖原则的理解和适用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和问题,包括迟延同意的范围和不可撤回性问题、与法院指示临时措施之间的冲突和有关判决的执行等。[38]这些问题在当事国的同意是由两个单独连续的行为所表示或由法院推定出来时则尤显突出,而往往引起一些非议和担忧。[39]因此,国际法院的迟延管辖规则也必须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这也是其能否得到整个国际社会普遍接受或认可的关键。
Jurisdictional Issu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Context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form
Jiang Guoqing and Yang Huifang
Abstract: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the United Nations kicked off an array of reform plans,some of which have been put into effect.As the principal judicial organ of the United Nations,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s also faced with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ssues.This paper mainly probes into some challenges to the jurisdiction system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and its new developmental trends,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optional compulsory jurisdiction and prorogated jurisdiction(forum prorogatum).
Key Words:Reform of the United Nations;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Optional Compulsory Jurisdiction;forum prorogatum
[1] 江国青,外交学院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杨慧芳,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法学博士。
[2] A/55/1,《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补编第1号,2000。同年9月联合国首脑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则明确表示要加强联合国国际法院的作用,在国际事务中确保正义和法治。
[3] 《联合国宪章》第92条;《国际法院规约》第1条。
[4] 例如联合国改革之友小组(Group of Friends for the U.N.Reform)曾对高级别小组的报告没有提到国际法院的改革问题表示疑惑,并专门发表了一份有关“联合国改革背景下国际法院的作用”的文件,其中就国际法院的改革提出了一些较为具体的思考和方案。联合国改革之友小组是2004年4月由时任墨西哥总统邀请德国、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荷兰、新加坡、瑞典等15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组成的一个旨在促进联合国整体改革的国家间小组。该小组成立后定期举行大使级和部长级会晤。此外,2005年12月,国际法协会美国分会的解决政府间争端委员会也对目前有关联合国改革文件中没有专门列入国际法院的改革问题表示关注,并就此专门发表了一份题为《改革联合国:国际法院怎么办?》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认为国家应该利用联合国改革的机会同时考虑对国际法院进行一些关键的改革。有鉴于此,安南在2005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大自由报告”中,又特别强调了加强法治和国际法院作用的内容。而这方面的内容随后也反映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之中。
[5] 例如国际法协会美国分会的解决政府间争端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国际法院的改革应该包括:如果安理会要扩大,那么联合国会员国也应该考虑增加国际法院法官的数目;国际法院法官不应该连任,而将其任期增加到12年;应该规定法官的年龄限制;应该增加女性法官候选人的数目;政府间国际组织应具有诉讼当事方的资格;新人权理事会和某些国际性法院和法庭应给予请求发表咨询管辖权的权力等。ABILA Committee on Intergovernmental Settlement of Disputes,“Reforming the United Nations:What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2006)5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9.
[6] 《联合国宪章》第93条。
[7] 参见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601~602页;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99-2000,pp.82-89.实际上,目前可以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的国家都是联合国会员国。
[8] 杉原高岭:《国际司法裁判制度》,王志安、易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第94~96页。
[9] 有关规定实际上也是从《国际联盟盟约》和《常设国际法院规约》沿袭而来的。
[10]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1999-2000,p.90.
[11] 但这不同于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在其司法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所谓“迟延同意管辖权”(forum prorogatum)。对此本文后面将予以专门讨论。
[12] http://www.icj-cij.org/jurisdiction/index.php?p1=5&p2=1&p3=4.
[13] 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
[14] 参见Anthony Aust,“The Future of Judicial Function”,(2000)11 Fin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82.
[15] 参见联合国大会第63届会议《国际法院的报告》:A/63/4(SUPP).
[16] GA/L/3355,31 October 2008;Philippe Sands and Pierre Klein,Bowett’s Law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London:Sweet & Maxwell,5th edn,2001),p.358.
[17] 也有几个国家如瑞士、乌干达没有附加保留,则是例外情况。
[18] Sands and Klein,Bowett’s Law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p.358.
[19] 如印度、加拿大等国家。
[20] Edward McWhinney,Judicia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Jurisdiction,Justiciability and Judicial Law-Making o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ur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1),pp.58-59.
[21] 〔英〕马尔科姆·N.肖:《国际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影印版),第979~980页。
[22] 挪威指出,法国1949年3月1日声明中所作的保留,排除了法院对于“有关实质上属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所理解的一国国内管辖的事件所引起的争端”的管辖权。根据相互性原则,这一保留应同样适用于挪威。
[23] Certain Norwegian Loans,Judgment,ICJ Reports,1957,p.34.
[24] 参见邹克渊《国际法院审判案例评析》,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第68~72页。
[25] McWhinney,Judicial Settlement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s:Jurisdiction,Justiciability and Judicial Law-Making o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Court,p.58.
[26] Shabtai Rosenne,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nd rev.edn,1985),pp.344-346.
[27] 杉原高岭:《国际司法裁判制度》,王志安、易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第103~104页。
[28] Shabtai Rosenne,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3rd edn,1997),pp.698-699.
[29] Rosenne,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2nd edn),pp.345-346,357-359.
[30] Certain Questions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Djidouti v.France),Judgment,I.C.J.Reports 2008,pp.203-206.
[31] Ibid.;Shabtai Rosenne,Proced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urt:A Cmmentary on the 1978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3),pp.92-94.
[32] Press Release GA/L/3014 31st meeting,4 Nov.,1996.
[33] Certain Questions of Mutu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Djidouti v.France),Judgment,I.C.J.Reports 2008,p.204;Speech by H.E.Judge Rosalyn Higgins,President of the Court of Justice,to the Sixth Committe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31 October 2008,at http://www.icj-cij.org/presscom/files/1/14841.pdf.
[34] 参见Sienho Yee,“Forum Prorogatum Retur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2003)16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pp.701-713.
[35] 但希金斯院长和其他一些法官(如Skotnikov法官等)似乎并不认为上述两个案件代表着一种制度的“回归”,而是认为这两个案件才是典型(pertinent)意义上的迟延同意管辖权。Speech by H.E.Judge Rosalyn Higgins,President of the Court of Justice,to the Sixth Committe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36] 见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网站,《联合国国际法院院长小和田恒大法官学术报告(一):联合国国际法院审判实践中的法律问题及其法律因素》,at http://www.nwsil.cn/main/HTML/1282.html。
[37] Shabtai Rosenne,The Law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3rd edn),pp.724-725;Yee,“Forum Prorogatum Retur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pp.705-709.
[38] 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将在其他文章中另行讨论。
[39] 杉原高岭:《国际司法裁判制度》,第103~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