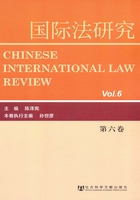
三 任意强制管辖权的接受与保留问题
长期以来,任意强制管辖权问题一直萦绕着常设国际法院和国际法院,在全球治理和联合国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则显得更为突出。前面述及,国际法院(及其前身常设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类似于国内法院的真正意义上的强制管辖权,它仍然是以国家选择同意为前提条件的。从常设国际法院成立伊始的近一个世纪以来,国际上先后曾提出过各种旨在加强这两个法院司法能力的建议或主张。从一般学者的观点来看,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是必须有司法制度作为其保障或支撑的,一个有效的司法制度往往起着“法律卫士”的作用,而缺乏司法制度的法律体系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法律体系。而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许多理想人士尤其是一些国际法学者更是从内心希望或渴望加强国际法院及其他一些国际司法机构的作用或权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国际法律体系的有效性。然而,从国际法院和常设国际法院的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个需要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国际社会能够演变到建立起或接受一个具有真正强制性管辖权的国际法院吗?对于该问题的看法,国际上的态度至少目前是悲观的,其答案是否定的。1999年联合国在荷兰海牙召开纪念第一次海牙和会和常设国际仲裁法院100周年大会,会上提交了一份题为《和平解决争端:21世纪的展望》的报告,其中也特别提到建立一种具有强制性管辖权的国际法院的可能性问题,但认为这在一个中长期阶段,甚至整个21世纪都是达不到的。
人们不会忘记,美国作为一个国内法治比较成熟的国家,一战后其总统威尔逊也曾积极倡导建立国际联盟和常设国际法院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但美国国会主要就是因为担心该法院对美国的管辖权而拒绝批准和约的,因而美国一直都没有参加国际联盟和成为常设国际法院的当事国。联合国成立后,美国虽然较早发表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但其所附加的有关国内事项的保留似乎又可以达到其完全不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效果。1985年尼加拉瓜案件后,美国又以各种理由撤销了其接受国际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声明,至今也没有重新接受。同样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法国在对待国际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问题上与美国有着类似的经历。法国最早于1949年发表声明接受任意强制管辖权,但范围很窄,因而在挪威公债案中败诉。在1973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诉法国的核试验案中,法国再次败诉,遂于1974年宣布撤回了其接受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声明,至今也没有重新接受。
应该看到的是,与不少国家对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消极态度不同,当代国际司法制度仍然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近二十多年来,国际上先后建立了一系列专门性和区域性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构、国际海洋法法庭、欧洲人权法院等。而在这些特定领域和区域范围内,国家之间接受了一些具有一定强制性管辖权或必须接受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程序,或所谓“自含机制”(self-contained regimes)和“一揽子协议”。一般认为,国际司法制度这种新的发展趋势固然反映当代国际社会进行全球治理和法治建设的需要,但它与国家不愿意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的情形还是有区别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是否愿意接受强制管辖权是与个别法院或程序的性质相联系的。与一些专门性或特定情形的区域性法院不同,国家之所以不愿意接受像国际法院这种具有一般国际法性质的强制管辖权,主要是因为一般国际法在许多问题上都是不太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在一些专门的和区域法律秩序中则可以大为减少。因此,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与否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决策问题,坚持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同意性质被认为是有利于国家保护自身权益以防止他国出于政治目的而滥用诉讼权利的,而不像接受一些其他条约的自含机制或专门性法庭的管辖权那样更多的是出于技术性质的考虑。
当然,国际法院管辖权制度的改革除了有国家的政治意愿问题,还有法律上的实际障碍。因为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改革,如使其成为某种具有一定强制管辖权性质的“自含机制”,[13]就必须修改《联合国宪章》和作为其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国际法院规约》的实体规定。而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造,无论是从宪章的修正程序或历史的实践来看,短期内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和目标,国际法院的改革更多的应该是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其作用和提高其工作效率的问题。例如,在诉讼管辖权方面,国际上一直比较普遍关注的就是如何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的现有规定下,尽量使更多的国家能够有效接受法院的管辖权,或以其他方式利用法院作为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途径。
关于任意强制管辖权的接受问题,前面述及目前共有66个国家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款向秘书长交存了承认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声明,仅约为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的1/3,这显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目和比率。根据有关统计来看,国际法院从1946年正式成立到1989年,规约当事国接受任意强制管辖权的比率整体是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如其中1950年为57.3%,1980年为29.6%)。冷战结束后该比率稍微有所回升,但目前也仅为34%。而在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曾经有美国、法国和英国3个国家声明接受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但后来法国和美国又分别撤回了其接受声明,目前只有英国1个国家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表示接受任意强制管辖权。
上述这种情况早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切,并认为国际法院的有关潜能和作用需要进一步发掘和加强。[14]应该肯定的是,国际法院的工作状况在冷战结束后已经有了明显改善,目前的案源也比较充足,而国际法院在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的报告和其他一些场合中,仍然希望各国重申对法院解决争端的能力具有信心。[15]近年来一些有关联合国的改革文件或方案也反复呼吁或敦促尚未承认国际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国家承认其管辖权,包括提出接受这种管辖权国家的数目应该有一个实质性的增加(a substantial increase),而且要尽量减少保留。换言之,国际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改革与加强同时涉及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有更多的国家接受;二是要尽量减少保留。从目前的情况看,后一个问题似乎更为突出。
如果仅从一般的计量分析角度来看,接受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国家无疑需要一个实质性增加,或者说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作为《国际法院规约》的当然当事国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接受的实际效果或质量问题。2008年10月,时任国际法院院长希金斯法官在联大六委的发言中专门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她特别谈到了国际法院管辖权的性质,指出联合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迫使其成员国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权的国际组织。因此,所有提交给法院的案件都是基于当事双方的选择和同意。这种相互同意的要求意味着法院过于经常的是在审查对其管辖权的异议或先决性抗辩,而不是处理手头更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具体到任意强制管辖权接受情况及其效果时,希金斯法官也进行了一些计量分析。她指出在目前66个接受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声明中,绝大部分都是附有一定保留或条件的,这往往需要法院进行解释。截至2008年10月31日,国际法院共收到113起诉讼案件,其中有些后来又被撤销。自1946年以来法院共作出了97个判决,而其中将近一半是单独审理管辖权问题的。一个案件只有先经过管辖权阶段(jurisdiction/admissibility stage)确定了管辖权,才能进入实体审理阶段(merits stage),实际上就是一个案件变成了两个案件。这在解决实体争端方面很难说是一种有效的模式。[16]
然而,保留对法院工作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程序方面的牵制,而往往还有其他的负面效果。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各国在声明接受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时不但普遍附加保留,[17]而且其保留内容也可谓范围广泛,种类齐全,既有属事(ratione materiae)管辖权的保留,也有属时(ratione temporis)管辖权的保留,甚至还有所谓属人(ratione personae)管辖权的保留。关于属事管辖权的保留,即对争端事项的保留,是指法院只能针对当事方所同意的那些争端事项行使管辖权,对声明中所保留的事项则没有管辖权。《国际法院规约》第36条第2项虽然明确规定法院对于该项所列四个方面的一切法律争端具有强制性管辖权,但许多国家在其接受声明中又都提出了一些保留。如在前述澳大利亚、新西兰诉法国的核试验一案中,法国就坚持认为其在南太平洋进行的核试验属于其国防问题的保留范围,因此国际法院不应该行使管辖权。关于属时管辖权的保留,一般是指对于接受法院管辖权的时间和期限的规定。国家在接受法院管辖的声明中一般会提出一个特定时间,如五年或十年期限,期限届满再视情况予以更新或展期。而有些国家的声明是采取一种通知终止或变更的做法,即向联合国秘书长发出终止或变更接受法院管辖的通知,而且该通知自作出之时即产生效力。这种随时通知终止或变更的做法既可能阻止法院对某个特定案件的审理,也有可能使整个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变得毫无意义。[18]关于属人的保留一般是指国家所作出的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对某类特定的国家不予适用。如英国接受管辖的声明中就排除了其与其他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的争端,而其他一些英联邦国家也有类似保留。[19]
国际法院任意强制性管辖权的效果除了受到国家提出的各种保留的影响,还进一步受到规约自身规定的相互性条件的影响。规约第36条第2项规定各国发表的接受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只“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他国家”适用或有效,这就是所谓“相互性原则[20]”(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换句话说,国家之间接受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范围适用最低公分母原则,即法院对一个国家的管辖权与另一个国家接受同样的义务相联系。这种同样义务并不必要当事方在其声明中使用同一措辞或表述,但必须是双方的声明都同意将有关争端提交法院管辖。[21]
在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中,这种理论往往可能导致一个当事方可以依赖另一个当事方在其声明中所明确提出的条件或保留从而拒绝法院管辖权的情况,即承认其他国家可以采取一种“以彼之保留,为己之保留”的做法。这方面最典型的是1957年的挪威公债案。在该案中,作为原告的法国与作为被告的挪威当时都作出了接受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声明。法国据此于1955年7月6日向国际法院提交诉讼请求书,要求法院判决挪威债务人按照有关黄金条款偿付法国的公债。但挪威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意见,认为该案属于其国内法院管辖事项,而法国并没有用尽当地救济。挪威的反对意见还特别提到根据法国接受法院强制性管辖权时所作的保留,国际法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22]国际法院于1957年7月6日对该案作出判决支持了挪威的主张。法院指出,在本案两个当事国的声明中,挪威的没有保留,而法国的有保留。当涉及两个单边声明时,法院只能在这两个声明相重合的范围内行使其管辖权。对两个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进行比较表明,法国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范围比挪威的更狭窄;因此,法院据以行使管辖权的当事方的共同意志存在于法国保留所表明的这种狭窄的范围之内。[23]法院还援引了其1952年在英伊石油公司案中的判决词加以论证:“由于伊朗的声明比联合王国的声明更为有限,法院必须以伊朗的声明作为自己管辖的基础。”因此,法院认为自己对本案没有管辖权。[24]
美国曾在接受国际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时也是挖空心思提具保留的。美国抱怨过自己有关法院强制性管辖权的“不幸”经历:曾七次不同地试图将一个国家诉诸国际法院,却都没有成功。但近乎荒谬的是,其失败的原因不仅是其他国家没有接受强制管辖权,而且是美国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声明因相互性原则而对美国自己的适用。1946年美国在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时提出了所谓“康纳利保留”(the Connally Reservation),即对于任何美国自己认为纯属于美国国内管辖权事项的争端,美国不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这种“自裁”(self-judging)性质的保留可谓天衣无缝,如果想排除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美国可以随时将任何争端确定为纯属美国国内法院管辖事项。但是,这种保留不但受到国际上广泛的批评,同时可以为别的国家所利用。如在1957年的击落客机案中,保加利亚就根据相互性原则援引了美国的“康纳利保留”。法院因此判决保加利亚有权对美国决定属于保加利亚国内管辖的事项,因此,法院无管辖权。[25]
综上可见,国际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制度的限制,除了其固有的自愿性质外,还有国家的政治意愿问题。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愿意接受法院的强制管辖权,而部分接受管辖权的国家又提出了过多过分的保留。这不但严重削弱了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作用,而且因为相互性原则的适用对自身也会产生不良后果。针对这种情况,联合国有关机构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近年来的一些改革文件中都一再强调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争端中的作用,并敦促各国尽量全面有效地承认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权。从一般国际法的角度而言,国家在接受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时提具一定保留也是无可非议的,《国际法院规约》的相关条款中也并没有任何禁止保留的明确规定。但有些过分的保留,如由国家自己解释或确定何谓国内管辖事项的所谓自裁性质的保留,原则上都是无效的。对于这些保留,国际法院应该根据一般国际法和条约法的有关规定以自己的判断进行审理并作出最终裁定,以防止有关国家滥用保留的权利。当然,用一句古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考虑如何加强任意强制管辖权制度时,最关键的还是需要《国际法院规约》的各当事国充分认识到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中的作用和意义,尽可能广泛和有效地接受和利用法院的诉讼管辖权制度。以往的实践表明,有些国家在接受任意强制管辖权时提出了一些过分或无效的保留,最后的负面效应也都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因此,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明智的选择是应该考虑是否完全或至少部分地撤回现有接受管辖权声明中的一些非技术性质的保留;对于其他一些准备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国家来说,则应该尽量不提具保留。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国际法院任意强制管辖权的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