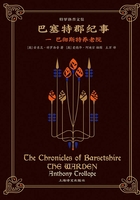
第5章 海拉姆的受施人
这个行动即将使巴彻斯特掀起轩然大波,可是那时候,像常有的那样,跟这个行动最有关系的人,却不是最先讨论这问题的是非曲直的人,然而当主教、会吏长、院长、总管和考克斯先生与克明先生各人按各人的方法忙着应付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也别以为海拉姆的受施人完全是消极的旁观者。那个法律代理人芬雷曾经去找过他们,问了些刁钻古怪的问题,激起了过奢的希望,促成了一个敌视院长的派别,并且像他自己比喻的,在敌人阵营里建立起了一支军队。可怜的老头儿们,不论这次调查弄清了谁是谁非,他们反正管保只会受到损害。就他们来说,这只是一场十足的灾难。他们的命运怎么能改进呢?他们需要的一切全不缺乏,一切舒适的用品全都供给了。他们有温暖的住房,丰衣足食,有毕生劳碌后的休息,以及晚年最可贵的珍宝,有个真诚、和蔼的朋友来关怀他们的悲伤,看护他们的疾病,在现世和来世,给予他们安慰!
约翰·波尔德把这些受施人置在他的保护之下,每逢他大谈起受施人的权利时,他偶尔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却用正义这个冠冕堂皇的词把心里的这种想法压了下去:“Fiat justitia ruat coelum。”[95]这些老人按理每年应当拿一百镑,而不是每天拿一先令六便士,院长应当拿两三百镑,而不是拿八百镑。凡是不公正的事一定不对,凡是不对的事一定应当加以矫正。如果他不做这件事,哪个别人会来做呢?
“按习惯法[96],你们每个人明明应当每年拿一百镑。”这便是芬雷传送进亚伯尔·汉狄耳朵里,亚伯尔·汉狄又传送进他的十一个弟兄耳朵里的重要的体己话。
约翰·海拉姆的受施人也是血肉之躯,咱们本不可以对他们要求太高。明确地答应每年让这十二个老头儿每人拿一百镑,的确动摇了他们大多数人。可是大邦斯却不肯受骗,他还得到两个附和的人来支持他的正统的看法。亚伯尔·汉狄是渴望钱财的人们的头领,得到了,哎呀,得到了较多的人附和。十二个人里有五个立刻相信他的看法是公正的,于是加上他们的头领,就占了养老院人数的一半。其余三个人生性摇摆不定,徘徊于两位头领之间,一会儿受到黄金欲的诱惑,一会儿又急于想向依然存在的权力讨好。
当时,芬雷提议由他们向负有监察职责的主教呈递一份请愿书,请求主教替约翰·海拉姆慈善事业的合法受惠人主持公道,然后把这份请愿书和所得的答复的副本送交给伦敦的各大报馆,这样把这问题宣扬开来。据他认为,这可以为将来的诉讼程序铺平道路。要是能使这十二个受害的遗产承受人全体签名画押,那当然最好,但是这办不到:邦斯是杀了头也不肯签名的。芬雷于是提议,倘若能够劝说十一个人来签署这份文件,那么那一个顽固抗拒的人简直可以给当作不配就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判断——事实上,就是把他当作Non compos mentis[97]——而请愿书就可以作为代表全体的意见了。但是,这也办不到:邦斯的朋友和他一样坚决,所以结果,只有六个“十”字画在这份文件上。而最气人的是,邦斯是会清清楚楚地签名的。那三个犹疑不定的人里,有一个多年来都夸口说他也有同样的本领,而且的确有一部《圣经》,上面具有他很得意地要人鉴赏的、他三十多年前的亲笔签名——“约伯·斯库尔庇特”。不过据说约伯·斯库尔庇特已经早把这种才学忘干净了,所以十分畏缩,不肯在请愿书上签名。其余两个犹疑不定的人都听他指挥,跟着他走。一份只有养老院半数人签名的请愿书,是绝起不了多大作用的。
请愿书那会儿正放在斯库尔庇特的房间里,等候着亚伯尔·汉狄凭他的口才所能争取到的其他签名。它上面的六个花押都正式画好了,是下面这样:
亚伯尔·汉狄 +
格雷戈里·穆迪 +
马修·斯普里格斯 +
等等,还用铅笔替那会儿料想会加入画押的弟兄们适当地标出了地方:单为斯库尔庇特一个人留了一大块空白,让他可以用清秀的书吏般的笔迹把他的亲笔签名写下来。汉狄把请愿书捧进房来,在那张小松木桌上摊开,这时正花言巧语、满心热切地站在一旁。穆迪拿着芬雷很周到地留下来的墨水匣跟在后边;斯普里格斯高举着一支墨水沾污了的旧钢笔,仿佛握着一柄宝剑似的。他不时企图把钢笔硬塞进斯库尔庇特那只不乐意接下的手里。
那位有才学的人的两个犹豫不决的帮手,威廉·盖舍和乔纳生·克伦普尔,正和他呆在一块儿。芬雷先生说过,要递请愿书,这会儿正是时候,所以这些人非常焦急,他们相信自己每年的一百镑,主要就要依靠当前的这份请愿书了。
“这个老傻瓜说,他能像有学问的人那样亲自签名,”贪婪的穆迪曾经向他的朋友汉狄嘟哝着说过,“咱们要是被这样一个傻瓜弄得拿不到这笔钱,那够多冤!”
“哟,约伯,”汉狄说,竭力想在自己的乖戾的、倒楣的脸上显出一丝赞赏的笑容,而实际上,他压根儿没能办到,“你原来已经预备好了啊,芬雷先生说来着。你瞧,就是这地方,”——他说着用褐色的大手指指到那张肮脏的纸上,——“签名或者画押,全都一样。来,朋友,要是那笔钱该是咱们的,那么越早越好——这是我的座右铭。”
“的确,”穆迪说,“咱们谁也年纪不小啦,咱们不能再等老‘肠线’[98]了。”
这些歹徒就这样叫唤我们善良的朋友。他原可以很轻易地原谅他们给他起这个绰号的,但是里面暗暗提到他的声乐乐趣的神圣来源,这连他那样的人也会给激怒起来的。我们希望他永远不知道这个侮辱才好。
“想想看,老比莱·盖舍[99],”斯普里格斯说,他年纪比弟兄们全轻得多,可是因为有一次喝醉了酒,摔进火里,所以一只眼给烧瞎了,一边脸蛋儿给烧通,一只胳膊也差点儿给烧断,因此,就容貌方面讲,他可不是最讨人喜欢的,“每年一百镑,尽着花。想想看,老比莱·盖舍。”他咧着牙可怕地笑笑,这一来把他遭到的不幸兜底儿显露出来了。
老比莱·盖舍对于人家的热忱一向麻木不仁。就连这样绝好的前途,也只能唤起他用受施人长袍的袖口去擦擦他的可怜的昏花老眼,一面轻声地嘟哝道,“我不知道,我不,我不知道。”
“可是,你是知道的,乔纳生。”斯普里格斯转身朝着斯库尔庇特的另一位朋友,继续说了下去。乔纳生·克伦普尔那会儿正坐在桌子旁边的一张凳子上,茫然地望着请愿书。他是个温厚、谦和的人,以前见过好日子,可是他的钱财都给不肖的子女胡花掉了,弄得他生活困苦,直到不久以前才给收进了养老院。从那天起,他无忧无虑,因此这个想使他心里充满新希望的企图,的确是一件残酷的行为。
“每年一百镑确实很不错,斯普里格斯老大哥,”他说,“我以前拿过将近这么多钱,可是那对我并没有什么好处。”他想到抢劫他的那些子女,不免低声叹了一口气。
“你又可以拿那么多啦,乔[100],”汉狄说,“这一次找个人替你稳稳妥妥地保管起来。”
克伦普尔又叹了一口气——他已经知道世上的钱财是毫无用处的,要是不受到诱惑的话,那么他一天拿一先令六便士也就快快活活,心满意足了。
“来,斯库尔庇特,”汉狄烦躁起来,又说了一遍,“你总不打算跟着老邦斯走,帮那个牧师来剥削咱们大伙儿吧。拿起笔来,朋友,取得你自己应得的权利吧。嗐,”他看见斯库尔庇特仍旧犹疑不定,便又说道,“我认为,瞧见一个人对自己的事都不敢上劲,那他就是最最没出息的人了。”
“为牧师就把钱全扔掉吗,唔,”穆迪咆哮着,“那帮饿疯了的乞丐,他们没把一切抢光以前,从不会满足的!”
“谁会来伤害你,嗳?”斯普里格斯劝说着。“让他们恶狠狠地望着你。你既然进来啦,他们就没法叫你出去——不会的,老‘肠线’即使有‘小腿’帮忙,也办不到!”说来很抱歉,会吏长本人却给叫着这个暗示他的大脚丫的粗鄙名称。
“每年可以得到一百镑,自己又毫无损失,”汉狄说了下去,“嗳呀!嗐,一个人怎么会对这么一块到嘴的肥肉还怀疑不信呢[101]——但是有些人的确是胆小的——有些人生来就没有勇气——有些人一瞧见绅士的衣服和坎肩就害怕了。”
唉,哈定先生,当乔·墨特斯和这个忘恩负义的煽动人争着要进养老院的时候,您要是在那场争执里听从了会吏长的劝告,那够多么好啊!
“怕一个牧师,”穆迪带着莫名轻蔑的神气咆哮着说,“我告诉你我怕什么——我只怕硬说软说,到头来从他们那儿还是什么也得不着——这是我对随便哪一个牧师都最害怕的事。”
“但是,”斯库尔庇特抱歉地说,“哈定先生可没有那么坏——他现在不是每天还多给咱们两便士吗?”
“每天两便士!”斯普里格斯轻蔑地嚷起来,把那只瞎眼的红窟窿睁得很大。
“每天两便士!”穆迪咒骂了一声,喃喃地说,“去他妈的两便士!”
“每天两便士!”汉狄嚷起来,“我还得拿着帽子为每天的两便士去谢谢那家伙,可是实在倒是他一年欠我一百镑。不,谢谢你,这你也许受得了,我可受不了。来啊,斯库尔庇特,你到底在不在这张纸上画押?”
斯库尔庇特犹疑不决、狼狈不堪地转过脸去看看他的两位朋友。“你觉得怎样,比尔·盖舍?”他说。
但是比尔·盖舍也想不出所以然来。他发出一种老羊叫的咩咩声,想表示他犹疑不决所感到的苦闷,跟着又嘟哝道,“我不知道。”
“拿过去,你这老瘸子,”汉狄说,把钢笔硬塞进可怜的比莱手里:“这儿,这样——啊!你这老傻瓜,你涂得这么稀里糊涂——唉——行了——这跟签得最好的姓名一样有效。”于是一大滴墨水便给认为是表示比莱·盖舍默认了。
“现在,该你啦,乔纳生。”汉狄转向克伦普尔说。
“每年一百镑确实很不错,”克伦普尔又说上一遍,“嗐,斯库尔庇特老大哥,怎么样呢?”
“哦,随便你,”斯库尔庇特说,“随便你,随便你怎么样都合我的意。”
钢笔于是塞进了克伦普尔的手里。他涂了一个模糊的、欹斜的、毫无意义的记号,代表乔纳生·克伦普尔所能表达的承认和同意。
“来啊,约伯,”汉狄说,事情的成功使他平和下来,“别让人家说,老邦斯有一个你这样的人听他支使——一个在养老院里一向和邦斯一样神气的人,虽然你从来没像他那样给邀去喝酒、奉承、胡扯些有钱有势的人的话。”
斯库尔庇特握着钢笔,在空中略略挥动了几下,可是依旧迟疑不决。
“你要是听我的,”汉狄说了下去,“干脆别在上面签名,跟别人一样,也在上面画个押就得啦,”——斯库尔庇特额上的疑云开始散去——“我们大伙儿都知道,乐意的话,你是会签名的,不过也许你不乐意显得高人一等,你知道。”
“是呀,画个押最好,”斯库尔庇特说,“一个人签名,其余的人画押,看起来也不好,是吗?”
“真太不好啦,”汉狄说,“喏——喏。”于是这个有才学的“书吏”弯下身去,在请愿书上留给他签名的地方画了一个大十字。
“这对啦,”汉狄扬扬得意地把请愿书收进衣袋时说。“咱们大伙儿现在同舟共济啦,那就是说,咱们九个人。至于老邦斯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或许会——”说来真巧,他刚一边撑着拐杖,一边握着手杖,一瘸一拐地走向门口时,竟然碰上了邦斯本人。
“唔,汉狄,老邦斯或许会怎么样?”那个头发花白的、正直的老人说。
汉狄嘟哝了一句,正打算走开,但是刚来的人的魁伟的身个儿却在门口堵住了他的去路。
“你在这儿没干好事,亚伯尔·汉狄,”他说,“这一看就明白。我想,你从来就没做过什么好事。”
“我可不去多管别人的事,邦斯大爷,”汉狄嗫嚅着说,“请你也别来管别人的事吧。我做的事跟你毫不相干——你到这儿来查看既没有好处,也没有坏处。”
“那么,我想,约伯,”邦斯继续说了下去,不理会他的对手,“如果非实说不可,你到底把名字附在他们的那个请愿书上啦。”
斯库尔庇特的样子仿佛羞得恨无地缝可钻。
“他签不签跟你什么相干?”汉狄说,“我想如果我们全想为自己请愿,我们并用不着先要你答应,邦斯先生,尽管你是个大人物。至于你趁约伯正忙的时候,不等人家请,就偷偷摸摸地跑进他的房间来——”
“我从小就认识约伯·斯库尔庇特,顶到现在六十年啦,”邦斯望着约伯·斯库尔庇特说,“那就是说,打他生下的那一天到现在。我认识他的亲娘,他妈和我小时候一块儿在那边教堂区里采雏菊,我跟他在一个屋子里住过十多年。因为这个,我用不着等他让,就可以走进他的房间来,而且也不是什么偷偷摸摸进来的。”
“你是可以这样,邦斯先生,”斯库尔庇特说,“你是可以这样,白天、夜晚,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而且我也可以随便把心里的话跟他直说,”邦斯眼睛望着这个老头儿,朝另一个继续说下去,“现在,我就告诉他,他糊里糊涂做了一件错事。他背叛了一个最好的朋友,被别人利用啦。别人不问他贫富、好歹、死活,压根儿就不管他。每年一百镑。你们这些个人难道这么笨,以为要是一年真有一百镑,是你们这样的人拿得到的吗?”他指着比莱·盖舍、斯普里格斯和克伦普尔。“咱们有谁做过什么值得拿这一半钱的事吗?全世界都不管咱们,咱们不能再挣钱糊口的时候,是给请进这儿来做绅士的吗?你们大伙儿凭你们的生活讲,不是和他一样有得花吗?”这位“演说家”指着院长住的那一边。“你们不是都称心如意了吗,嗯,而且比你们想要的还多?你们每人都乐意昧了良心[102],去得到使你们这么忘恩负义的钱吗?”
“我们只要约翰·海拉姆留下来给我们的钱,”汉狄说,“我们只要按照法律该归我们的钱;我们指望点儿什么,压根儿没有关系。凭法律应当是我们的,就该给我们,我们无论如何总得要。”
“法律!”邦斯说,把他知道如何表示的轻蔑全表示出来了——“法律!你知道有哪个穷人靠了法律,或是靠了律师变好了吗?约伯,芬雷待你会像那个人待你这样吗?你不舒服的时候,他会照料你吗;你倒运的时候,他会安慰你吗?你——”
“不会,大哥,也不会在冻得发慌的冬天晚上给你葡萄酒喝!他不会这样,对吗?”汉狄问。他为自己的锋利的俏皮话哈哈大笑,然后拿着那会儿已经变得强有力的请愿书,跟同伴们一起去了。
这件事实在也无法挽回,邦斯先生只好退回自己的房间去,对人性的脆弱感到厌恶——约伯·斯库尔庇特搔搔脑袋——乔纳生·克伦普尔又说了一遍,“每年一百镑倒确实不错”——比莱·盖舍又揩揩眼睛,低声喃喃说道,“我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