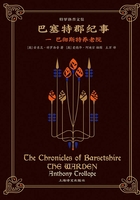
第4章 巴彻斯特的主教
波尔德马上到养老院去。那会儿已经是薄暮,但是他知道哈定先生夏天四点钟就吃晚饭,爱莉娜一到傍晚总乘马车出去兜兜,因此,他大概会发现哈定先生独个儿呆在家里的。他到达通向圣诗班领唱人花园的细铁门的时候,已经七点多了。虽然,像贾德威克先生所说的,六月里这样的天气真算很冷,可是傍晚倒是暄和、愉快的。小门开着。他拔开门闩,听见哈定先生大提琴的声音从花园那头传来。他走过草地,到了屋子前边,看见哈定先生在拉提琴,而且并不缺乏听众。这位音乐家坐在凉亭里边一张帆布椅子上,这样好把夹在膝间的大提琴放在干燥的石地上。在他面前,放着一个粗糙的乐谱架,上面摊开那部心爱的神圣的书,那卷煞费心血、极其珍惜的圣乐的一页,这部书曾经花去了那么多几尼[83]。在他四周,坐着、躺着、站着、靠着十个老头儿,是跟他一块儿寄居在老约翰·海拉姆篱下的十二个老头儿中的十个。两个“改革家”没有在那儿。我可不是说,他们心里知道自己对厚道的院长已经做了什么不当做的事,或是将要做什么不当做的事,不过新近,他们老是躲避开他,他的音乐已经不再合他们的脾胃了。
看看这些生活宽裕的老头儿的姿态和洗耳恭听的脸神,倒真怪有意思的。我并不是说,他们全能欣赏他们听到的音乐,不过他们却专心一志地想显得是这样。他们对于自己眼下的处境都很满意,所以决心要尽力来报答一下,叫主人也感到高兴。他们的确相当成功。圣诗班领唱人一向认为音乐是满含着近乎迷人的欢乐的,他想到自己爱护的老受施人全这么欣赏音乐,心头不禁大为高兴。他一直夸口说,养老院的这种气氛,简直使它成了一个特别适合崇拜圣塞西丽亚[84]的境地了。
有一个老头儿面对着哈定先生,坐在凉亭里边一圈长凳的那头。他把手帕平铺在膝上,那时候的确是在欣赏,——至少也是装得很好。他已经是个年过八十的人了,不过时光并没有多么损害到他的高大的身躯,——他的身个儿仍旧笔直、硬朗、匀称,额头开阔、厚实,边上长着几绺(虽然很少)稀疏的灰色鬈发。养老院的粗糙的黑袍子、裤子,以及有带扣的鞋都很适合他。他两手合起来,握着拐杖坐在那儿,下巴颏儿搁在手上边,成了一个大多数音乐家都乐于欢迎的听客。
这个人的确是养老院的“骄子”。积习相传,他们一向总得选出一个多少有权管辖旁人的人。虽然邦斯先生——这便是他的姓,他下面的弟兄们一向都这样唤他——拿的钱并不比别人多,他却端起了一副尊严的架子,而且很知道怎样保持着它。圣诗班领唱人喜欢管他唤作副院长,偶尔,没有旁的客人的时候,还不拘形迹地吩咐他一块儿在客厅壁炉旁坐下,喝上一大杯放在他身旁的葡萄酒。邦斯总喝完第二杯才走,可是任你再怎么挽留,却从来不肯喝第三杯。
“嗳,嗳,哈定先生,您太好啦,真太好啦。”第二杯酒斟满的时候,他总这么说,可是等那杯喝完,半小时过去以后,邦斯便直挺挺地站起身来,说上一句他的庇护人很重视的祝福的话,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他世故很深,不肯把这种舒适、美好的时刻延长下去,以免会变得不很愉快。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邦斯先生当然是最激烈地反对改革的。他对于想干涉养老院事务的那些人所感到的万分厌恶,连格伦雷博士也差上一筹。他彻头彻尾是一个国教信徒,虽然私下并不十分喜欢格伦雷博士。这是因为养老院里容纳不下博士和他两个这么相像的人,而不是因为什么意见上的不一致。邦斯先生认为,院长和他就很可以管理养老院了,用不着别人再来协助;他还认为,虽然主教按规定讲,是可以来巡视的,这使他有权受到和约翰·海拉姆遗嘱有关的所有人员的特别尊敬,然而约翰·海拉姆却从来没有打算叫一个会吏长来干涉他的事情。
不过当下,他心里却没有这种烦恼。他望着院长,仿佛认为这音乐是来自天上的,而演奏的人也是这样。
波尔德静悄悄地走过草地。哈定先生起先并没有瞧见他,继续把乐弓缓缓地拉过音调悲凉的琴弦,可是他不久便从听众的脸色上发觉,有个陌生人来了。他抬起头来,以坦率、殷勤的态度欢迎这位年轻的朋友。
“哈定先生,请您,请您别因为我来了就停下,”波尔德说,“您知道我多么喜欢圣乐。”
“哦!没有关系。”圣诗班领唱人说,一面把乐谱合起来,可是一眼看见老朋友邦斯的讨喜的央告的神情,便又把乐谱翻开。哦,邦斯,邦斯,邦斯,我恐怕你也只是个擅长拍马的角色吧。“好,那么我就把这拉完,这是主教最喜欢的一支小曲子。波尔德先生,待会儿咱们散散步,闲聊聊,等爱莉娜回来,给咱们弄点儿点心吃。”于是波尔德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坐下来倾听,或者还不如说是细想:在这样美妙和谐的音乐之后,他怎样才能把一个非常不和谐的话题最好地提了出来,搅乱这么殷勤、亲切地欢迎他的这个人心地的宁静哩。
波尔德觉得演奏没多大工夫便结束了,因为他感到自己有一个相当困难的工作得做。尽管老头儿们慢吞吞地一个个告辞,他几乎舍不得最后一个老头儿临末了的告别。
圣诗班领唱人对于他的光临,说了一句亲切的客套话,波尔德心里不禁一怔。
“挨晚的一次访问,”他说,“抵得上早晨的十次。早晨不过是礼节性的,真正友好的聊天,向来总在晚饭以后才开始。这就是我干吗总早吃晚饭,为的就是好尽量多有点儿时间聊聊。”
“您说得很对,哈定先生,”波尔德说,“可是我恐怕,我把事情给弄颠倒啦。我很抱歉,这时刻拿正经事来麻烦您。我现在就是为这种事来找您的。”
哈定先生显得烦扰、纳闷,这个年轻人的嗓音里有点儿什么叫他觉得这次会面是不愉快的。他的亲切的欢迎竟然遭到这样的拒绝,这使他有些畏缩。
“我想跟您谈谈养老院的事。”波尔德说了下去。
“噢,噢,凡是我可以告诉你的事,我都挺乐意——”
“就是关于账目的事。”
“唔,亲爱的朋友,这我可没法告诉你,因为我跟个孩子一样,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的就是,他们每年给我八百镑。你去找贾德威克,那本账他全清楚。还有,请问你,可怜的玛丽·琼斯的腿将来还可以走路吗?”
“唔,我想可以,假如她小心的话。不过,哈定先生,我希望您不反对跟我谈谈我对养老院不能不说的一些话。”
哈定先生深深地长叹了一声。他的确反对,激烈地反对跟约翰·波尔德谈论任何这样的问题,可是他没有贾德威克先生办事的那种圆滑手腕,不知道怎样摆脱掉临头的灾难。他伤感地又叹息了一声,没有答话。
“我挺尊重您,哈定先生,”波尔德继续说下去,“非常尊敬您,出自衷心的——”
“谢谢你,谢谢你,波尔德先生,”圣诗班领唱人有点儿不耐烦地抢着说,“我很感激,可是别谈这些。我和别人一样,也可能犯错误——非常可能。”
“但是,哈定先生,我非得把我的意思说出来,要不您还以为我要做的事里有什么私怨哩。”
“私怨!要做的事!嗐,你总不打算割断我的喉咙,或是把我交给教会法庭[85]——”
波尔德想笑又笑不出。他非常认真,坚定不移,没法拿这件事来开玩笑。他沉默地朝前走了一会儿,才又展开攻势。哈定先生手里仍旧拿着琴弓,这时候一直迅速地在拉着一只假想的大提琴。“哈定先生,我恐怕咱们有理由认为,约翰·海拉姆的遗嘱没有严格地执行,”年轻人终于说了,“我受托来调查一下这件事。”
“那很好,我一点儿也不反对。现在,咱们一个字也别再提啦。”
“还有一句话,哈定先生。贾德威克叫我去找考克斯和克明,我认为我有责任去向他们要一份关于养老院的报告。这么一来,我也许会显得是在干涉您的事情,我希望您能原谅我这么做。”
“波尔德先生,”另一个站住脚,相当严肃地说,“如果你很公正地去做,对这件事全按实说,也不用什么不光明的武器来达到你的目的,那也没有什么要我原谅的。我想你是认为我不该拿养老院给我的那笔收入,那笔钱该由别人拿。不论人家会怎么做,我决不会因为你和我意见不一,损害了我的利益,便认为你有什么卑鄙的动机:请你只管做你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的事,我不能帮助你,也不会怎样来阻碍你。不过,我要告诉你,咱们俩不论怎么谈论,一点儿也不能对你的见解有帮助,也不能对我的见解有帮助。爱莉娜乘马车回来啦,咱们进去吃点儿点心吧。”
可是波尔德觉得经过方才这件事以后,他实在不能安安逸逸地跟哈定先生和他女儿一块儿坐下,因此很忸怩地托故谢绝了。他走过爱莉娜的小马车时,只脱帽鞠了一躬,撇下爱莉娜失望而惊讶地望着他离去。
哈定先生的态度的确叫波尔德深信不疑,院长是觉得自己的脚跟站得很稳。这几乎使波尔德认为,他是毫无正当的理由就来干涉一个正直可敬的人的私事,可是哈定先生本人却偏偏很不满意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首先,为了爱莉娜,他希望能认为波尔德人很不错,并且能喜欢他,然而他却实在禁不住对他的傲慢举动感到厌恶。他凭什么来说,约翰·海拉姆的遗嘱没有公正地执行呢?可是接下来,他心里就想到这问题:那份遗嘱到底是不是公公正正地在奉行着?养老院是为那十二个老头儿建造的。约翰·海拉姆的意思是说,养老院的院长该从那笔遗产里领取比那十二个老头儿全体所领取的还多得多的钱吗?约翰·波尔德会不会是对的?养老院的可敬的院长在过去十多年里,会不会是不正当地拿了别人合法应得的收入呢?他的生活一直非常快活平静,受人尊敬。如果在光天化日下,他们竟然证明出来,他吞没了八百镑不应该拿的钱,而他又绝对无法归还出来,那怎么办呢?我并不是说,他害怕真是这种情形,不过他心里这会儿第一次掠过了怀疑的阴影。从那天晚上起,有好多好多天,咱们的慈祥恺悌的院长既不快乐,也不安定。
那天晚上,哈定先生茫然不安地坐着呷茶的时候,这种想头,这些最初的十分痛苦的时刻,使他烦闷不堪。可怜的爱莉娜觉得一切都不对头,可是她对于那天晚上烦闷的理由,却只想到她的情人身上,以及他的突然无礼的离去。她以为波尔德和她父亲一定起了一场争执。她对他们俩都有点儿生气,虽然她不想向自己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
哈定先生在就寝前和就寝后(他躺在床上有一会儿睡不着)把这些事细想了好半天,自己问自己,他究竟有没有权领取他所享有的收入。不论他陷到这样一个境况中多么不幸,没有人能说他应该一开头便拒绝担任这个职务,或是随后应该不要这笔收入,这一点至少似乎很明白。全世界——意思是说,仅限于英国国教的教会界——都知道,巴彻斯特养老院院长的职位是一个很舒服的闲缺,但是没有人曾经因为接受了这个闲缺而受到指责。反过来说,倘若他拒绝了,他会遭到多少指责啊!当这个职位出了缺,派他担任的时候,如果他说自己有点儿顾虑,不愿意每年从约翰·海拉姆的产业里领取八百镑,宁愿让一个陌生人去拿它,那么人家会认为他多么愚蠢呢!格伦雷博士会怎样大摇起他的聪明的脑袋,还去和教堂区的朋友们商量,万一这个可怜的低级驻堂牧师疯了,把他送到哪一个适当的收容所去!如果他接受这个职位是对的,那么他很明白,拒绝这个职位的任何一部分收入都会是不对的了。这个推荐权是主教的一项很有价值的附属权,他当然无权去贬低授给他的这个尊荣的职位的价值,他当然应该支持自己的教会。
但是不知怎么,这些说法虽然似乎很有理,却并不多么令人满意。约翰·海拉姆的遗嘱是不是公公正正地执行了呢?真正的问题在这儿:如果没有,他是不是特别有责任应该设法公公正正地来执行呢?他特别有责任,不论这种责任对他的教会多么有害——不论他的赞助人[86]和朋友们会多么厌恶这种责任。他想到朋友们的时候,脑子里便愁闷地转到他的大女婿身上。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他肯把这件事交给会吏长,让他去战斗,格伦雷博士会多么坚强地支持他,但是,他也知道,他没法为自己的怀疑在他那方面得到同情,他不会得到友谊,内心也不会得到安慰。格伦雷博士非常乐意代表卫道者[87]奋起反抗一切来人,但是他是根据教会绝无过错[88]这种令人厌恶的立场,而这么做的。这样一场斗争,对哈定先生的怀疑不会带来什么安慰。他倒不是急于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急于要消除自己的怀疑。
我前面已经说过,格伦雷博士是主教区里实际工作的人,他父亲那位主教,多少是喜欢过悠闲生活的。这是实情,不过主教虽然一向不好活动,他的品德却使认识他的人都喜欢他。他和儿子恰巧相反,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异常反对夸耀权力和讲主教的排场。然而他儿子早年便能做到他年轻时所做不好、而现在年过七十已经做不了的事,这对他目前的地位说,也许倒很不错。主教知道怎样款待他区里的教士,怎样跟教区长的太太们闲扯家常,怎样安抚副牧师们,然而却需要会吏长的坚强手腕去应付那些在教义上或是生活上桀骜不驯的人。
主教和哈定先生热忱相爱。他们一块儿生活到晚年,以教士的身份在工作和谈论中共同消磨了许多岁月。当一个做了主教,另一个还只不过是个低级驻堂牧师的时候,他们就常呆在一块儿。可是从他们成了亲家,哈定先生做了院长和圣诗班领唱人以后,他们简直相依为命了。我可不是说,他们共同管理这个主教区,不过他们花了不少时间去讨论负责管理的那个人,制定了一些小办法来平息他对玩忽教职的人的愤怒和缓和一下他想支配教会的雄心。
哈定先生打定主意去向他的老朋友倾吐一下心事,说明自己的怀疑。他于是在约翰·波尔德冒昧无礼地来访的第二天早晨,便上主教那儿去了。
顶到这时候,攻击养老院的这些使人痛苦的举动,没有一点儿风声传到主教的耳里。他当然听说过有人质问他有没有权每年给予一个闲缺八百镑,就像他不时听到巴彻斯特这座一向淳朴、宁静的城里出了一件特别不道德的行为,或是一场丢脸的骚动一般,但是碰到这种时候,他所做的和要求他做的,便是摇摇脑袋,请他儿子,那位“大独裁者”,去照顾着,不让教会受到损害。
哈定先生不得不先说上一大套,才使主教听明白了他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不过我们不必听他说那一套。起先,主教只劝他采取一个步骤,只提出了一个补救办法,在他的处方书里,也只有一味药效力极大,可以医治这么严重的毛病——他所开的药就是去找会吏长。“叫他到会吏长那儿去。”哈定先生提到波尔德的拜访时,主教一再地说。“会吏长在这方面会帮你把事情安排好的。”当他的朋友踌躇地提到自己的处境是否正当的时候,主教亲切地说。“没有人能把这一切办得像会吏长那么好的。”但是这一味药虽然剂量很大,却没有能安住病人的心。说真的,它差点儿引起了呕吐。
“但是,主教,”他说,“您看过约翰·海拉姆的遗嘱吗?”
主教认为,三十五年前他初就职的时候,大概看过,但是他不能肯定地这么说,不过他知道得极清楚,他绝对有权任命院长,而院长的收入是早经决定了的。
“但是,主教,问题是谁有权决定呢?如果像那个年轻人说的,遗嘱上规定,产业的收入应当分成一份一份,那么谁有权更改这些规定呢?”主教模糊地认为,这些规定随着时间的消逝自行更改,而教会的一种限制法规,限制了那十二个受施人由于产业增值而稍增收入的权利。他提到传统,讲了半天用实例来证明目前这种办法的许多学者,接着又详谈了一番,在享有圣俸的教士和某些依靠救济的穷老头儿之间,保持适当的等级与收入上的区别,是处置得宜的,最后重又提到去找会吏长,这样结束了他的议论。
圣诗班领唱人沉思地坐在那儿,盯视着炉火,一面听着他朋友的温和的议论。主教的话里多少有点儿安慰,可是却不是持久的安慰。他的话使哈定先生觉得,许多别人——真个的,教会里所有的别人——都会认为他没错,可是这却没有能证明给他看,他的确没错。
“主教,”他们俩静坐了一会儿后,他终于这么说,“我要是不告诉您我为这件事觉得很烦闷,那我就欺骗了您和我自己。假如我不能和格伦雷博士所见相同!——调查之后,我发觉那个年轻人是对的,我是不对——那怎么办呢?”
这两个老头儿坐得很近——非常近,因此主教可以把手放到另一个的膝上。他把手伸过去,轻轻按了一下。哈定先生知道得很清楚,这一下是什么意思。主教提不出什么进一步的论点,他不会像儿子那样为这件事战斗,他不能证明圣诗班领唱人的怀疑全是毫无理由的,但是他可以同情他的朋友,他真就这么办了。哈定先生也觉得他已经获得了来取的东西。于是他们又静坐了半晌,接着主教露出一点儿平时少见的急躁,着力地问他,这个“可恶的多管闲事的人”(指约翰·波尔德)在巴彻斯特有没有朋友。
哈定先生早就打定主意,要把一切全告诉主教:讲明女儿的恋爱和自己的烦恼,说出约翰·波尔德既是自己未来的女婿、又是目前的敌人这种双重身份。虽然他觉得这很不是味儿,不过现在倒是该说的时候了。
“主教,他跟我家就很亲密。”主教直眉瞪眼地望着。他并不像儿子那样主张维持正统和教会的战斗精神,但是他还是搞不明白,国教的这么一个公敌,怎么可以给很亲密地接待进哈定先生这样一个坚定的柱石的家里去,而且又是这么受他欺侮的养老院院长的家里。
“说真的,我个人很喜欢波尔德,”心地公正的受害人继续说下去,“而且‘老实’告诉您”——他把这个糟透了的消息迟迟地说出来——“我有时候还认为他可能会做我的二女婿哩。”主教并没有失声尖叫出来。我们相信他们因为身任圣职,所以失去了这么做的权力,不过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碰上一个腐败的法官,和碰上一个尖叫的主教一样容易。话虽如此,他还是显得仿佛要不是因为他穿了长坎肩,他早就尖叫出来了。
这是会吏长的一个多么好的连襟啊!巴彻斯特教堂区的一次多么好的联姻!甚至是主教公馆的一位多么好的亲戚!主教的简单的头脑里觉得,约翰·波尔德如果有极大的权力的话,一定会把所有的大教堂,也许还把所有教区教堂,全部封闭起来,把什一税[89]全部分给循道公会教徒[90]、浸礼会教徒[91]和其他的旁门左道,把主教完全消灭掉,并且使铲形帽和麻布袖[92]变得跟头巾、凉鞋和麻衣[93]一样不合法!把这样一个歹人,一个怀疑牧师的廉洁,大概还不相信三位一体[94]的人,带到教会的神秘的安乐窝里来,这可真不错!
哈定先生瞧出来,他透露的这消息起了多大的影响,几乎后悔不该直率地明说了,但是他却尽可能设法去减轻他朋友和赞助人的伤感。“我并不是说,他们已经有了婚约。要是有的话,爱莉娜会告诉我的。我很知道她,相信她会这么做的,可是我瞧得出来他们彼此相爱。作为一个男子汉,作为一个父亲,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他们亲近。”
“但是,哈定先生,”主教说,“如果他是你的女婿,你怎么好反对他呢?”
“我并不想反对他,是他在反对我。假如得采取什么步骤来自卫,我想贾德威克会做的。我想——”
“哦,这一点会吏长会瞧着办的:即使这个年轻人跟他的关系比连襟还亲,会吏长也决不会不去做他认为正当的事的。”
哈定先生提醒主教,会吏长和这个改革家还不是连襟,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是连襟。他硬要主教答应,在做主教的父亲和做会吏长的儿子讨论到养老院的时候,决不要提起爱莉娜的名字。接着,他告辞出来,撇下那个可怜的老友惊愕惶惑、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