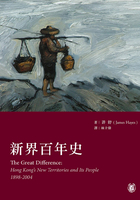
新界租約時期的習慣法
陳奕麟近期出版的一本書很值得注意,雖然這本書的主題除了新界租約初期,還談到其結束,不符合這裏主要按時間順序的敘事。(77)他根據人類學田野調查和檔案研究,從一個不同的角度探討這個範疇,他指出,港府與大多數香港史家和人類學家眼中的「傳統社會」,其實已因地籍整理而改變。此外,殖民政府的土地政策,以及租借新界時期實行的新土地登記制度,也繼續改變這個「傳統社會」,而變化之大,他甚至認為足以在副標題中用「殖民實踐的虛妄」(“The ‘Fictions of Colonial Practice’ ”)來概括。在標題中還有他所形容的土地「不斷變化的現實」。
地籍整理肯定令傳統社會結構出現重大改變,而英國接管新界後,海上和陸上的警務工作提升了公共安全,進一步改變它們。另外,鄉事派游說團體在二次大戰前後和日佔時期經常提出的主題,無疑是因政府的土地政策(儘管是為應對不斷變化的情況)而出現,這個主題是:港府剝奪了新界居民在中國統治時期享有的權利。(78)陳奕麟也正確地指出,殖民政府的規則和條例不斷改變,可稱為「以規訓的方式重新整理日常生活」;(79)這個觀察可在納爾信(Howard Nelson)那裏獲得印證,納爾信根據在1967-1968年所做的鄉村田野研究,認為香港政府的效率提升,並且與居民的生活有更密切的接觸,「對中國社會組織造成重大干擾」。(80)至於「土地不斷變化的現實」,這點無法否認,不過促使這種情況發生,是因為需要彈性地決定新的(並能為人接受的)補償方式。(81)
但是,若說殖民政府「不自然地扼殺」習慣法「可能出現有意義的變化」,(82)我看不出有這種情況。我在上文已提供了審視這些說法的背景:在地籍整理後,傳統文件再沿用了至少五十年;關於繼承、受託人和司理的登記冊更新,是由鄉村提出並在那裏審視;以及在過去幾十年村民大多忽視做這些事情,因為根據直至1950年代仍然主宰農村生活的習慣法安排,所有人都知道誰擁有哪些東西,可以行使什麼權利,所以覺得更新登記冊是多此一舉(見第79-84頁連註釋)。
陳奕麟的各種看法應當另外再深入探究,這裏無法詳細討論,但我必須強調,到那時候,許多甚至大部分新界鄉村的外貌和生活方式,幾乎無異於租借新界初期;新界居民的心態也反映那個時代仍然頗為原始的環境。我還必須指出,鄉村地區採用的習慣法和實踐很有活力,這是我得到的印象。
鄉村世界在1960-1970年代急速變化,習慣法已逐漸無法繼續沿用,而新界民政署在新界快速發展的時候,日益忙於處理其他責任。但即使如此,習慣法仍保留了一些舊日的活力。根據1975-1982年間我在荃灣的經驗所見,習慣法在自治的地方傳統中,仍然是生氣蓬勃的過程。(83)如有需要,它也能夠創新,祖、堂司理因時制宜的做法就是例子:在政府收地之後,這些司理須要諮詢成員的意見,並決定應如何在成員間分配現金賠償或換地證;到了這個時候,這些成員被認為包括未成年人,甚至嬰兒和婦女。(84)進入1980年代,村代表和宗族耆老在處理出現的問題時,愈來愈力不從心;(85)但是,與土地有關的習慣法對於維繫原居民社會(包括那些已居住在大量新村的人)和賦予他們認同感仍然很重要(86)——甚至到了新界租約屆滿之時,所有相關的人都清楚明白這點。(87)由於上述原因,我所採取的路向,不同於陳奕麟和其他研究這些課題的人。(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