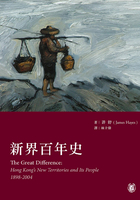
丈量土地的原因
身為特派專員的駱克(奉倫敦的訓令)密切關注土地情況,尤其是擁有權的登記、從地產獲得的稅收、稅款向誰徵收,以及如何徵收。(3)
他很快發現,中國的土地管理制度有重大缺失,不能襲用。以下描述指出了一個問題:
所有與新界土地有關的文件,都登記在新安縣的田冊,但該冊只是地契登記冊,而不是土地業權登記冊……
大部分有價值的土地,都不只一方擁有業權,這種情況造成非解決不可的重大困難,但如果每個業權單獨來看,它似乎沒有什麼不妥當。
長沙灣的土地糾紛很能代表這種難題,這個地方位於九龍西北沿岸,直接面向香港島和已聞名遐邇的維多利亞港。擁有這樣的地利,它確實是「有價值的」土地:
……這幅長沙灣的土地包括前灘和前方海域,有四個不同家庭聲稱擁有這塊地,他們都各有業權憑證。兩份關於同一幅土地的業權憑證,是直接由兩廣總督按照欽命授予。另外兩個業權憑證是在《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定前發出,來自新安知縣主持審判後發出的歸屬令,一名知縣裁定這幅土地屬於鄧氏,另一名知縣則把它判歸趙氏。(4)
地契登記制度會製造這種混亂,但問題還不止於此。除了缺乏準確的丈量記錄和新安縣的田地冊籍已經過時外,更大的問題是稅收是掌握在一些中介人手中,這些中介人向耕作的農民收租,再向官府完納應繳的田賦。
這些「收租主」(rent charge owner)(港府也用「完糧人」〔taxlord〕一詞)(5)是獲得地皮權和地骨權的個人或家庭,這些權利可能是過去由朝廷賞賜,或者向當局購買土地得來。(6)他們的土地登記於縣的田冊,但通常冊上所載的人名,是已死了幾百年的業主。他們的後人並不親自耕種田地,而是向擁有地皮權(實際上是耕作權)的人收取白銀或米糧作為租金,這種地皮權屬於可續租的永久租約。他們也向另一些人收款,這些人以沒向官府登記的傳統契約(通稱「白契」,有別於已登記的「紅契」),從原來的承租人手上買下地皮權。本地習慣法是准許這種買賣的,條件是須向地骨主(即已登記在冊)繳付相同的租金,通常金額會在買賣契約中列明。(7)一般來說,地骨主通常是祖或堂這種由司理管理的宗族信託組織,但也不完全一定。(8)
那些根據習慣法擁有地皮權的人,雖然世世代代在使用他們的土地,但無人擁有已向官府登記的業權憑據,而只有由地骨主定期重新發出的「永久租約」,或者傳統的「白契」。簡言之,這些人在官府眼中是隱形的,因為他們在州縣田地冊籍中並不存在。一名曾出席1860年舊英屬九龍移交的香港官員,憶述中國官員一句態度輕蔑的話,應該非常典型地顯示他們怎樣看待這群數目眾多(如果是附屬的)的人。(9)地骨主似乎也不認識他們,因為田土法庭成員發現,許多地骨主不清楚自己的租戶是誰,只要能收到租他們就心滿意足。(10)
不久又發現另一個不正常現象,就是那些登記了業權的地主,把他們在地方上的權利擅自擴大。在這些事例中,載於地契登記冊須向官府繳稅的區域,遠少於佃戶正在耕作的土地。有田土法庭成員報告了一個這類事例,顯示實地的真正情況:不但原本獲授予的土地面積很小,所在地點很含糊,並且在宣稱擁有土地的宗族內,擁有權也很混亂。(11)就是這樣,擁有地骨的家族暴富起來,官府的土地收入則毫無寸進。(12)
即使初步調查的範圍有限,但在殖民地政府眼中,這種情況不可接受,因此有必要將土地的使用納入法律規範,並按之分配繳交田賦(1899年後變為官地地稅)的責任。要達成此目標,最好的方法是盡早在新界丈量土地、劃界和整理地籍。以成本和工作量而言,這是一項重大舉措,在中國很少進行。(13)事實上,駱克等人指出的情況,在中國大陸一直持續到1930年代及之後,而少數幾個實行類似改革的例子,證明香港政府決定着手這項工作十分正確。(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