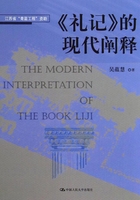
三、《礼记》的流传及研习
《礼记》作为孔门弟子和儒家后学研习《礼经》之“记”的汇编,历代研究著述颇丰,代不乏人。
汉末党锢之祸、三国鼎立,经学衰落,而“郑君党徒遍天下,即经学论,可谓小统一时代” 。自东汉学者马融、卢植,尤其是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后,《礼记》逐渐被接受和传习,始与《仪礼》、《周礼》鼎足为三,独立成书。
。自东汉学者马融、卢植,尤其是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后,《礼记》逐渐被接受和传习,始与《仪礼》、《周礼》鼎足为三,独立成书。
魏时王肃不好郑氏学,亦博古通今,遍注群经,时称王学,皆立于学官,因此,《礼记》也第一次为之立学官。东晋时,《礼记》又立为博士,其传习胜过《仪礼》了。魏晋南北朝时,王肃、孙炎、刘世明等先后为《礼记》作注,沈重、熊安生、皇侃又为之作“义疏”。
隋朝之博士,“三礼”之学亦宗郑氏。唐初李世民命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为郑注作疏,著成《礼记正义》,并列为科举考试定本,《礼记》被列为“九经”之一,自此《礼记》被归为经书之列。唐贞观中勅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又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根,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陈浩之流,益如莛与楹矣” 。
。
宋代朱熹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摘出,与《论语》、《孟子》并行,是为“四书”。宋儒研习《礼记》成就最显著者当属宋卫湜《礼记集说》,自作前序、后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详,该书“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 。
。
元代研究《礼记》之作影响较著者当数吴澄《礼记纂言》和陈澔《礼记集说》。《礼记纂言》重定篇第,“其书每一卷为一篇,大旨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于左” 。《礼记集说》较之郑注、孔疏的典瞻,显得浅显易明,较之卫湜的卷恢浩繁,则显得简便,“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
。《礼记集说》较之郑注、孔疏的典瞻,显得浅显易明,较之卫湜的卷恢浩繁,则显得简便,“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 。
。
明永乐中,胡广等敕修《礼记大全》,采掇诸儒四十二家,始废郑注改用陈澔《礼记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士,好之者终不绝也。明人关于《礼记》的著作,见于《四库存目》者甚多,然几无可称道者。其中,如郝敬所撰《礼记通解》二十二卷,“于郑义多所驳难,然得者仅十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 ,是亦宋学习气所使然。
,是亦宋学习气所使然。
清初尊宋,中期兼采汉、宋。这一时期,《礼记》研究的著作有纳兰性德的《陈氏礼记集说补正》、张廷玉等的《日讲礼记解义》、江永的《礼记训义则言》、杭世骏的《礼记集说》、江绂的《礼记章句》、孙希旦的《礼记集解》、朱彬的《礼记训纂》、郭嵩焘的《礼记质疑》。其中,孙希旦的《礼记集解》博采郑注、孔疏以及宋、元诸儒之说,而断以己意。“然清乾嘉学派重考据,《礼记》的研究不及《仪礼》、《周礼》之盛……对于《礼记》的研究,不过重在其中若干篇 (如《礼运》、《王制》等)的‘微言大义’,以宣扬所谓孔子托古改制之义以及儒家的大同理想。因此清代虽号称‘经学复盛’,然于《礼记》之学的研究,则未堪其称。清人于《十三经》,唯《礼记》无新《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