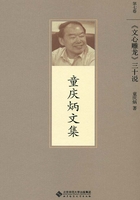
三、我研究《文心雕龙》的旨趣
(一)重点在研究文学理论要点,阐述文学理论范畴
《文心雕龙》研究有广阔的空间,每位研究者都能寻找到自己的空间。如对《文心雕龙》原文的校对、注释、疏解,对《文心雕龙》文体的专门研究,对《文心雕龙》文学史论的研究,对《文心雕龙》文章立论的研究等,我的兴趣则在对《文心雕龙》文学理论要点的研究上面。《文心雕龙》是不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呢?有人认为只是文章理论,并不包含文学理论,或者说根本就不是文学理论著作。按刘勰自己的说法,他的《文心雕龙》属于“论文”的著作。这里关键是对“文”的理解,以及《文心雕龙》中对“文”的涵盖情况。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在对《原道》篇“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的注释中,他先引了他的老师章太炎的《文言说》,阐述泛文学观念,随后又引了阮元的《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阐述“必沈思藻翰”的文学观,难得的是黄侃没有局限于章太炎的泛文学观念,认为阮元的观点也不可废。黄侃提出三种文学观来研究《文心雕龙》,他说:“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这基本上是用章太炎的泛文学观。的确,《文心雕龙》所包含文体极多,其中一些就在章太炎所理解的文学范围内。接着,黄侃又说:“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稍小于前,而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这是第二种文学观,其范围比前面的泛文学观要缩小一些。黄侃接着说:“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摛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8]黄侃所言切合《文心雕龙》实际,是实事求是之论。《文心雕龙》中《神思》以下各篇,的确是论属于现代意义的文学,其中所引属于现代意义的文学作品如诗词歌赋占着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文心雕龙》有文章学内容,但却属于文学理论著作。
因为《文心雕龙》中有丰富的文学理论,我自己本人又长期从事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所以我的兴趣很自然地就在《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的要义上面。为了把《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要义挖掘出来,我认为最值得做的是文学理论的“范畴”研究。“原道”、“奇正”、“感物吟志”、“神思”、“体性”、“风骨”、“通变”、“情采”、“比兴”、“夸饰”等也就成为了我研究的重点。我的立意是要从《文心雕龙》里面概括出一些文论学说来,“道心神理”说、“奇正华实”说、“以情观物”说、“感物吟志”说、“因内符外”说、“风清骨峻”说、“情经辞纬”说、“比显兴隐”说、“心物宛转”说、“阴阳惨舒”说等三十说就是我十余年来初步的研究成果。
(二)重视古今比较,揭示普适意义
我从长期的文学研究、文学教学和文学创作中体会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欣赏总是带有一定的共同规律的。例如,古今中外的文学都要讲“情”,完全没有感情的文学是没有的,“情”的表现有一定的规律,合乎规律其情就感人,不合乎规律其情就不感人。又如,文学创作都要讲想象与虚构,完全没有想象与虚构的创作是没有的,而想象与虚构也有其共同性,揭示想象与虚构的共同性,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再如,文学表现最终都要落实到辞采上面,完全不讲辞采的文学表现是没有的,而文学的语言表现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如何把语言表现的规律寻找出来,无疑也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这些就是我所理解的关于文学的普适性的东西。我的兴趣是对古今中外的这些普适性的东西进行对比,看看古今中外在这些问题上的同与异。我觉得这样做有助于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建设。今天的文学理论绝不是与传统的文学理论完全隔绝的、没有联系的、没有承继关系的。我的这种研究工作带有一定的创造性。我喜欢创造,我很高兴我在《文心雕龙》研究的古今对比上面的“创造”,已经得到一些同行的认同。如陈良运先生是当代研究古代文论的重要学者,他在读了我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一书后,写了《找到解释古文论的一把钥匙》一文,其中谈到的我对刘勰《情采》篇的研究,有过这样一段评价。“童先生对于刘勰‘蓄愤’、‘郁陶’的阐释,也出人意外。《文心雕龙·情采》云‘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在我的印象中,历来《文心》的注、释者,对‘蓄愤’与‘郁陶’者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或是从‘真诗’与‘伪诗’角度和文之优劣原因方面解释,童氏从心理学找到了新的角度——‘情感的一度转换’。阐释的焦点在‘蓄’与‘郁’二字,‘蓄’是一个过程,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浑浊到澄净,由杂乱到富于美感。‘郁’,郁结、郁积之意,与‘蓄’互文见义,皆指情感在心中蓄积、郁结……总起来看,诗情一般不是即兴式的感情,要有一个蓄积、回旋和沉淀的过程。这样,自然的感情,才能转变为诗情。刘勰强调‘为情而造文’需要有情感的‘蓄愤’、‘郁陶’,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是从自然到诗的情感的一度转换。(他稍后又谈了‘联辞结采’——情感的二度转换,此不赘述。)这个道理,今天看起来并不深奥,童氏之‘深’就在于发现了‘蓄’与‘郁’的现代价值,他将此与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沉思’说(见《抒情歌谣序言》)、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再度体验’说(见《论艺术》)、美国美学家苏珊·朗格的‘非征兆性情感’说(见《情感的形式》)进行比较,诸说虽然‘产生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但‘都是在探讨文学艺术的普遍规律’;早于他们一千多年,‘刘勰的确发现了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艺术规律’。笔者在此也要说一句:刘氏当会心于童庆炳的再发现!我坚信,古今中西的比较将是研究《文心雕龙》一条有前途的新路线。”
(三)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
“文化诗学”是我1998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方法。实际上,在我开始研究《文心雕龙》的时候,就较为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有人对我的“文化诗学”的方法不甚了然,在此很难详细论述,这里仅把“文化诗学”的三个要点两种品格简单地介绍一下。
(1)双向拓展的方法。
在研究文学问题(作家研究、作品研究、理论家研究、理论范畴研究等)的时候,一方面向宏观的文化视野拓展,以文化的眼光来关注研究的对象,把研究对象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不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研究。因为任何文学对象都是更广阔的文化的产物。这样,研究文学和文论都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关联”、“社会的关联”。恩格斯曾经称赞过黑格尔的“伟大的历史感”,认为“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在历史中有一种发展、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认为他“在现象论中,在美学中,在历史哲学中,到处贯穿着这种伟大的历史观,材料到处是历史的,即放在与一定的历史联系中来处理的”。恩格斯的观点表明了一种历史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历史优先”是文化诗学的第一原则。例如,《文心雕龙·原道》篇强调“自然之道”,强调“天地”、“山川”之美,《物色》篇又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宛转和相互赠答的关系,这是否有当时的社会历史的原因?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就会知道,原来六朝时期的自然崇拜观念和实践,比古代又有所加强。六朝时期流行天地崇拜、日月星辰崇拜、气象崇拜、山水崇拜、动植物崇拜等,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刘勰的思想。再如要研究《文心雕龙》的《声律》《丽辞》《事类》《练字》等篇,就一定要充分考察六朝时期历史文化的背景,特别是那时候文学创作中讲究对偶、文饰、用典、文字修饰的情况,我们才会知道刘勰所讲的这些问题、提出的这些观点,是密切联系当时创作实践的。另一方面是向微观的、文本的语言方面拓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分析对文学而言至关重要,这已经成为共识。其实对于文论著作来说,说什么诚然重要,怎么说也是重要的,也许就在怎么说中隐含了著作家的重要观点。如“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明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物方,数必酌于新声”;“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等句子,都要仔细玩味、力求理解。上面所举我对《情采》篇“郁陶”一词的发现也是一例。
(2)审美评价。
文学研究就是以文学为对象的研究,文学的特质是审美,“文化诗学”之所以是“诗学”,就是它重视文学中的“诗情画意”。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是审美。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它经不起起码的“审美”的检验,那么它就不是文学,就不值得去研究。“审美”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或者说审美是人性的展开,其背后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谈论的人文精神,因此它关系到人的感性与理性发展的大问题,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研究文学作品要重视“审美”,研究“文论”也要重视“审美”。如果一部文论作品,完全不讲审美,不讲文学的审美特点,那么它的文论价值就很可疑。也正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对《文心雕龙·情采》篇提出的“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和“为情而造文”特别重视,认为“情者文之经”道出了一个“文学原理”。《文心雕龙》一书涉及的“情”字特别多,上文已举例,此不赘述。但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物以情观”这四个字,它表明的是人的情感的观照和评价。可以说,情感的观照和评价就是我们现今说的“审美”。这就是说,早在刘勰那里,就对“物以情观”给以“审美”的确切解释。这是很了不起的。
(3)对话精神。
古人是一个主体,今人也是一个主体。尽管古人已不在,但他们留下了作品,我们要通过各种办法激活古人,使他能够成为一个主体,与今人构成一种对话局面。这种对话并不是要给古人穿上现代的西装,而是要从中挖掘出具有普遍价值的观念来。对话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也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同时也是文论研究的本质。对话是什么精神?对话就是民主精神。文化诗学所要提倡的就是这种民主的对话精神。我尊重刘勰,尊重刘勰的研究者,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刘勰及其研究者,但我与刘勰及其研究者进行对话,从对话中发现新的文论世界。
如果我们能做到上面三点,那么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必然会具有如下两种品格。
(1)学科品格:超越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
从文学研究的学科角度看,过去有专门研究文本的文学语言的所谓“内部研究”,也有专门研究文学与社会关系、文学与政治关系、文学与经济关系等的所谓“外部研究”。这两种的研究的局限是明显的。因为文学是一种活动,是一种复杂的事物,其中有属于内部文化诗学的方法要在上述两种研究中实现新的综合,超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
(2)现实品格:以积极的文化精神回应现实。
文化诗学最终目标是要联系现实,回应现实,因而这种理论方法具有现实性品格。现实中存在许多消极的文化现象,有不少庸俗的、浅陋的、败坏人的精神的寡廉鲜耻的东西。有人可以不顾现实的问题,为学术而学术,但我关切现实的问题,不搞为学术而学术。我的研究是要从研究的对象中提炼出一种积极的文化精神,以此回应现实。尽管这种回应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终究与现实的积极的文化精神血脉相通。《文心雕龙》中的“自然之道”,“折衷”精神,“文质并重”精神,“因内符外”精神,“风清骨峻”精神,“参伍因革”精神,等等,都是积极的文化精神,难道这些精神不是可以烛照、驱散现实中的俗气和陋气吗?
此文由我的学生耿波催促而匆匆写完。我自己力求“实话实说”,但有些地方会让人觉得“自吹自擂”。其实,“人贵有自知之明”,是我终生推崇的一句话。我知道自己的分量,知道“自卑”,知道不足,知道空虚。在学术面前,我知道敬畏。我期待在有生之年,能稍稍增加这分量、克服这“自卑”、弥补这不足、填补这空虚。
(2005年9月7日, 9月26日又改。2011年9月又改。我讲《文心雕龙》研究一直到2007年,总共讲了12遍。)
[1]张少康等:《文心雕龙研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
[2]姚思廉:《梁书·列传第四十四》,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2页。
[3]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88页。
[4]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28页。
[5]章学诚:《文史通义》第二册,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75页。
[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7]鲁迅:《论诗题记》,见《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
[8]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