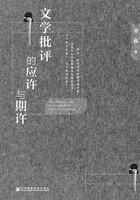
三 “力度”,知识性批评要稳、要准、要狠
“力度”主要是针对目前知识性批评在批评主体的思维模式固化、主体对作品的研读及评价能力限度来说的。知识性批评在分析评价或宏观或具体的文学问题时要起到“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的作用,批评者介绍文学史、文学思潮、创作流派、艺术手法等知识,为作家作品归类、定位,总结、鉴定作家创作实绩;使读者了解作品的文学史背景知识,以便更好地阅读欣赏。相较理论批评而言,知识性批评更接地气一些,它直面文学舆情,既能为作家提供文学性的指引,又能让读者更好地走入作品、提升读者的审美品位,给作家、作品、读者提供沟通的平台。这一批评方式在目前的不足是,我们能看到批评家说某个作品好,某个作品不好,却总感觉文学好的并不一定如评论的那么好,坏的也并不一定如评论的那么坏,批评并没有真的“做实”,没有做到“稳、准、狠”地击中要害。知识性批评要想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做到:评论家对他所评论的对象要有不带偏见的态度;评论家对评论对象所在场域要有全面而精深的知识储备;评论家对作品的品读要有个性化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
知识性批评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先验的假设框定了评论家的思维,文学性的灵感难以被激活。“尊重现实生活,不信先验的假设,无论那些假设如何为想象所喜欢,——这就是现在科学中的主导倾向的性质。”[14]但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面对那些为人熟知的作家的作品时,更易束缚我们的往往是已知的文学史知识、文艺理论知识,而非我们对作家作品的未知部分的直接、大胆的探究。在已知世界与有待理解未知事物之间,横着一道由隐形的理解权力划定的界限。福柯发现了这道边缘界限,并试图逃离或者说超越被这个界限所固定的权力陷阱。他在《无名者的生活》中先是指认“总是同样无能跨越这条线,无能通过到另一边……总是同样地选择,在权力的一边,在它所说或促使说的一边”,继而针对这条无法跨越的“线”,他解答说“生命中强度最强之点,那些凝聚生命能量之处,就是在他与权力撞击、搏斗,并企图运用其力量或企图自权力陷阱逃离之处。”[15]可我们今天的批评往往容易沉迷于、“自闭于权力”的沾沾自喜中,既定的成果沉淀在那里,因袭总比突破来得稳妥,我们于是没有勇气去撞击、搏斗乃至抵达未知的彼岸。比如对萧红的研究,基于文学史的“定论”,我们总会先验地推断她写作的关键词是苦难、悲悯、战乱、死亡、寂寞,等等,我们甚至不愿意正视她后来的转变,她经历人生哀乐后一切了然于心的欢愉。我们常注意到她作品中的女人之痛(“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女人之轻(“农家无论是一棵菜,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女人之愚(“麻面婆错把白菜抱成倭瓜,夏天去稻草堆里找羊”),却忽略了她笔下的女人之美与善。“有一双亮油油的黑辫子”的金枝,“打渔村最美丽的女人”月英,“长得窈窕”的翠姨等。女人在萧红的笔下虽然常是无能为力地听从命定的摆布,但她仍是自怜自爱地欣赏着她们的美丽,并未因其困窘、愚钝就自轻自贱。评论家在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要利用自身的“前理解”“审美预设”解读研究对象,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只按照已存在的视角、观点和方法来研读作家作品,知识性的读解不过是再一次被整合过的观点复制,失去了批评的意义。柏格森说,无论艺术家如何努力,在其实践终点上都会与一种“无”相遇;他提供给世界的虽然是一件可以“观”的作品,“但是,那个具体的结果中包含的、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全部内容的东西,却依然是不可预见的。而占据着时间的正是这种‘无’。”[16]如果评论不试图跨越从已知到未知的理解权力界限,那么批评的穿透性该从何而来?
浩繁的文学场域影响了批评者的判断,批评的知识储备不够精准和丰盈。知识储备既包括批评者对自己洞察能力、辨识能力的储备,又包括他们对文学资源的储备,建立在精准独到、客观全面知识储备基础上的评论、判断才能有“力度”。就如高建平一针见血指出的:“我们今天更加需要另一种批评,像医生治病一样的诊断性批评。这主要指不带任何外在的意图,只是面对作品本身实话实说、发现问题、揭示病症的批评。这种批评要专业化,需要文学批评家多方面的能力,既要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有对文学理论的深入把握,也要有文史哲等相邻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知识和修养,有对当下文学发展状况的了解,更重要的是有对当代文学作品的深入感受力。”[17]那么,评论家如何能够底气十足地相信自己的眼光,又如何能对特定问题全面精深地把握?评论家的天赋、才情、底蕴等都是必要的,但在其中,勤奋和沉潜却是重中之重。
知识性批评文章的作者多为作协系统或高校教师,阅读者不仅是单纯的评论家同行(专业读者),还有被评论的作家们,他们也较为在意自己在阶段性总结上(比如“70年代出生作家”“文学期刊扫描”“年度文情报告”)有没有“上榜”。 这样专业的关注度对研究者的勤奋程度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否则批评家的结论便难有说服力。就关注文学实绩、追随文学动态、解读论争热点而言,从事批评工作是很辛苦的。它要求论者对作家作品、文坛纪事都要有既翔实又敏锐的把握,然后积极应对并写出一篇短评、一篇论文或年度报告,为已然或未然的文学史备份。然而,面对文坛多元驳杂的作品,恐怕再努力的人也只能涉猎冰山一角。难怪经常有人质疑,从事批评的学者除了理论著作之外还读不读晚近的文学作品?哪怕是在一年3000部长篇小说中选取一部,或者字数不多的散文、诗歌?知识性批评比较讨巧的做法是在细分化的基础上守住评论家各自的那块版图,专注一个论题,在可以把握的范围内回旋,并以小见大。“文学批评只有站在文学创作之上,评判价值,洞见趋势,指出存在的问题,才是杰出的、有效的和富有启示性的,才是这个年代最为需要的批评。”[18]
难就难在,即便勤奋和经验同在,还要尊重文学批评自身的特性。阅读是一段不能急于求成的旅程,欣赏一部小说或一首诗,是要在一定的心境和一定的情境下才能完成的。基于阅读之上的批评不也是一样吗?它不是即时性的一次性的投入与产出。对同一部作品的评价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心智的变换而变化的。比如少女看《红楼梦》,或许只对宝钗黛的三角恋爱关系感兴趣;长大成熟后,读者或许会对薛宝钗的为人之道、小说中的饮食服饰较为关注;及至中老年,读者或许会对书中的人情世故、哲学意味生出感悟。可见文学批评是无法讲究“时效”的,它是太需要时间沉潜的一门艺术。更何况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有当下的,有历时的,可能再过几年便不会有人记得今年的砥砺之作。翻阅今年的学术期刊,还有多少文章是专门论述毕飞宇的《推拿》或是张炜的《你在高原》呢?现今的知识性批评会因为研讨会、因为急于在刊物赴印之前交稿、因为某个纪念年份而“赶任务”……功利目的促使评论家过早、过快地为文学下结论,有几成把握便去给作家做个定性的论断,再从作品中寻找定量的信息来佐证这个论断。“一个批评家应当从中衡的人性追求高深,却不应当凭空架高,把一个不相干的同类硬扯上去。普通却是,最坏而且相反的例子,把一个作者从较高的地方揪下来,揪到批评者自己的淤泥坑里。”[19]这种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批评很难释放来自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又怎能使作者和读者信服?评论家有底气才敢说话,敢在评论中写出对优秀创作和技艺的褒扬,写出对粗制滥造的挞伐,对读者接受水准降低的痛心疾首,这样的评论才会有“力度”。
批评家个性化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是文学批评力度最直接的外在体现形态。文学批评是一种写作,是一种“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的写作,对文学批评文本形式、结构、语言、风格的要求丝毫不逊于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是文学批评,但比文艺作品还要精彩;刘勰的《文心雕龙》、李渔的《闲情偶寄》都是文学批评,留给我们的财富除了宏深学理,更是其诗性的语言和高深的意境。批评主体的情绪、底蕴和联想都渗透在了“批评”之中,以直言不讳、机智敏锐,又不乏独特风格特色的写作来彰显“力度”,才能做到入文学之内又出文学之外。知识批评娓娓道来的如王国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20]严谨周密的如马丁·海德格尔,“我们从事物中复归自我——从来就不必否认我们寄寓于事物之中。确实,那种在压抑状态下发生的与事物失掉密切关系的事完全不可能出现,即便这种状态不再作为一种人生状态……”[21]激情澎湃的如阿多诺,“(法西斯)是绝对的感性……在第三帝国,新闻和谣传的抽象恐怖作为唯一的刺激大行其道,足以在大众虚弱的感觉中枢煽起一种短暂的激情”[22]。如上,批评家的精神个性、思维方式、观念主张都融化在批评著作的话语秩序之中,足见得批评是“以文字装饰思想的一种特殊方式”。
评论家要有开放的视野、开阔的胸襟,要兼顾理论界的文艺导向、作品本身的审美意识、大众的欣赏期待等多方面因素,如何协调而保持本色就成了问题。比如有论者从文学的生产、评价与传播几方面批评当下文学没有感召力和内驱力,这当然是偏颇的。事实上,作家从来就没远离过读者,只不过他们的作品在以另一种方式为读者接受。纸质时代读小说的人依然在读小说,图像时代不读小说的人反而因影视的传播读作品了,这难道不好吗?周梅森的《人间正道》、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张平的《抉择》等的发行和热播不正展示了文学的恒久魅力吗?提倡文学与生俱来的人文关怀和审美关怀并非是要将其引入商业的对立面,何况文学本身就有其实验和探讨的性质,走向图像不失为发展的策略之一。至于弊端,则可视为不成熟的表现,所以更需要理论的引导和扶持。再比如,批评家对作家不深入生活的批评,实则反证了批评家对作家的不深入。“打工文学”不就是来自底层凝血凝泪的真实声音吗?林白的《妇女闲聊录》不就是她沿着铁路线一句一句地采访整理出来的吗?《昆仑殇》不就是毕淑敏在阿里11年军旅生涯的追溯与升华吗?所以说,文学不是科学,无法以整齐划一的标准去衡量。批评家要博大精深,更要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当下知识性批评者的言说个性未免模糊,我们在越来越发达的研究方法、写作语词中反而读不出批评家精神愉悦和诗意“力度”,读不出审美个体的差异性感动与风格化表达。多数批评者正面阐释作品的能力下降,常以暧昧的批评态度、中性的批评用语来评价作品,做不到一语中的,无法树立自己的批评风格,也无法让作品真正站立起来。如果文学批评为各种非文学的利益所支配,过多地圈囿于话语权力、物质是非、人脉圈子,则无法完成对自身的深度反省和锐意创新。就如契诃夫所说,“只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好的批评家,许多有益于文明的东西和许多优美的艺术就被埋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