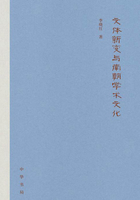
绪论
第一节 南朝“文体新变”的历史考察
“文体新变”是南朝文坛的显著标志。从当时史书的记载中可见一斑。《南齐书·文学传·陆厥传》称陆厥(472—499)[1]“五言诗体甚新变”,并记载:“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2]《梁书·文学传上·庾肩吾传》论及王融(467—493)、谢朓(464—499)、沈约(441—513)等所制“永明体”,评曰“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3];《徐摛传》称徐摛(477—551)“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4]。《陈书·姚察传》载姚察(533—606)“每有制述,多用新奇”等[5]。这样集中而明确地标揭作家文体新变现象的历史书写,在此前的正史中从未见到,在此后的正史中也很少见,透露出当时人们对于文体新变的敏感与关注[6]。
南朝文士对于文体新变有自觉的追求。如“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的南齐张融(444—497),在其《门律自序》中对其子说:“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临卒,又戒其子曰:“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岂吾天挺,盖不嵉家声。”[7]说明其文章并非颠倒错乱物理人情的怪异之体,而是尽己所能随物赋形[8];子嗣若别有新得,作为父亲不会拘限之,且视文体新变为“不嵉家声”之举,可见其家教中对文体新变之认识与追求。不仅如此,作为史家的萧子显(487—535)[9]在其《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亦提出:“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明确推崇文体新变[10]。可以说,南朝文坛从私人领域的家教,到公共领域的史家言论,整体上对文体新变持有认同态度[11]。这与此前重视“模仿”、“拟作”的汉晋文学传统大异[12]。由是更促成新文体、新题材、新创作思维的涌现与发展。
现代学界在解释南朝文体新变现象时,往往从南朝统治者由武功起家,再由武转文,由是所形成的新兴文士阶层,整体上较为尚俗好奇的文化取向着眼进行解释。如关于吴声西曲的兴起:王运熙1955年刊行的《吴声西曲的产生时代》中提出,这首先是整个上层社会的风气,因“老庄思想流行,士大夫往往蔑弃礼法,崇尚放诞”,儒教礼法“对上层阶级的约束力量非常薄弱,为‘淫哇’的‘委巷风谣’敞开了大门,使它们能够大量地涌入乐府”,并强调“必须指出南朝许多统治者的出身情况……寒微的出身,使南朝的统治者们一方面容易喜爱产生于民间的歌谣,一方面又容易不受礼法的束缚把它们大胆地引入乐府”[13]。唐长孺也认为这是伴随南朝寒人兴起的文化现象,其《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说:“南朝流行的民歌所谓吴歌与西曲一般是反映城市生活而以爱情为主题的歌谣。歌谣中的男子通常是来往于长江中下游诸城市的商人、估客。南渡以后,就在北来人士中传播,而且特别在宫廷中盛行。自宋至陈很多皇帝或皇室曾模拟此种民歌而写出一些作品……宫廷中流行吴歌、西曲的原因之一正是和模仿市里工商一样由于宫廷中聚集了大批‘市里小人’,特别是商人。我们看吴歌、西曲在皇室中流行起于宋代,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寒人掌机要的开始。我想这不能说是偶合。”[14]后来曹道衡《南朝政局与“吴声歌”、“西曲歌”的兴盛》及王运熙《刘宋王室与吴声西曲的发展》等文,仍主张是“刘裕出身寒贱,由一介武夫而逐步篡登王位,其家族人员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教养,在艺术方面自更容易喜爱通俗的民间乐曲”[15],“南朝的上层官员、文人和士大夫中既然包括着‘北府兵’出身的人物和南方士人,他们的艺术趣味自然和原来的北方士族不完全一样”[16]。至于五言四句体、七言体等诗体之兴起的研究,学界也大致持新兴士族趣味说。这种解释视角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尚存在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首先,从文体新变的创作者家世文化来看。南朝时代掀起文体新变的文士,有不少出身于东晋以来的旧高门士族。王运熙曾指出,吴声西曲的“作者往往是一些文人学士、达官显宦”,这些歌辞本旨多非反映城市生活而是抒写爱情。如王珉的《团扇歌》、王缮的《长史变歌》、谢尚的《大道曲》等,本身即源自士族生活和仕宦情绪[17];即使是现存歌辞内容充满民间情调的《阿子歌》、《欢闻歌》、《丁督护歌》等,题意本旨也实为帝王将相的政治悲歌。[18]唐长孺也注意到,《世说新语·言语篇》载:“桓玄问羊孚,何以共重吴声?羊曰:‘以其妖而浮。’”《太平御览》卷四九一引《晋中兴书》载:“王恭尝宴于司马道子室,尚书谢石为吴歌。”唐先生指出司马道子是作吴语和使宫人为酒肆的人,谢石之为吴歌盖是投其所好[19]。无论王珉、王廞还是司马道子、羊孚,都是北来士族中的高门,因此吴声西曲的兴起,未可简单视为南朝寒人的文化风尚。宇文所安、田晓菲指出:“贵族阶层对吴声歌的迷恋始于四世纪,而且恐怕毫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迷恋源于南渡的北方贵族移民。……大量的南朝乐府有可能是在公元六世纪才被初次编集在一起。虽然常被现代学者称为‘民歌’,这些南朝乐府实际上是在宫廷中演奏并由宫廷乐师传播下来的;其中很多都是由宫廷乐师、贵族成员甚至是皇帝本人创作的。这并不是否认这些乐府植根于当代流行文化,但是它们的传播却经过了南方精英阶层的中介。正因为如此,它们更主要地代表了贵族阶层的想象,而并非‘人民百姓’的创作。有几首乐府被系于知名的东晋人物孙绰王献之和谢尚名下,这些人物都是北方贵族移民。据说谢尚曾坐在市集佛寺门楼的一张胡床上弹奏琵琶歌唱《大道曲》,‘市人不知其三公也’,正如这首曲子本身就歌咏了隐姓埋名一样,谢尚的所为可以被视为一种‘阶级的易装’。这并不是由于南朝社会经历了所谓文化上的‘庸俗化’,相反,通过将自己想象成南方平民这一社会和文化上的他者,在这片土地上作为难民、定居者和殖民者生活的北方贵族移民得以维持和确认他们自己的身份。”[20]说明吴声西曲进入精英文化视野主要是北方贵族移民“需要想像出一种特定的南方文化来和自己的文化身份相区别的结果”,从“东晋的精英集团为保持自身的优越性而刻意制造身份区别的努力”角度观察文体新变现象,非常有启发性。进入南朝之后,旧高门子弟对于新声新体的创造与审美追求,更加引人瞩目[21]。梁钟嵘(约468—518)《诗品下·序》曰:“齐有王元长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颜宪子论文,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尝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擗积细微,专相凌架。”[22]指出永明诗体声律新变的引领者为王融、谢朓、沈约,三位“咸贵公子孙”。此中王融出身琅邪王氏,谢朓出身陈郡谢氏,都可谓是成长于旧高门士族文化中的文士。而且他们与吴兴沈氏这样的南方本土精英共同推出永明体新诗,已然超越了南北文化身份的区隔。
其次,从文体新变的具体现象看。南朝文士笔下的文体新变,并非皆从南方通俗文体入手,也并非皆从流行的通俗文化中取资。如《宋书·乐志》所载谢庄(421—466)造《宋明堂歌辞》,“以数立言”造作祭祀五帝歌辞,尤其“依金数九”立言造作九言体《歌白帝》辞,乃前所未见。这一乐歌体式新变,是在传统王朝体制枢纽之明堂礼典上发起,贯通运用了郑玄注《周礼》、谶纬五行、礼典歌诗礼仪等多种旧学知识[23]。由谢庄所创制的这套祀五帝歌新文体,经其族人谢超宗、谢朓传承,应用于南齐的明堂、雩祭礼典上。后传入北朝,由祖珽沿用。庾信入北周后,利用《月令》五行数改革陈郡谢氏五帝歌所依五行数,将“以数立言”造作乐歌的方式运用到元会大典歌辞《周五声调曲二十四首》的创制上。其中依《月令》“角属木”、“木数八”所创制《角调曲》,是现存最早的八言体乐府诗[24]。可以说,南朝文士是在运用传统经学知识的基础上,创制出前所未见的八言、九言乐府诗的,可见文体新变与传统学术文化的关系之密切。
因此对南朝时代的文体新变现象,还值得从士族的家世文化、知识结构乃至礼乐追求等视角加以新考察。从另一角度看,南朝文体新变现象也反映出各种学术文化在此期的独特接受状况,并提供了认识此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线索。譬如南朝时期新兴的宫体诗文,后人常常对其描写内容之浅薄甚至恶俗大加诟病。如徐摛所写“一人病痈”:“朱血夜流,黄脓昼写,斜看紫肺,正视红肝。”[25]描摹“一种从外观到气味都很丑恶的疾病”[26]。但这令我们联想到鸠摩罗什《大智度论》“释初品中·九相义”。佛经论死尸“九相”,其中“胀相,坏相,血涂相,脓烂相,青相”,与徐摛所写“一人病痈”“黄脓昼泻”意象相似。它们都异于健康人的形相,同样地令人“心生厌畏”。佛经通过“行者见已念此死尸本有好色,好香涂身衣以上服饰以华彩。今但臭坏脓烂涂染,此是其实分,先所饰彩皆是假借”[27],以丑恶的死尸九相,说明世人欲念中的身体好色皆是假借,产生强烈对比反差。由此反观徐摛此诗,则不仅其对“痈”脓烂相的关注,可能受到佛经的影响;其以时人最欣赏的色彩绚丽、对仗工整、音韵铿锵的骈体文写令人厌畏的“痈”,这种外在形式之美与内容之丑的强烈对比思维,也可能是源自佛经[28]。从学术文化的角度看,此诗不仅与佛经有着某种关联,其对痈发病时肺、肝颜色变化的想象,也反映出对《黄帝内经》等传统医学观念的了解。可以说徐摛乃至其引领下的宫体诗文创作的这种文体新变,蕴含着多元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知识积淀,是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线索,值得展开系统细致的研究。
本书试图在多学科视野中考察南朝时代的文体新变现象与其时学术文化的内在互动:一方面力求更全面、准确、深刻地揭示南朝文体新变的表现形式与深层内涵;一方面重新认识文学新变现象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