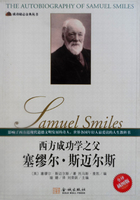
第6章 革命——劳德暴乱——霍乱
1831年——革命
这一时期,“革命”盛行。在1830年7月的三天里,法国大革命惊醒了欧洲,激起了民众普遍的革命呼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而在南爱尔兰地区,人们陷入了困境。在肯特郡和南部村庄,人们纵火焚烧干草堆;在工业区,人们捣毁机器;在格拉斯哥,激进派开始了与贵族的较量,工人阶级普遍忧心忡忡。人们认为,议会改革是所有改革的重中之重。在位的水手国王对新观念表示赞成。威灵顿公爵退位,格里伯爵上任。议会于1831年2月3日召开会议;3月1日,约翰·罗素男爵提出了议会改革措施。举国上下都为这一议案振奋不已。各地区纷纷派去请愿者;政治联盟纷纷建立;国内的“革命时代”似乎一触即发。随后,议案通过了多数党的二读。
当时,爱丁堡张灯结彩。从卡尔顿山或北桥鸟瞰它的时候,这座城市尤其显得灯火通明。一边是王子大街的狭长通道,一边是古城明灯熠熠的房屋。但是,那伙总是人多势众的暴徒,蛮横了起来。每个人都得对他们唯唯诺诺,否则就要自食其果。这回,他们跑去捣毁那些没有点灯的人家的窗户了。王子大街沿街堆了许多修补碎石路的石头,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方便。他们不顾警察的喝斥,捡起石头,砸碎了许多窗户。
我想,大概是在乔治大街上吧,这群暴徒涌进了一座黑灯瞎火的大房子,摔起了东西。这时,三个漂亮女人突然出现在阳台上,每人手里都捧着一只点燃的蜡烛,于是,她们拯救了这座房子。暴徒崇尚美人和勇气,大呼小叫之后,继续横冲直撞。“光荣的多数党”就这样四处闹事。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讽刺。
大臣们最终转向了少数派。国王解散了议会,议会成员只好求助于立宪会议,孤注一掷。国家卷入了一场骚乱之中。6月14日,新返还文书出台,要求进行新的议会选举的呼声在城镇日渐高涨,人们的口号是,“法案、法案、完整的法案”。1831年的4月底,学校的课程结束了,我回到了哈丁顿,发现这里也同样充斥着对改革法案的激情。
1831年——哈丁顿区
哈丁顿是举行议会成员选举的五大教区之一。五个教区轮流推选议员。这一次,轮到劳德教区了,这是位于拉莫缪尔山区侧翼的一个小镇。哈丁顿和杰德堡是两个最大的教区,它们都宣称拥护辉格党,而丹巴和北贝里克拥护托利党,人们认为,只有劳德还举棋不定。是奥德斯顿的改革者罗伯特·斯图尔特重返议会,还是兰德达利主教提名的改革反对者A·J·达尔林普尔爵士重返议会,一切都取决于劳德的决定。我不知道结果怎样,只知道由哈丁顿的改革者组成的一支强大的特遣部队企图向劳德进军,想方设法地确保他们支持的候选人重返议会。于是,我决定穿越拉莫缪尔山区,见证这次进军。
那是五月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怀着十分愉悦的心情向拉莫罗前进。一年前,我曾到过山顶的界标处,欣赏了壮丽的风景。我经由吉福德,穿过叶斯特森林,越过朗·叶斯特农场,然后沿着石兰花丛上行;石兰花丛间有许多古代部落遗留下来的营地,在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入侵前,这些部落早就占据了这个国家,而苏格兰人和皮克特人只不过是入侵者而已。当我向上攀登的时候,空气清冽凉爽,沁人心脾;快到山顶的时候,我俯瞰整个拉莫缪尔山坡,视野所及之处,群山林立,静谧而肃穆。除了一只苏格兰雷鸟飞回巢的呼呼声和受惊的绵羊偶尔发出的叫声,万籁俱寂。
从南坡下山,我踏上了前往哈热尔迪安的路途。又经过了几个前面提到过的古代营地,绕过焚烧之后遗留下来的空地,我来到了里德河边,接着,我踏上了去往爱丁堡的大路。从拉莫罗顶峰下来,步行约10英里后,我到达了劳德镇——第二天的选举现场。我叫上一个朋友跟我同行,不久就来到了大街上,跟从邻镇过来的人碰面。我见到了两个选举干事——斯托比先生和杨格尔先生——他们请我加入他们的帮派,总部在镇上第二大旅馆楼上的一间房里,而第一大旅馆——“劳德戴尔军队”旅馆已被另一派的人占了。
这个小房间里热闹非凡,弥漫着威士忌酒的味儿。改革运动者首领都在这儿;候选人罗伯特·斯图尔特也在那儿。气氛很随意,谈话间歇期间,大家还唱起了歌。但我没等聚会结束就离开了。
1831年——议会选举
第二天一早,成群的外地人朝镇子里涌来,大部分都是从哈丁顿来的。人群中有许多改革运动者,由“将军”班吉打头,随队还有一名演说者——“雄辩家”麦克劳席兰——一个来自新兴门[23]的面包师,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选举快要开始了,一群人在“劳德戴尔军队”旅馆对面集结在一起。梅特兰勋爵、安东尼·梅特兰爵士和另一些人从旅馆里走出来,一行人穿过街道,在猎场看守人和农场主们的护卫下,来到了议会大厅。梅特兰获准进入,可猎场看守人却跟别人打了起来。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哈丁顿木匠用手杖的粗头一杖子砸在猎场看守人的秃头上,他就跟中了枪子儿似的应声倒地。这是一次十分残暴的攻击事件。安东尼·梅特兰爵士来到议会大厅的露台上,朝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挥舞着拳头,发誓要报仇。
不过,最重大的一件事,发生在离镇区较远的地方。市政官辛普森,是一位议员,他由于身体不适,没打算参加投票,可劳德戴尔派派了一辆马车去接他,而另一辆配了两匹快马的车也准备把他接走。在马路的拐角处,有人把载着这位市政官的马车逼停,把市政官赶下了车,塞进另一辆马车里。那辆载过他的马车被一个力大无穷的哈丁顿屠夫推倒在沟里。选举开始了,宣布代表多数党的罗伯特·斯图尔特当选——又是“光荣的多数党!”
人们再次集结起来,向哈丁顿出发,这次胜利令他们欢欣鼓舞。直到第二天,我才向哈丁顿返回,再次翻越了群山;我得知,队伍回到哈丁顿以后,在几个人的带领下,人们用头顶着燃烧的焦油桶来庆祝胜利;在漆黑的夜里,那种场面十分惊心动魄,他们可真是高兴得发了狂啊。
几天后,新议员驻进了镇子。他在距镇上一英里处的劳伦斯豪斯受到了男男女女和孩子们的热情迎接。当然,选举结果并没有站稳脚跟,它遭到了请愿者的抗议,罗伯特·斯图尔特被撤职,而A·J·达尔林普尔在旧议会解散期间成为了该区的候选议员。当局企图调查出劳德暴乱的策划者。劫走投票者的马车夫被逮捕,在监狱里关了12个月。而主凶——哈丁顿那位大力士屠夫,却再也找不到了。那个击倒猎场看守人的年轻木匠获准继续在镇上生活,但后来再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一位重要议员得到了奖赏,被封为西印度群岛的地方官员。这就是“劳德暴乱”的结局。
1832年——父亲去世
还是回到我的个人历史吧,第二年的11月,我回到了爱丁堡。这是我的第三个学期。我进修了两位利萨斯先生的解剖学和外科实践课程,以及麦金托什博士的药物学实践课程。我中午步行去医院,利斯顿是这里的主治医师,一切重要手术都由他操刀。
此时,亚细亚霍乱正沿着西北方向横扫欧洲,向英格兰袭来。它已经抵达了汉堡,就要光顾英国了。第一批感染者大概是在盖茨黑德[24],第二批就轮到了哈丁顿。1832年1月清晨,我在爱丁堡的寓所里被一阵很响亮的敲门声惊醒了。我当时正在做噩梦。我马上明白过来,一定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害怕得不得了。我推开窗户,问明了这个人的来意。他叫我必须马上赶回哈丁顿,因为我父亲染上了霍乱。轻便马车就在门前停着,等着载我回去。我赶紧收拾停当,不到15分钟就踏上了回家的路途。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早晨,当我们的马车经过拜尔斯雷山坡的时候,太阳正从福斯湾升起。尽管仆人弗塞斯把马车驾得又快又稳,可我们到家时已经太晚了。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平静地躺着,长眠在那里。我发现,这与我见祖父的最后一面惊人的相似。
当时在镇上,霍乱是一种致命疾病。许多人死在了街口上,就在我父亲的住处附近。后来,人们发现了灾祸的源头——卫生饮用水的短缺和排污系统的严重缺乏。这一问题在多年以后,终于得到了解决。在古老的哈丁顿大教堂唱诗班的歌声中,父亲被安葬在约翰·威尔士大夫的墓地附近。
家人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中。家里有11个孩子需要供养——最小的还是个婴儿,只有三个孩子年龄大点儿。为了安慰母亲,我在家里呆了些日子。一开始,我不知道是否要继续我的医学学业,它的花费很可能会非常高昂——看看我们所面临的情况吧。接着,另一种糟糕的事又发生了:我父亲曾跟另外两个人一起当了他大哥约翰的担保人。约翰是爱丁堡附近的科林顿的一个造纸商,由于交不起税,造纸厂被停产,必须交800英镑的保证金。我父亲去世以后,首先要解决的事,就是揍齐这笔钱的三分之一,交给爱丁堡的律师。我们借了一部分钱,由我到爱丁堡去交钱。经证明,这桩案子属于全损,在这种时候出这种事,令大家十分苦恼。
在家呆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表示自愿放弃自己的学业。可我母亲不听。“不,不能这么做,”她说,“你必须回爱丁堡去,按照你父亲的意愿去做,上帝会保佑你的。”她笃信天意,相信只要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上帝就会自始至终地保佑她。她有着卓越的胆识,她的品格似乎是应运而生的,困难只会引出其本性里的精髓。我不能不受这位好母亲的影响。我受到了她的鼓舞,服从了她。
1832年——我获得了文凭
于是,我回到了爱丁堡,在学校读完了第三个冬季学期的课程;在夏季学期,我进修了西密先生主讲的临床医学、麦金托什博士主讲的产科学和亚历山大·利萨斯先生主讲的解剖学实践,然后,我就迎来了考试。当时,找人为自己辅导的情况很普遍。可我放弃了这种代价昂贵的应考准备,只是每天跟一个年纪相仿的学生亨利·史密斯一起复习——他后来成了一位有名的化学品制造商,在他的帮助下,我也得到了所有必要而详尽的辅导。
我们一起参加了考试。当我们在新建的外科医生学院前厅等待考试时,第一位应考者出来了,接着另一位也出来了——他们没有考及格!有个学生比我年长许多。我想,要是他都过不了,那我也没什么着落了。亨利·史密斯接着被叫了进去。经过很长时间的“刁难”(我是这么想的)——长得我都怕他出不来了——他喜气洋洋地出现了。“我过了,”他说。“难吗?”“不难,一点儿都不难。我知道你的能力。你也会觉得简单的!”因此,下一个叫到我的时候,我也就放心地进去了。
尽管那时的考试是以口试形式来进行的,没有任何笔试项目,但考官很快就能摸清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考官先一个接一个地对我进行考查,在特殊题目的考查结束后,就能迅速得出结论。考官包括胡易博士——一位不好对付的考官、西姆森博士、贝格比博士、麦克拉甘博士等等。首先,他们会给出一篇格雷戈里的拉丁文版《概论》或者《塞尔萨斯》里的一段文字让学生解释。然后考的是药物学,要求学生说出配制锑粉和甘汞的方法。接着考的是解剖学,要求学生描述头部的动脉、神经和肌肉。我对它们了如指掌,因为我的解剖学基础很牢固。最后考的是外科学,要求学生叙述脱肠还原法和腿部截肢手术的操作程序,以及手术和给药的操作细节。用这些让应考者始料不及的题目,精准地探知他们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样,考官就能对没有考查到的其它科目的学习情况得出结论。经过1小时左右的考查,考官们对学生的能力和知识的掌握情况了解了很多。我轻轻松松地通过了考试,高高兴兴地拿到了文凭,这一天是1832年11月6日,刚好是订下学徒契约的第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