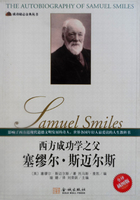
第5章 医学学生
1826年——选择未来的道路
我14岁了,问题来了,将来我该做什么呢?我们家是个大家庭,而且家庭人口还在增长,每个成员都必须做点事儿,而且最终总要为谋生而工作。
阿道弗斯·特罗洛普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有人问一名男孩长大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男孩答道,“我想当伟人,或者自由股票经纪人!”我不像他那么野心勃勃,可当母亲问我“萨姆,你想当什么?”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我想当漆匠”——我指的是画家。我爱好绘画和色彩,多年以后,我还为自己的书绘制了插图呢。
我也许是受了堂兄叶娄利斯的鼓舞,因为他为我父母画过肖像,而且我十分欣赏他以邮车为主题的那些画,这些都是他三下五除二的成果。可母亲还以为我想当油漆匠呢。“哦,不!”她说,“那可是一种脏活儿。”我没有回答,我们俩都暂时没再提这件事儿。
后来,有一天她又问我,“难道你不愿意当牧师吗?”“唔,不愿意!”我坚决地说,“我可不想当牧师。”“为什么?”当时我也解释不清楚,可现在能了。那是因为我们小孩子都被传福音、布道给淹没了。星期天,也就是“休息日”,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星期里最累、最不愉快的一天。我们的牧师是个好斗的人,宣扬的是最狭隘的加尔文主义,他的布道,与其说是宣扬仁爱,倒不如说是散布恐慌。
我们不得不在所谓的“休息日”里努力工作。早晨,做完祈祷,我们得学习“教义问答”和“圣经章节释义”。接着,我们要去教会,唱了赞美歌、做了祈祷以后,我们得听一个多钟头的布道,下午一点才散会。吃点东西以后,两点钟我们又要去教会,听下一场布道,四点散会。然后,我们还要背诵教义问答和释义。晚上6点,还有第三场布道要听;我们8点回家,背诵教义问答和释义。每个星期天,我们都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除了步行去教会,连散步也是禁止的。除了圣经、教义问答手册、教会期刊或者某些福音书,什么书都不能看。
这些都是为我们好,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是,在我的少年时代里,我从未对星期天有过任何美好的回忆。我们的牧师是一个优秀而勤勉的人。毫无疑问,他把自己的所有学问都传授给了我们;可他也是个乏味而无情的人;尽管他的教条是用来想吓唬我们,促使我们从善的,当它们却可能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因此,我不想当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1826年——医学学徒
母亲向我提的第二个问题是:“你不想当医生吗?”这个问题起初着实令我吃了一惊,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人们对医生持有许多偏见。家里的仆人常常吓唬我们说,“穿黑衣的医生”要拿橡皮膏封我们嘴,把我们拐到没人知道的地方去,害得我们心惊肉跳的。后来,为防止“医生”盗墓,把死尸送到爱丁堡的解剖室,人们就开始定期守卫教区墓地。我记得第一次轮到父亲守墓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了。那儿大约有三、四个人,其中一个被选为工头。人们为他们配备了步枪和刺刀,要给掘尸人一点儿颜色看看。几年后,伯克和赫尔为了给爱丁堡的诺克斯医生的解剖课提供“活体”而杀人,这种可怕的事也就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然而,医生这个职业也是不可或缺的,这有多种原因。有一次,我跌倒在地板上,撕裂了腹股沟,伤口离股动脉很近。家人请来了大夫,大夫给我缝了两针,我的伤很快就好了。这位大夫名叫罗伯特·利文斯,是个十分和蔼可亲的人,有着许多传奇故事。他的合伙人是罗伯特·罗里默大夫,是教区教堂牧师的大儿子,也很优秀。我的伤好以后,母亲问利文斯大夫能否收我当徒弟。他答道,“好吧,我的徒弟詹姆斯·杜尔沃德就要离开我去爱丁堡念书了,所以正好有个空缺,让你儿子来吧。”于是,事情也就这么定了。1826年11月6日,我成了利文斯大夫和罗里默大夫的徒弟,一直干了5年。
1826年——书籍、图书馆、讲座
在这个崭新的职业生涯里,我也并没多少事要做。我得学习药物的种类和性质,怎样开方子,怎样做片剂、合剂、汤剂、药膏、发泡药,怎样注射,怎样做药酒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了放血和包扎的技术。我得协助大夫为下层阶级的病人看病,还要继续自己的学业。镇上有许多图书馆,我可以免费使用它们。镇上有一座镇级图书馆——这里的书和一笔捐款是约翰·格雷于150年左右前移交给镇上的。这里的大部分图书都是关于神学的,不过,一些新添的书还是有阅读价值的。但我也没怎么用这家图书馆。这家图书馆的管理员正是英语学校的校长帕特里克·哈代;当我借走吉布[13]的《罗马帝国的兴衰史》时,他用一贯的蛮横口气,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说我怎能看得懂它。我讨厌他这么说,就去别的图书馆借书看了。
另一家有名的图书馆叫做“贝格比图书馆”,它是镇上的一个本地人留给公众使用的,他还留给图书管理人一小笔薪水。不过,我去得最多的图书馆是“东洛锡安流动图书馆”,它是由一位十分杰出的人物——已故的塞缪尔·布朗设立和管理的。卧病在床的他,在那段漫长的康复过程中,读了许多有益而有趣的书,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慰藉。这让他想到,或许能帮帮那些没有足够能力买书的人,让他们也得到同样的慰藉。他手里剩了一大笔“民兵保金结余”,而他又找不到任何索赔人。他拿出一部分钱,选购了两百册图书,一些是道德和宗教方面的书,另一些是旅游、农业、机械技术和大众科学方面的书。他把这些书分成四类,每类50册,然后分配给四个大村子,由义务图书管理员来管理。等这些书在村子里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就把它们换到另一个村子。这样一来,这些流动图书就总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还使大家养成了读书的习惯。
为了把图书馆维持下去,并使其规模得到扩展,布朗引进了订金制。年订户交纳5先令,就能使新购进的图书在郡上的三个主镇流动两年,然后再进入整体循环。这样,经过20年左右的不断努力,塞缪尔·布朗在全郡范围内设立了47家高品质的流动图书馆,几乎离每个居民家一英里半的地方就有一座图书馆。由于哈丁顿是图书馆运动的中心,在新书开始流通的时候,我就具备先睹为快的优势,就这样,我极大地增加了自己的知识储备量。
除了上述的图书馆,镇上还有订阅图书馆——当时我不是它的会员、两个流动图书馆——泰特图书馆和尼埃尔图书馆——在那儿可以借到当时市场上有的各类小说和另一些五花八门的书。因此,读者们就能埋头在知识、诗歌、文学、小说和神学的文库里,读个痛快。
塞缪尔·布朗主要想设立的另一个优良的公共机构是“哈丁顿技术学校”,爱丁堡一所类似的学校成立以后,这所技术学校也很快成立。我的导师和朋友罗伯特·罗里默大夫是第一批为这所学校的学生讲课的人之一,他的授课内容是“机械原理”和“化学原理”。听讲座的人很多,都是镇上最优秀的技术工人。我还记得其中的三个人,他们是为桑尼班克的斯高拉先生制作手推车、犁以及农具的木匠。其中有两人在一个夏天就省下了足够的钱,以支付爱丁堡大学冬季课程的学费。后来,他们一个成了布莱克本[14]长老教会的牧师,另一个成了赫尔[15]一所大型公立学校的校长,第三个还是干本行,但比别人晋升得更快。这个人名叫安德鲁·拉姆,是技术学校的一位热心学员。我对他印象很深,因为他常常参加青少年教会团的委员会会议,而我正好是该组织的非正式税收员。不久后,他离开了哈丁顿;多年以后,他还去伦敦大桥车站拜访了我。后来,他当上了半岛东方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再后来,他在南安普敦[16]定居,成为了当地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罗里默大夫在哈丁顿和丹巴[17]主讲几个科目的化学课和技术课,当时我还在当他的学徒;我荣幸地被他选为助手。他为人非常友善,还一丝不苟地教导我,给了我许多好建议。他教我为授课准备各种材料,当他因出诊不能上课的时候,我就替他上课。这不仅很有趣,还能让我学到知识,对我将来的学习大有帮助。利文斯大夫也是位好心人,允许我进出他的藏书室,那儿有许多古代英国小说家的著作,种类齐全——有菲尔丁[18]、理查森和斯莫利特[19]的著作,恐怕它们比科学书籍更吸引我吧。
我曾目睹了医生为撰写文书而烦恼的情景。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为了避免被厨房的嘈杂打扰,我们就在屋子最深处的卧室里进行写作。大夫穿着长长的睡袍,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把想到的内容口授给我,构成了一篇关于婴儿间歇性发热的论文。我对它了如指掌,因为我把这篇论文改写了三四遍。这篇论文有许多相当冗长的词,比如“intromittent(插入的)”、“恶化(exacerbations)”等等。几年后,这篇论文在《爱丁堡医学期刊》上出版。
与此同时,我继续着自己的学业。为此,我晚上要去进修教区学校校长约翰斯通先生的数学、法语和拉丁语课程。约翰斯通是位卓有建树、学识渊博的人;他是一位优秀的语言学家、数学家,他在课上讲的每句话都显示了他的见多识广。他是托马斯·卡莱尔[20]的密友,他们之间有密切的书信来往,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是后来才知道的。后面的事情是这样的,多年以后(1882年),当卡莱尔大名鼎鼎的时候,约翰斯通先生的女儿——当时她住在邓弗里斯郡的洛克比——寄给我大量卡莱尔寄给他父亲的信件,请我把它们编辑一下,然后付印出版。我了解到弗劳德[21]先生当时正忙着撰写《卡莱尔的一生》,于是建议她把信件寄给他,让它们成为那部传记的一部分。但是,据我估计,她并没有听取我的建议,因为当我把自传写到这里的时候,它们还没有出版。
在我当学徒的第三年底,为了接替克里大夫——利文斯大夫从前的导师,利文斯大夫移居去了利斯。他带上了我跟他一起去,于是我就开始进修爱丁堡大学的医学课程。我于1829年11月被爱丁堡大学录取,进修了邓肯博士主讲的药物学、霍普博士主讲的化学和里萨斯先生主讲的解剖学。课程从上午9点钟开始,我就从利斯步行前往爱丁堡——约三英里路程去上课。在阴冷的冬天,我常常摸黑吃完早饭,然后爬山去爱丁堡,及时在上课时间赶到。接下来是化学课和解剖课。中午,我返回利斯,给利文斯大夫帮忙。
那时,我活得十分快活。海港的繁忙,海边的风景,往返于校园间的徒步行走,百看不厌的爱丁堡的独特美景,还有我结交的朋友——这一切都让生活变得十分惬意。
第二年,我在爱丁堡寄宿,就住在校园附近。我继续着自己的学业——侧重于解剖学。我还选修了利斯顿先生的外科学和弗莱彻博士的临床医学。两人都很有才干,前者可谓是当时技术最娴熟的外科医生,另一位是业内造诣最深的讲师。他博览群书,研究课题涉及了整个欧洲的科学领域。达尔文的著作问世时,我还认为弗莱彻早在他之前就提出了非常类似的观点了呢,无论如何,这也说明了他的观点的先进性。几年以后,他去世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利文斯大夫出版了他的演讲稿,这些稿件充分地展现了他的天赋和才华。
1829年——约翰·布朗大夫
我的一个朋友约翰·布朗,也是弗莱彻博士班上的学生。他就是后来的著名作家,《雷布和他的朋友》一书的作者。他当时穿着一件夹克,拥有无穷的幽默感,尽管他非常害羞。要是有谁想了解他的性格,那可要花上一段时间。不过,等你了解了他,就一定会喜欢上他的。我了解他的堂兄塞缪尔甚于他本人。塞缪尔·布朗是我的同乡,我常常跟他讨论问题,也有不少书信来往。他是雪莱[22]心目中的理想品格的化身——“豹一样的灵魂,敏捷而优美。”即使是在小时候,他也很有想法——虽然不是所有的想法都很切合实际。他好冲动,是个急性子,做决定的时候风风火火的——后面我还会讲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