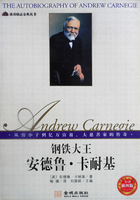
第9章 安德森上校·图书
信使们快乐而努力地工作着。公司要求他们隔天晚上值一次班,直到公司关门,因此在这些天的晚上,我很少11点以前回家。如果晚上要值班,我们就在6点钟交班。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多少时间进行自我提高,更别提让家里留些钱给我买书了。不过,我找到了一种打开文学宝库的方法,它似乎就是上帝赐给我的福祉。
詹姆斯·安德森上校——但愿我写对了他的名字——向大家宣布,他将为孩子们开放他那座藏书400册的藏书室,这样的话,每个年轻人都能在星期六下午借走一本书,而在下个星期六,这本书就可以换成另外一本。我的朋友托马斯·N.米勒提醒我说,安德森上校的图书是首次向“工人小伙子们”开放的,于是,问题就来了,信使和职员等人并不是普通劳动者,是否有权借书呢。我给《匹兹堡电讯》写了一封短信,这是我第一次跟出版社沟通。我在信中主张,我们不应该被排除在外;尽管我们现在不是普通劳动者,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从事过这些职业,因此,我们也是真正的劳动者。可爱的安德森上校立刻就扩大了借书范围。因此,第一次作为一名公众作者露面,我就取得了胜利。
我亲爱的朋友汤姆·米勒把我介绍给了安德森上校。他是我朋友圈子里的一员,住在安德森上校家附近。就这样,“地牢”墙上的窗户打开了,知识之光倾泻进来。我随身带着书,从工作期间的休息时间里挤出时间来看书。每天工作的辛苦,甚至是值夜时的漫长煎熬,都因书籍而变得精彩。一想到星期六又可以借到新书,未来就变得光明起来。就这样,我熟读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以及班克罗夫特[30]的《美国史》——我读这本书比任何一本书都来得仔细。我尤其喜欢拉姆的散文。不过,除了学校课本里的选文以外,当时我对伟大的文学巨匠莎士比亚还一无所知。我对他的喜爱还是后来在匹兹堡的老剧院里培养起来的。
约翰·菲普斯、詹姆斯·R.威尔逊、托马斯·N.米勒、威廉·考利——我的朋友圈子里的成员——分享着对安德森上校藏书室的宝贵使用权。由于他的明智和慷慨,那些本来无从获取的图书成了我唾手可得的东西;而我对文学的爱好也要归功于他,就算拿人类积累的所有财富跟我交换,我也不会拿它去换。如果没有对文学的喜爱,生活就是平淡难耐的。没有什么比这位好心上校的善行更能使我和我的伙伴们远离坏人和恶习了。后来,当财富向我微笑时,我的职责之一就是为我的恩人树立一座纪念碑。这座碑矗立在我为阿莱干尼捐建的钻石广场的礼堂和图书馆前。碑铭如下:
致宾夕法尼亚西区免费图书馆的创始者詹姆斯·安德森上校。他向工人小伙子们开放自己的藏书室,并在星期六下午充当图书管理员,在这项高尚的工作上,他不仅献出了自己的图书,还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这为“工人小伙子们”开启了一座宝贵的知识和想象的宝库,一座能使年轻人进步的宝库。怀着感激和怀念之情,“工人小伙子们”当中的一员安德鲁·卡内基,树立了这座纪念碑。
这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礼物,它还不足以表达对他为我和伙伴们所做的一切的深切感激。书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财富,而这座宝库正好适时地向我打开了。图书馆的主要好处就在于,它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年轻人们必须自己去获取知识,没有人可以例外。多年以后,我发现,丹佛姆林的五个织布工把自己的少量图书集中起来,成立了镇上第一家流动图书馆,而我父亲是五人当中的一员,这给了我极大的满足感。
这家图书馆的历史很有趣。在发展过程中,它的地址迁了不下7次。第一次迁址是创始人发起的,他们把书放在围裙和煤桶里,从织布铺子搬到另一个地方。毫无疑问,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之一,就是我父亲是家乡第一座流动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又幸运地成为最后一座流动图书馆的创始人。我常常在公众演说中表示,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出身能让我用创始图书馆的织布工的出身去换。在图书馆的创办上,我不知不觉地追随着父亲——这项事业吸引着我,这种吸引可以说是天意——它曾给了我强烈的满足感。像我父亲这样的先导是值得追随的,他是我熟悉的人当中最美好、最纯粹、最仁慈的人。
我曾讲过,是剧院第一次激起了我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在我当信使的日子里,福斯特先生把老匹兹堡剧院管理得红红火火。公司对他的电报业务是免费的,而报务员也可以免费看戏,信使在某种程度上也享有这种特权,因此,信使们有时会把下午晚些时候到达的信件收起来,直到晚上才把它们送到剧院门口,然后不好意思地请求剧院的人允许他们溜到楼上的第二排座位看戏——这个请求总是能得到应允。小伙子们常常轮流去送信,这样一来,每个人都有偷看的机会了。
就这样,我熟悉了绿色幕布后面的世界。剧院里上演的通常是场面宏大的剧目,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足以让一个15岁的年轻人眼花缭乱。我不仅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场面,也从来没有进过剧院和音乐厅,而且从来没有见过任何形式的大众娱乐。我们被奇妙的舞台折服了,不愿错过一次看戏的机会。
在当时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狂风”亚当斯在匹兹堡上演莎士比亚的一系列剧目时,我的戏剧品味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除了莎士比亚,我对谁的剧目都不感兴趣。以前我还不知道语言里蕴藏的魔力,但现在我已经能轻而易举地记住他的台词了。一切节奏和旋律似乎都在我的内心找到了栖身之地,融合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并且一触即发。这是一种新的语言,戏剧的表现手法使我欣赏到了它的魅力,因为直到看到《麦克白》,我才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产生兴趣,可当时我并没有读过那些剧本。
又过了很久,我在《罗英格林》中领略到了瓦格纳的魅力。我曾在纽约音乐学院听过瓦格纳的一小段《罗英格林》序曲,当时我就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激动。他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天才。他是一架新梯子,顺着这架梯子往上爬,人就能得到提升——他跟莎士比亚一样,成了我的新朋友。
也许我该在这儿提一提同时期发生的另一件事。阿莱干尼的少数人——总数可能不超过100人——自发成立了斯韦登博格教会,而我们的美国亲戚是教会里的名人。在脱离长老教会以后,我父亲加入了这个教会,当然,我也被带了去。然而,我母亲对斯韦登博格教不感兴趣。尽管她常常劝大家尊重一切形式的宗教,抵制神学争论,但她自己对宗教却非常保守。
我第一次爱上音乐就跟斯韦登博格教会有关。教会赞美诗的附录上有一段短短的清唱剧选段,我本能地对它产生了兴趣。尽管省略了许多声部,但我还是唱得很有“表情”,因此成了唱诗练习的常客。我有理由认为,由于我对唱诗的热情,指挥考森先生常常对我在唱诗班里发出不和谐音表示谅解。当我还是个无知的孩子时,我曾挑选了一些自己最喜欢的选段,后来当我全面地了解清唱剧时,我很高兴地发现,其中有几段恰恰被音乐界尊为亨德尔的音乐瑰宝。由此可见,我的音乐教育是从参加匹兹堡的斯韦登博格教会的小型唱诗班开始的。
然而,我决不会忘记,是父亲哼出的那些无与伦比的家乡民谣,为我对美妙音乐的热爱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几乎每一首苏格兰老歌我都耳熟能详,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要使一个人的音乐鉴赏力提高到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高度,听民谣是打基础的最好方法。父亲是我所见过的嗓音最美妙、抒发的感情最凄悲的歌手之一。尽管没有遗传他的歌喉,但我或许遗传了他对音乐和唱歌的爱好。孔夫子的惊叹常常在我耳边回响:“音乐,是神灵神圣的语言!听到你的召唤,我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