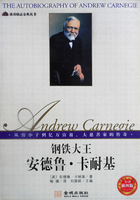
第8章 匹兹堡·我的工作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我能找些什么事儿做。我刚满十四岁,很想找一份工作,这样我才能使这个家在新的地方有所起色。在我看来,对前途的希望曾是一个可怕的噩梦。当时,我的想法都集中在一个决定上,那就是我们应该挣到足够的钱、省下足够的钱,这样的话,每年才有300美元的积蓄——平均每个月就得创造25美元。我算出的这个数目,能使我们不依赖他人,自力更生。当时,一切生活必需品都非常便宜。
霍根姨父的弟弟常常问我父母,打算让我做什么,有一天,我所见过的最不幸的场面出现了,让我永远也忘不了。霍根先生怀着世界上最善良的意图,对我母亲说,我是一个有希望的、好学的男孩,因此他想,如果为我准备一个篮子,里面放些小玩意儿让我去卖,我就可以去码头周围叫卖,还能挣到数目可观的钱呢。我永远也弄不明白怒火中烧的母亲当时的意图,因为正坐着做针线活儿的她一听到这话就跳了起来,张开双手,在他面前挥动。
“什么!叫我儿子去做小贩,在那些码头上的粗人堆里混!真是那样的话,我宁愿把他扔进阿莱干尼河。你给我走开!”她指着门口叫道,于是,霍根先生走了。
她就像一位悲剧中的女王那样站在那里。接着她哭了起来,但只哭了一会儿。随后,她把两个儿子抱在臂弯里,对我们说,不要介意她的鲁莽。世界上有许多事我们都能做,我们能够成为对社会有益、受人尊敬的人,只要一直都做正确的事。海伦·麦克格里格在答复奥斯伯迪斯通时威胁着要把她的囚犯“剁成碎片,就像格子呢上的图案那样”,而母亲的行为就是她的翻版。但是,母亲发作的原因跟她是不一样的。这不是因为霍根先生建议的职业是一种默默无闻的劳动岗位——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无所事事是可耻的,而是因为那种职业有点儿无业游民的性质,在她看来不太体面。她认为与其那样,还不如去死。是呀,母亲宁愿两臂搂着她的两个儿子,跟他们一起离开这个世界,也不愿意年纪轻轻的他们跟低贱的伙伴混在一块儿。
回想早年发生的这次冲突,我可以这么说:在这块土地上,没有比我们更骄傲的家族了。整个家族都拥有敏锐的荣誉感和独立自尊的意识。沃尔特·司各特说,伯恩斯拥有他所见识到的最非凡的见解。我可以说,我母亲也是如此。任何卑贱、低劣、虚假、诡诈、粗俗、阴险或搬弄是非跟她那种崇高的灵魂都是格格不入的。有了这样的父母——父亲也是一个天生的贵族,一个大家都喜欢的圣徒——汤姆和我便不由自主地养成了端正的品性。
这件事发生后不久,父亲觉得有必要放弃织布生意,于是就在我们居住的阿莱干尼市的棉厂找了一份工作。棉厂是一位苏格兰老人布莱克斯托克先生开办的。父亲还在这家厂子里给我找了一份绕线的工作,因此,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从那儿开始的,每周的工资是1.2美元。那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冬天,我和父亲不得不在黑暗中起床和吃早餐,在天亮以前赶到工厂,然后一直干到天黑以后,只有午餐期间能稍事休息。工作是紧张的,我无法从工作中得到一点儿乐趣;不过,坏事也有好的一面,因为这份工作让我感到,我正在为我的世界——我的家庭做一些事。在此以后,我挣了几百万美元,但是,它们给我的快乐还不及第一个星期的工资给我的快乐多。现在,我成了家庭的帮手,是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人,而不完全是父母的负担了。
不久后,约翰·海先生——阿莱干尼的苏格兰线轴制造商想招一个男孩,于是就问我是否愿意为他干活儿。我去了他那儿,每周的工资是2美元,但这份工作起初甚至比工厂的工作更令人厌恶。在线轴厂,我不得不看管一台小型蒸汽机,还要在地下室里烧锅炉。工作对我来说太繁重。我夜以继日地坐在机架上调整气压表,唯恐什么时候蒸汽气压太低,会使上面的工人抱怨动力不足,而如果气压太高,锅炉就可能爆裂。
不过,这一切我都瞒着父母,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麻烦。我必须做一个男子汉,自己承受一切。我的希望很高,每天都在寻求某种改变。我并不知道这种改变是什么,但我确信,如果我坚持下去,这种改变就会发生。此外,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会问自己,华莱士会怎么办,一个苏格兰人又该怎么办。我确信一点,他决不会放弃。
有一天,这种改变发生了。海先生要制作一些广告。他没有书记员,而他自己的书法又很糟糕。他问我能写什么书法,并提供了一些内容让我写。他对我写的东西很满意,认为以后让我来为他写广告,事情就好办了。除了书法,我还擅长算术。他很快就发现,让我干另一种不那么单调乏味的活儿,对他是有好处的——此外,我想这位可亲的老人对我这个白头发的男孩产生了好感,因为这位老人是个苏格兰人,有一颗善良的心,希望把我从机器旁边解放出来。
现在,我的职责是把刚做好的线轴放在大油桶里浸泡。幸好海先生留了一间屋子来完成这道工序。我一个人在屋里干活,不过,并不是所有问题我都能解决。我为自己的脆弱感到愤怒,但这种愤怒却不能驯服我那极不听话的胃。我始终无法克服油味儿产生的反胃,甚至华莱士和布鲁斯到这时都帮不了我。但如果我因此不吃早饭或午饭的话,我反而有更好的胃口吃晚饭,还能把分配的工作做完。一个真正的华莱士和布鲁斯的信徒不会放弃,否则,他宁愿去死。
我在海先生这里干的活儿的性质跟棉厂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我还结识了这位待我十分友善的雇主。海先生采用的是单式记账法,这我能帮他应付;但我听说,所有大公司采用的都是复式记账法,在跟我的伙伴约翰·菲普斯、托马斯·N.米勒和威廉·考利商量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决定在冬季参加夜校,学习更复杂的记账体系。于是,我们四人在匹兹堡的威廉姆斯先生开办的夜校里学到了复式记账法。
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当我下班回家时,有人告诉我,电报公司的经理大卫·布鲁克斯先生曾向我姨父霍根打听,问他是否知道上哪儿去找一个能做信使的优秀男孩。姨父和布鲁克斯先生都是狂热的跳棋手,这个重要问题是在一局终了之后提出来的,而这件“小事”让却最重要的事情悬而未决。一个字、一个眼神、一种口音也许不仅会影响个人命运,还会影响国家命运。年轻人应该记住,上帝最好的礼物常常是挂在小事上的。
姨父提到了我的名字,说他要去问问我,是否愿意接受这个职位。我记得很清楚,家人为此召开了一个讨论会。毫无疑问,我高兴得发疯。我比任何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都更渴望自由。母亲同意我去,但父亲则想打消我的念头。他说,这项工作对我的考验太大,而且我太年轻太瘦小了。他们给的工资是每周2.5美元,这就证明,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更强壮的男孩。他们可能会要我深夜去城外送电报,而我可能会遇到危险。总之,父亲说我最好呆在原来的岗位上。但最后他收回了反对意见,想放手让我试试;我猜测,他已经找过了海先生,并跟他商量了这件事。海先生认为,这份工作对我有好处,尽管他说这为他添了麻烦,但他仍然建议我去试试;他还很好心地说,如果我失败了,还可以回到原来的岗位上。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他让我过河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父亲想陪我一块儿去,我们最终决定,他只陪我到福斯伍德大街拐角处的电报公司就行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预示着一切顺利。父亲和我穿过阿莱干尼抵达了匹兹堡,从我家到那儿差不多有两英里远。到了公司门口,我让父亲在外面等,坚持要独自上二楼去见那位伟大的先生,从此得知自己的命运。也许是有什么在引导我这么做,因为当时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像美国人了。起初,孩子们常常叫我“苏格兰佬!苏格兰佬!”而我答道,“是的,我就是苏格兰佬,我也为这个称号感到自豪。”但是,在我的语言和谈吐中,宽泛的“苏格兰式”却逐渐缩小到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了,而且我想,如果我单独跟布鲁克斯先生见面,会比我好心的苏格兰老父亲在场时表现得更好,因为他可能会笑话我的装腔作势。
我穿上了自己唯一一件为表示庄重,通常只在安息日穿的白色亚麻衬衫,再在外面套上短上衣和在星期天穿的整套行头。当时以及进入电报公司工作以后的几周里,我都只有一套亚麻夏装;每个星期六晚上,即使这天晚上我值夜班值到快要午夜的时候才回来,母亲都会把这些衣服洗干净、熨平,这样我在安息日的早上就有整洁的衣服穿了。当我们在西方世界里奋力打拼时,这位女英雄为我们做了一切。漫长的工作时间也考验着父亲的体力,但他也像英雄一样打了好仗,而且不断地给我鼓励。
面试是成功的。我小心翼翼地解释说,我对匹兹堡不熟,也许我干不了这份工作,也许我的身体还不够强壮,但我需要的只是考验。他问我,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公司上班,我说,如果需要我留下来,我现在就可以留下来。如果抓不住机会,那就犯了大错。得到这份工作以后,我就打算尽量留在匹兹堡。布鲁克斯先生十分好心地叫来了另一位男孩——公司还需要另外一位信使。他让他带我看看公司,并让我跟着他学业务。我很快找到机会,跑到街角,告诉我父亲一切顺利,让他回家告诉母亲,我已经得到了这份工作。
这就是1850年我生命中第一次真正起步的经过。以前,我在阴暗的地下室里操作蒸汽机,每周挣2美元,弄得浑身煤灰,看不到生命中有一点儿起色,而现在,我就像上了天堂,是的,在我看来就是天堂,因为我身边还有报纸、钢笔、铅笔和阳光。每时每刻,我都能学到知识,或者发现自己的知识是多么贫乏、还有多少知识要去学。我感到脚下有一台梯子,而我必然要往上爬。
我只担心一点,那就是我无法迅速地熟悉许多需要发信的商家地址。因此,我开始注意这些商家的特征,从街道这边观察到街道那边。晚上我就挨个儿背诵这些商家的名字。不久以后,我就能闭上眼睛,从一侧的街尾到街头,把每家商店的名字按正确顺序说出来,然后再从另一侧的街头到街尾,把每家商店的名字按正确顺序说出来。
下一步要做的是认识人。如果信使认识商店里的成员或雇员,这会给他带来很大好处,而且通常都不用跑远路,因为他可能会碰见一个正要回自己办公室的员工。在这条街上送信的小伙子们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耐。而且,如果一个大人物(对信使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大人物)因此在街上停下脚步,并且常常关注和称赞这个小伙子的话,这个小伙子就会感到分外得意。
1850年的匹兹堡跟现在的匹兹堡今非昔比。那时它还没有从1845年4月10日的大火中恢复过来——那场大火把这座城市的整个商圈都毁了。市里的房屋主要是木制的,只有少数房屋是砖房,而且没有一座是耐火的。匹兹堡市内及周边的全部人口不超过4万人。城市的商业范围还不到第五大街,而当时的第五大街还是一条十分寂静的街道,仅仅因为有一座剧院而闻名。联邦街和阿莱干尼有一些稀稀拉拉的商铺,它们之间都有很宽敞的开阔空间,我还记得在现在的第五区正中心的池塘上溜冰的情景。我们在数年以后成立的联合铁厂的厂址在当时还是一块卷心菜田。
罗宾逊总经理是第一个在俄亥俄河以西出生的白人孩子,我替他送过许多电报。我目睹了第一条电报线从东面延伸到匹兹堡,后来,我还目睹了第一列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洲铁路线运营的火车从费城经运河运来,在到达阿莱干尼市后,被人们从一艘平底船上卸下来。当时,费城和东部地区之间还没有通铁路。乘客先通过运河到达阿莱干尼山脚下,越过这座山以后,再乘火车行30英里到达霍利迪斯堡,然后通过运河到达哥伦比亚,接着乘火车行81英里到达费城——这段旅程一共耗时3天。
当时,由于城际日常交通体系的建立,往返于匹兹堡与辛辛那提的蒸汽班轮的到岸或启程就是匹兹堡的盛事。匹兹堡是从俄亥俄河到运河的大型中转站,因此,从匹兹堡运往东、西部地区的商品使它的商业规模壮大了起来。有座轧铁厂已经开始轧铁,但没有轧出一吨铁,后来的许多年里也没有产出一吨钢。这座铁厂是第一家由于缺乏合适的燃料而彻底破产的厂商,尽管世界上最值钱的焦煤离他们只有几英里远,他们也没有想到,用于燃烧焦炭以冶炼铁矿石的天然气也原封不动地在这座城市底下埋藏了几个世纪。
信使工作很快就使我认识了城里的几个头面人物。匹兹堡的律师业很有名。威尔金斯法官是律师业的领头人,他和麦克坎德里斯、麦克卢尔法官、查尔斯·夏勒及其合伙人埃德温·M.斯坦顿(后来伟大的战时大臣)这几个人我都很熟悉——特别是后者,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好心的他就开始关注我了。商业界名人托马斯·M.豪、詹姆斯·帕克、C.G.于塞、本杰明·F.琼斯、威廉·索、约翰·查尔范特和哈里上校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现在仍然健在),信使们都拿他们当自己的榜样。
总的来说,我的信使生涯是快乐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跟朋友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后来,高级信使晋升了,需要一个新人来替他,来的这个新人名叫大卫·麦卡戈,也就是后来阿莱干尼山谷铁路公司的著名负责人。他成了我的同伴。我们的工作是递送来自东线的电报,另外两个小伙子则递送来自西线的电报。东电报公司和西电报公司当时是分开的,尽管它们都在同一座楼里。我和“戴维”很快就成了铁哥们儿。他也是苏格兰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尽管戴维生在美国,但他父亲跟我父亲一样,都是地道的苏格兰人,甚至从口音上听也是如此。
戴维来后不久,公司又需要增加信使了,于是就问我是否能找到合适的人。我毫不费力地找到我的密友罗伯特·皮特克恩——后来接替我担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公司负责人和总代理的人就是他。罗伯特跟我一样,不仅是苏格兰人,还是土生土长的苏格兰人。于是,“戴维”、“鲍勃”、“安迪”这三个苏格兰小伙子就担负起了递送匹兹堡西线所有电报的责任。当时,每周2.5美元的工资算得上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每天早上打扫办公室是我们的职责,由大伙儿轮流来做,由此可见,我们都是从基层做起的。后来伟大的奥利弗兄弟制造公司的总裁H.W.奥利弗阁下和律师W.C.莫兰也进了这两家电报公司,并且也是从这些活儿做起的。在生活的赛跑中,上进的年轻奋斗者们不必畏惧富人的儿子,也不必畏惧他的外甥或其他亲戚,就让富人们瞧瞧从打扫办公室起家的“黑马”吧。
那时,信使能得到许多“好处”。城里有一些水果批发铺子,有时我们及时地送到了电报,就能得到一整袋苹果;有时面包店和糖果店的人也会送些香甜的糕点给我们。信使能见到一些和善可敬的人,他们说的话让信使们感到舒服,他们还会因他送信送得及时而称赞他,也许还会请他在回办公室的路上帮他递一封信。据我所知,信使这个行当最容易使一个小伙子变得引人注目,而这正是一个真正聪明的小伙子飞黄腾达所需要的东西。聪明人总是在物色聪明的小伙子。
当我们送的信超过一定的数量,公司就允许我们每封信收取10美分的额外费用,这是信使生涯中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可以想象,我们都急切地关注这些“10美分信件”,为这些信件的递送权而争吵。有时大伙儿还会争先恐后地抢着递送10美分信件。这是引起我们激烈争吵的唯一原因。为了解决问题,我提议把这些信件集中起来,然后在每周末平均分钱,大家还委任我为出纳。后来,大伙儿再也没有吵过嘴,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这种将额外收入集中起来而不产生人为价值的做法,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也是我在财务体制上的第一次尝试。
小伙子们认为,自己完全有权花掉这些额外的津贴,因此大多数人都在隔壁的糖果店里建立了账户。有时,这些账户透支极大。于是,我这位出纳不得不以适当的方式告知糖果店店主,说我不会为这些贪吃的小伙子们欠下的债负责。长着满口糖牙的罗伯特·皮特克恩是小伙子们当中对我的做法反对最强烈的一个。有一天,当我责怪他的时候,他神秘兮兮地跟我解释,说他胃里有一些活生生的东西,如果不喂糖给它们的话,它们就会啃掉他的内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