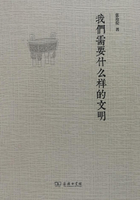
自序
临近岁末,我编完自己最近的一部论文集,郑重取名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这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书名,而是最近十余年我自己思考的种种问题背后的一个总问题。回顾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愈益觉得此乃全体人类不能不思的重大问题。
最近五百年,西方人以“文明”的名义征服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被征服与被改造者也因为“文明”而甘心被征服和改造,甚至以为那种以血与火为代价的征服将使他们逐渐进入文明的境地,却没有想过这种以大炮开路的文明是否真是人类的福音。另一方面,西方人面对被他们征服的世界的其余部分,也骄傲地自称自己代表“文明世界”。尽管不是没有少数先知先觉者从一开始就对用资本加大炮开路的文明嗤之以鼻,但多数人还是对这文明无比向往,认为一旦实现的话,不啻人间天堂。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使得现代文明一直被物质繁荣和制度建设掩盖的阴暗面,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眼前。如果说,此前在西方还只有一些思想特别敏锐之士对现代文明提出质疑和反思的话,那么20世纪以来这种质疑与反思几乎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一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西方思想的成就,都与这种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和反思有关。
在中国,进化论的信徒们相信,正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现代文明或没有建成现代文明(没有完成现代化),所以我们应该无保留地拥抱现代文明,对其的任何质疑与反思,在政治上是反动的、经济上是有害的、文化上是落后的、社会效应上是消极的。我们始终相信,只要“融入主流文明”,也就是西方人开其端的现代文明,我们就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对于这种文明几百年来表现出的本质缺陷和深层次的问题,不愿正视,更不愿反思和批判,甚至可笑地以为,至少在中国,思考这些问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还没有现代化(即达到现代文明),任何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都会妨碍我们的现代化进程。
但历史不会那么温情与天真,它不断将现代文明的残酷真相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现在人们面前。21世纪还过了不到20年,人们已经发现,文明的危机不但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是不断地以超乎常理的荒谬和野蛮挑战人类良知和想象力的底线。只有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和麻木不仁者,才会继续他们现代文明的迷梦。当恐怖袭击、种族和宗教残杀、经济衰退、生态危机、气候灾难、道德崩溃像天气预报一样成为媒体报道的日常内容时,人类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吗?
中国古代已经有文明概念,虽然与西方的civilization概念并非毫无交集之处,但却有自己的特殊规定。《舜典》“浚哲文明”之“文明”,指的是深邃智慧造成的世界万事万物合理有序,光明美好。《易·文言》的“天下文明”之“文明”的意思与之相似,即天下人受教化而万事开化。“文明”在中国是指一种精神、文化、道德上高度合情合理的状态,它的中心在精神教化和开化,而不在物质的开发;在文化自觉的纯粹与精致,不在对于心与物的技术操控;在于人的完美与完善,不在人欲的无限满足和放纵。与之相比,civilization一词偏重社会发展和物质与精神资源的开发。这就使得它无法完全覆盖精神层面的东西,如人类生存各种要素的平衡协调、普遍的教化与道德,以及社会与人际关系的公正与和谐。这就使得西方人(尤其是德国人)用“文化”这个概念来弥补civilization概念上述的不足。但中国人由于自身原来的“文明”一词的含义,不免会要求“文明”概念应该包含上述的非物质发展方面的内容。当现代文明不断暴露出其“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一面时,尤其当文明与野蛮的界限日趋模糊之时,人类真的应该问自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是当下这种将我们和地球带向毁灭的文明,还是一种全新的文明?
我是从事哲学研究的。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到近代之前,根本就不是什么学科,而是人类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如果说西方哲学产生于惊异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则产生于忧患。《易·系辞下》有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催生了中国哲学,也推动了中国哲学。西方人虽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将忧患意识视为哲学的动力,但伟大的西方哲学家几乎无一不对他们面临的时代问题有深切的感受,他们的哲学也无一不透露出他们的忧患意识。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哲学逐渐成了纯粹理论和一门“学科”。正是哲学的“专业化”造成了哲学的危机:与那些多少有些实用的学科相比,越来越琐碎和技术化的哲学的确只能是一小部分专业“哲学家”自娱自乐的玩意,无法具有它在历史上曾长期具有的那种现实性和感召力。
我是在自己生命的忧患时刻接触到哲学,哲学让我明白生活的荒谬实际反映了时代的荒谬,人生的问题也是历史的问题。哲学要求以哲学家自居的人不仅仅替自己思考,也要替人类思考。哲学之所以在今天这个以“有用性”为最高准则的世界还不绝如缕,就是有一些真正的哲学家没有放弃对世界和历史的思考。他们知道自己也许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世界并不是纯粹思想的世界;但他们相信可以揭示一个不同的世界,历史会因这些揭示而有所不同。
这就是哲学家的价值所在。哲学家与哲学教授是不同的概念(尽管不少大哲学家也确实是哲学教授,但人们首先想到他们是哲学家。如问一个人黑格尔是什么人,回答一定是“哲学家”,而不会是“哲学教授”),这是当年洪谦先生对我的教诲。在他看来,哲学家首先应该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关心世道沧桑;而哲学教授只要具有诸如逻辑推理、概念分析之类的技术能力就行了。世上有太多的哲学教授,哲学家却是越来越少。我是否是真正的哲学家要让世人来评判,但的确不想只当上述意义的哲学教授。所以我在哲学研究上不太“安分”,从不把自己限定在哪个公认的“专业领域”。这当然不是说我的研究随心所欲,不够“专业”。真正的哲学家没有不专业的,即使是像尼采和克尔凯郭尔这样的人,只有被学院哲学彻底规训了的人才会认为他们“不专业”。在中国,又有谁敢说庄子不如某个现代大学教授专业?
哲学是自由的思想,而“专业”即使从字面上看都是对自由的限制。对一个哲学家,我们只该问他有没有思想,不该问他是否专业。从有大学哲学系、哲学变成学院专业以来,有过无数非常“专业”的哲学教授,如今安在哉?那些根本通不过现代学院专业标准的哲学巨人,如中国的老子和庄子,西方的柏拉图、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却将永远被人作为哲学的典范而传承下去。我自知离那样的境界尚有距离,具体表现就是还在写现代学院哲学类型的论文。不过,无论是论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或是讨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都是有着深层的现实关怀,针对我所体察到的时代问题。细心的读者当会读得出我的关注所在。但这并不是说这些论文根本就不是学术论文;它们当然也是学术论文,但首先是哲学论文,哲学论文往往是通过讨论学术问题的方式来讨论时代问题。人类哲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指不胜屈,无须一一列举。
我始终认为我们的时代问题归根结底是现代性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问题主要体现为现代中国自我建构和自我理解的问题。毋庸讳言,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思维与话语,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和自我理解;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这种自我建构和自我理解的辩证法,必然要求对之进行批判和解构,否则这种自我建构和自我理解就不可能最终完成。这种批判和解构,必然是世界现代性批判的一个迟到但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的全部哲学活动和哲学思考可以说是基于这个基本认识进行的。它试图在弄清我们今天之所是的基础上,探索未来的种种可能性。它主要是质疑与批判,而非教条地建构或背书。我始终认为,哲学始于怀疑和批判(忧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怀疑与批判),哲学没有第二个出发点。真正的哲学恰恰是通过怀疑与批判来建构的。
这本文集由三种类型的文字组成:一类是我历年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正规学术论文;第二类是我写的一些学术书评;第三类是演讲稿。第一类的文章引证齐全,符合所谓“学术规范”;第二、三两类的文字大都把引文出处略去,因为当初发表时由于特殊的文体——书评和演讲稿——不要求引文注明出处。在编此文集时我一仍其旧,不再补上引文出处。
是为序。
张汝伦
2016年岁末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