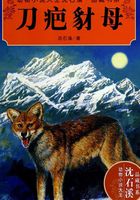
第4章 刀疤豺母(4)
强巴也意识到我们处境危险,很无奈地将绳索解开了。黑脖子母驴翻身站了起来,委屈地吭吭叫着,跑回野驴群去。
我们以为,释放了黑脖子母驴,野驴群就会停止对我们的骚扰和攻击。但我们想错了,驴群依然围着我们不放。我和强巴朝坡顶移动,只要回到那丛灌木,拿到枪,朝天开上几枪,就一定能让这些狂热的野驴冷静下来,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
强巴挥舞绊马索,啊啊叫着,我也像练武术一样挥拳踢腿,嘿嘿高喊,企图冲开野驴的包围圈。
我们离野驴还有十几公尺远时,白脸公驴突然转了个身,其他野驴本来都是头朝着我们的,此时也跟着一百八十度转弯,将屁股对着我们。我晓得,它们绝不是要开屁股展览会——驴屁股没什么美感,也不是要集体朝我们放屁熏死我们,集体朝我们喷粪臭死我们,而是准备施展野驴最具威力的尥蹶子战术。
凡马科动物,遇到敌害时,除了奔逃,有两种自卫方式,一是用前蹄践踏,二是尥蹶子。所谓尥蹶子,就是跳起来后腿猛烈朝后踢蹬。马科动物腿部肌肉非常发达,蹄子坚硬,尥蹶子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我曾在一篇报道中看到,一只金钱豹想猎杀一匹小马驹,愤怒的母马拼命尥蹶子,正好踢中豹的脑袋,金钱豹当场昏死过去。书本记载,野驴在荒野遭遇狼群,来不及躲避时,就会布下头朝内尾朝外的圆圈阵,集体尥蹶子,以对付狼的扑咬。
一百多头野驴,颠跳着尥蹶子,草叶纷飞,尘土漫卷,蔚为壮观。我和强巴别说逃出包围圈了,连东南西北都快分不清了。
白脸公驴被砸伤的嘴唇肿起好大一块,面目狰狞,一面踢蹬后腿,一面吭吭高叫,气焰十分嚣张。野驴们步步进逼,包围圈越缩越小,半径只剩下五六公尺远了。这样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铁锤似的驴蹄就会无情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会像足球似的被踢来踹去,从东边踢到西边,又从南边踹回北边,最后被它们踢进死亡的地狱之门。
我脊梁发麻,腿都软了,强巴的额头上也沁出一层冷汗。一个动物学家和他雇请的向导,以身殉职,死在驴蹄下,这难免不会被人笑掉大牙啊。
就在这危急关头,突然,呦(左口右欧)——坡顶传来一声尖厉的豺啸,大部分野驴就像听到了为它们敲响的丧钟,停止尥蹶子,惊慌地抬头张望。我也循声望去,哦,就是我所熟悉的那群金背豺,正从坡顶穿越而过。我心头一喜,据野外考察记录,野驴最惧怕的天敌不是老虎豹子,也不是狼群,而是豺群;野驴遇到老虎、豹子或狼群时,可以围成圆圈用尥蹶子的办法顽强抵抗,但同样这个本领,用到豺群身上,却丝毫不起作用,反而会加速送命。豺有一个其他猛兽所不具备的制伏大型猎物的绝招,就是跳到猎物的臀部,尖利的豺爪捅进猎物肛门,将猎物的肠子活活掏出来;野驴撅着屁股尥蹶子,无疑给豺施展捅肛门掏肠子的绝招提供了方便。
豺这种怪异的猎杀方式很龌龊很下流也很残忍,这大概也是豺的名声很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不管怎么说,野驴怕豺,就像老鼠怕猫,只要豺群从坡顶冲下来,该死的野驴群就会闻风丧胆,撒腿奔逃,我们也算解围了。
事实上,有好几头胆小的母驴已经摆开了逃跑的姿势。
但好几十秒钟过去了,豺群只是站在坡顶遥相观望,并没朝野驴群扑冲过来。我再仔细望去,不由得心凉了半截,我看见,许多豺嘴里都叼着肉块和骨头,所有的豺肚子都是圆鼓鼓的,这表明它们刚刚捕获了猎物,刚刚享用完一顿丰盛的大餐。豺同许多其他食肉兽一样,并非是喜好杀戮的屠夫,也没有为了消闲娱乐而去打猎的癖好。它们捕捉其他动物,是生存的需要,为了能使自己活下去。一旦混饱了肚皮,它们就没有兴趣再去追逐猎杀。这就是说,这群豺此时此刻没有扑咬野驴的冲动和欲望。
领头的刀疤豺母,摇了摇叼在嘴里的半只红毛雪兔,从嘴角呜呦发出一声轻啸,转身欲走。对它来说,荒原各种不同的动物打斗厮杀乃司空见惯,毫无新鲜感可言,不值得观赏。
白脸公驴显然已经获取这群过路的豺不会前来干预的某种信息,萎瘪的气势重新又膨胀起来,吭吭叫着,朝我们蹦跶尥蹶子。其他野驴也抛却了惧怕心理,振作精神来对付我们。
一头母驴在离我仅两公尺的位置尥蹶子,虽没踢着我,但泥沙飞射到我脸上,我眼睛里也落进了沙子。白脸公驴趁我用手蒙着脸揉眼睛之际,绕到我身后,蹦跶跳跃,两只后蹄狠狠朝我踢来。我要是被它踢着,轻则腰杆断裂,重则一命呜呼。强巴发现了,一个箭步蹿上来,猛地把我推开,他自己躲闪不及,小腿被驴蹄蹭了一下。虽然只是蹭了一下,也疼得他咝咝倒吸冷气,站也站不稳了。
我朝坡顶的豺群大喊救命。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到要向豺群呼救的,也许是出于溺海人想捞救命稻草的心理,也许是潜意识里觉得刀疤豺母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我前两天曾在铁索桥上对陷入绝境的豺群网开一面,它也会帮我一次的。
不管怎么说,眼下只有这群豺能将我和强巴从这群疯驴中解救出来,我不能放弃最后的希望。
我看见,转身欲走的刀疤豺母又转了回来,面朝着驴群,三角形的耳朵竖得笔直,一副凝神谛听的模样。驴群团团围着我们,驴蹄刨起的泥尘遮挡了它的视线。我使劲跳着,拼命挥舞双手,让它能透过泥尘看见我。
我求生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刀疤豺母背上金红色的绒毛倏地恣张开来,吐掉口中那半只红毛雪兔,直起脖子呦(左口右欧)长啸一声,发出准备采取行动的指令。我看见,豺们纷纷吐掉叼在嘴里的兔肉和兔骨,慵懒的身体刹那间变得紧张,张牙舞爪地啸叫起来。
野驴们又变得慌张起来,停止尥蹶子,心惊胆寒地望着坡顶。
刀疤豺母率领豺群顺着缓坡冲了下来,夕阳西下,艳红的晚霞涂抹在豺金色的背毛上,像一片流动的火焰。驴群炸了窝,纷纷夺路奔逃,包围圈一下子溃散了。只有白脸公驴和另两头年轻的公驴还不服输,打着响鼻,将屁股对着冲在最前面的刀疤豺母,大概是想让刀疤豺母尝尝驴蹄的厉害。刀疤豺母到了白脸公驴的身后,白脸公驴唰地玩了个尥蹶子,驴蹄眼瞅着就要踢中刀疤豺母的下巴了,刀疤豺母敏捷地扭腰一闪,躲到两条驴腿之间,驴蹄踢了个空,它不等驴蹄落地,便纵身一跃,扑到驴屁股上。白脸公驴大概晓得豺会活掏肠子,魂飞魄散,像踩着火炭似的乱蹦乱跳,前蹄腾空身子竖得笔直,喊爹哭娘地吼叫。刀疤豺母被从驴屁股上颠了下来,白脸公驴再也不敢恋战,带着屁股上好几条被豺爪抓出来的血痕,飞也似的落荒而逃。另两头年轻的公驴也狂奔而去。
豺群冲着驴群的背影啸叫了一阵,不再追赶。它们本来肚子就是饱的,没必要耗费体力去追捕逃遁的野驴。
八
我们解围了,我们获救了,快要绷断的神经一下子松弛,顿觉极度疲惫,身体像稀泥似的瘫软下来。我趴在蚁丘上喘息,强巴坐在地上用袖管揩去额角的冷汗,搓揉被驴蹄蹭伤的小腿。我瞥了一眼,他小腿肌肉上有一大块淤血,已经肿了起来。
刀疤豺母来到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友好地甩动尾巴,慢慢将身体蹲伏下来。显然,它是认出我来后才率领豺群撵走野驴群的,它没忘记前两天我解救豺群的这份恩情。
我朝它挥挥手,示意它快带着豺群离去。我们已经脱离危险,不再需要它们了。它们毕竟也是茹毛饮血的猛兽,待在我们身边总让人心里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刀疤豺母知趣地站起来,啸叫一声,准备将散落在四周的豺召集在一起,撤回坡顶。
那只胸毛已秃光的老豺,经过我们的身边时,温和的眼光注视着我,像是在对我行注目礼,然后,又将眼光移向我旁边的强巴……突然,它神经质地蹦跳起来,呦啊发出一声惨啸,声音恐怖得就像有一支利箭穿透了它的心脏。所有的豺,如临大敌,尾巴一根根平举,背毛一片片竖起,豺脸一张张变得凶暴残忍。
我一下子蒙了,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胸毛已经秃光的老豺跑到刀疤豺母跟前,嘴吻对着嘴吻叽叽呦呦了一阵。我看见,刀疤豺母眼角上吊,嘴吻歪扭,刚才还挺温柔的脸霎时间像涂了一层冰霜,透出一种掠食者的冷酷。它冷飕飕的眼光盯着强巴,压低身体,伸直嘴吻,小心谨慎地一步步走过来,就像在检测布满疑点的危险物品。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涨得比簸箕还大。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胸毛已秃光的老豺认出了强巴就是三年前被豺群围困在罗汉松上的那个猎人,当然也就是将一条豺尾悬吊在歪脖子小树上的猎人,也就是摸进豺窝掳走八只幼豺的猎人,也就是用幼豺做诱饵放火烧荒差一点把整个豺群都赶进怒江去喂鱼的猎人。刀疤豺母瞪大眼珠、耸动鼻吻,一步步走近来,是要用敏锐的视觉和嗅觉来进一步确认这个事实。
都怪我,我只顾着让这些金背豺来对付那群疯驴,而忘了我的向导强巴同这些金背豺有着血海深仇。
强巴好像也从豺群的喧嚣与骚动中领悟到了什么,腾地站起来,攥紧拳头,双目圆睁,像头发怒的狮子。
呦(左口右欧)呜——刀疤豺母仰天发出一声悲愤的长啸。
这是验证,这是确认,也是指控。
随着刀疤豺母的这声长啸,豺们呼啦全围了上来,龇牙咧嘴,朝着强巴呦呦啸叫。
强巴拔腿往坡顶冲去。我晓得,他是想到坡顶那丛灌木去取猎枪,只要有枪在手,他就能和这些杀气腾腾的豺周旋一番。他的小腿被驴蹄蹭伤,一沾地就疼得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根本跑不快;即使他没有受伤,恐怕也跑不回坡顶去取枪的。在他刚跑出几米远时,好几只豺蹿到前头堵截他,胸毛已秃光的老豺和一只歪嘴巴雌豺从背后蹿跃,扑到他背上,把他扑倒在地。
众豺蜂拥而上,有的去咬他的胳膊,有的去咬他的腿,胸毛已秃光的老豺噬咬的目标是他的后脖颈,歪嘴巴雌豺则用尖利的爪子在他屁股上鼓捣,想活掏他的肠子。
强巴猛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拳打脚踢,将粘到他身上的豺推开。我赶紧跑过去,帮着他对付这些恶豺。
哗,我的一只衣袖被一只公豺咬下来了;咝,我的一只裤腿被一只雌豺撕破了。我心里很清楚,我和强巴手无寸铁,不是这些豺的对手,我们不过是在进行徒劳的抵抗而已,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被它们的尖牙利爪撕成碎片的。
呦(左口右欧)——刀疤豺母威严地啸叫一声,正缠着我们混战的豺纷纷跳开去,和我们脱离了接触,但没有跑远,而是团团将我们围了起来。
强巴的衣裳也被撕破了,肩头还被豺爪抓出数道血痕,幸好伤得不重。
呦呜——刀疤豺母的视线落到我的身上,蓬松的尾巴甩摆着,发出柔和的啸叫。
呦呜,呦呜,呦呜。其他豺也都望着我,或蹲或坐或趴,朝我摆出和平的姿势,急切地啸叫。
我懂了,刀疤豺母之所以要发出指令让缠住我们厮杀的豺退出来,是不想伤害我。它虽然是豺,倒也恩怨分明,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很明显,它们是要让我走,让我离开。
强巴似乎也看出了点蹊跷,推着我让我走:“你快走,它们好像不想为难你。你走,你快走!”
“不,我不走。”我不会抛下强巴不管,在野外考察中,他多次救过我的命。有一次我被一群马蜂追逐,无处躲藏,他挥舞树枝拼命抽打,将蜂群引开,我顺利脱险,他却身上被马蜂蜇叮出十几个包;就在刚才,他还把我从白脸公驴蹄下解救出来,自己被驴蹄蹭伤了小腿。我决不能为了自己活命,屈服恶豺淫威,出卖自己的朋友。
呦呦呜呜,豺群一个劲地朝我啸叫,催促我走。
“你快走吧,我跟它们结算三年前的血债,跟你没关系。”强巴将那根绊马索结成一个活套,咬着牙说,“你不用为我担心,我要勒断这些恶豺的脖子!”说着,他比量着要用绊马索扎成的活套去套离他最近的歪嘴巴雌豺。
我晓得,强巴是条硬汉子,不愿意连累我。
“强巴,你是我请来的向导,你要听我的。”我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绊马索,扔在地上,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他说,“来,趴下来,唔,跟着我做。”
我匍匐在地,手脚伸开,把自己的身体摆成一个大字,拧着脖颈,露出最易受到伤害的颈侧动脉血管。
“你这是在干什么呀?让这些恶豺更方便地来咬死我们?要向这些恶豺下跪求饶?”强巴满脸诧异地问,身体仍站得笔直,大有一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气概。他就是这样的人,宁肯死也不做软骨头。
“强巴,就算我求你了,快躺下来。我以后再跟你解释为啥要这样做。”我抱住他的脚用力一拖,把他拖倒在我身边。
我是想起刀疤豺母在铁索桥上乞求我网开一面时的情景,灵机一动,才决定采用同样的方式来渡过难关的。我晓得,身体平趴在地上,在豺的世界里表示屈服和放弃抵抗,朝对方暴露最易受到伤害的颈侧,其实是要平息对方的怒火,促使对方遵循豺社会的重要禁忌:不攻击诚心诚意的不设防的求和者。
在铁索桥时,刀疤豺母用这种姿势使我动了恻隐之心;我希望现在我用这个姿势也能使它大发慈悲。
刀疤豺母望着趴在地上的我和强巴,若有所思地垂下脑袋。
(左口右欧)——(左口右欧)——歪嘴巴雌豺和另外几只腹部吊着一排乳房的母豺恶狠狠地咆哮起来。我猜想,它们是被强巴掳走的八只幼豺的母亲,对它们来说,失子之痛是难以磨灭的,劫子之仇是一定要报的。它们不满意刀疤豺母的犹犹豫豫,它们在催促刀疤豺母对我们,不,准确地说是对强巴实施最严厉的报复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