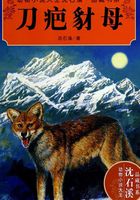
第3章 刀疤豺母(3)
悬吊的豺尾、关押的幼豺、残酷的私刑,突然间我脑子豁然一亮,找到了这几件事情间那条因果链。悬吊在歪脖子小树上的豺尾,明白无误地告诉豺群,有人要为三年前那条被豺群撕成碎片的藏獒报仇雪恨。紧接着,八只豺崽被掳掠,它们虽然找到关押幼豺的地方,但无力将它们营救出来。那条挂在树上的豺尾,是悬在豺群头上的闪着寒光的复仇的利剑。饱经风霜的刀疤豺母心里很清楚,它们不是人的对手,无法与复仇者抗衡。它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妥协就是让步。既然复仇者将那条豺尾高挂在树上,它们理所当然地以为,复仇者主要是针对肇事惹祸的断尾公豺来的。为了救出那八只幼豺,为了整个豺群的生存,它们决定牺牲断尾公豺。这虽然残酷,却是明智之举。刀疤豺母不忍心这样去做,却又不得不这样去做,因此在咬断了断尾公豺的脚杆后,会发出凄厉的啸叫,会像对待自己的豺崽那样吐出糊状肉糜去喂断尾公豺。
我想,我的推断是站得住脚的。
豺群走远了,我和强巴从山腰爬下去,来到荒山沟那棵小树下。暮色苍茫,黑老鸹的聒噪和断尾公豺的呻吟组合成世界上最难听的二重奏。但一见到我们的身影,它就咬紧牙关停止了呻吟。它知道我们会出现,没有任何惊恐不安。它虽然站不起来,但尽量挺胸昂首,艰难地保持着猛兽的尊严。它眼光里没有畏惧,也没有悔恨,只有悲凉和无奈。
强巴拉动枪栓,枪口对准断尾公豺的脑袋,骂道:“恶豺,你也有今天!唔,我要用你的豺头祭我的雪娇!”
断尾公豺仍倔强地抬着头。我想,它早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当众豺将它围在圆圈中间,像开公审大会似的朝它呦呦啸叫,它就应该料到将面对猎人黑森森的枪口。它不愿意送死,它曾冲开豺的包围圈,有机会逃之夭夭,但最后它还是回到了要将它置于死地的豺群中间。种群的利益战胜了求生的本能,在片刻的动摇后,它接受了豺群对它的制裁,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愿意以自己的死来换取整个豺群的安全和八只幼豺的生命。
我心里油然对它产生了一种敬意。
“轰”,强巴扣响了猎枪,一团青蓝色的硝烟,从枪口喷吐出来,将断尾公豺包裹起来……
歪脖子小树上的乌鸦惊叫着飞走了,就像一支送葬的小乐队。
“强巴,你也瞧见了,豺群替你惩罚了断尾公豺。刀疤豺母这样做的用意你也清楚,是为三年前的事向你赔罪。”我拍拍他的肩膀说,“我看,冤家宜解不宜结,你的雪娇的仇已经报了,把八只幼豺还给它们算啦。”
强巴浓眉紧锁,思忖了一会儿,摇摇头说:“不。我在埋葬我的雪娇时,发过誓,要把这群恶豺通通消灭。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不错,断尾公豺是杀害我的雪娇的罪魁祸首,但其他豺也罪责难逃。我是看着我的雪娇被这群恶豺你一口我一口咬死的。我记得清清楚楚,一只歪嘴巴雌豺用爪子将雪娇的肠子掏出来,当时雪娇还没死;一只黑耳朵公豺啃咬雪娇的心,那颗心还在噗噗跳动;几只半大的豺撕扯吞咽雪娇的腿肉,雪娇还没咽气……这是一群十恶不赦的豺,千刀万剐也难解我的心头之恨。”
“冤冤相报何时了。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别再想它了。”我劝慰道。
他缄默不语,执拗地摇摇头,过了好一阵才耳语般地轻轻说了一句:“这八只豺崽没参与杀害我的雪娇,报完仇后,我负责把它们养大,放归山林。”
六
纯粹从狩猎角度看,这称得上是个绝妙的办法,能把这群金背豺一网打尽,且我和强巴不会冒任何风险。
荒山沟的尽头是被称为一线天的狭长山谷,仅有五六米宽,满地蒿草,两边都是九十度的绝壁,连猿猴都难以攀登;出了一线天,是一座在滇北很常见的铁索桥,悬挂在两山之间,底下是湍急的怒江;铁索桥的桥面上铺着木板,人畜勉强可以通行。
强巴设计的具体步骤是:在山谷口的蒿草丛里撒些硫黄,将装着八只豺崽的柳条筐放在山谷中段,豺群听到豺崽的叫声后,会毫不迟疑地赶来援救,钻进一线天,便等于钻进了圈套。强巴在山崖上朝撒有硫黄的蒿草丛扔下火把,正值旱季,天干物燥,枯黄的蒿草肯定一点就燃,霎时间便会蔓延成一道火墙。这几日刮的是西南风,峡谷劲风,往怒江方向吹,豺群必然往江边逃,江边也是几十丈深的绝壁,唯一的生路就是铁索桥,而我早就守候在铁索桥上,等待浓烟升起,便抽掉桥面上两块木板。豺爪不比猴爪,能抓住滑溜溜的铁链攀缘而行,它们不是被背后的野火烧焦,就是从铁索桥上跌下怒江去被浪涛吞噬,没有一只豺能幸免于难。
强巴实践自己的诺言,用一根长长的麻绳,系在柳条筐上,火点燃后,即动手将柳条筐拉上山崖,以留下八只豺崽的性命。
强巴是个经验丰富的猎手,一切都按他的设想在进行。我看到浓浓的烟柱腾空而起,看到那只装有八只豺崽的柳条筐像乘电梯一样被拉上山崖,很快,便听到豺群呦呦(左口右欧)(左口右欧)的啸叫声。
我站在铁索桥中央,动手将桥面上的两块木板抽掉。
几分钟后,刀疤豺母便带着惊慌失措的豺群拥到桥头,看见我站在桥中央,刀疤豺母停住了脚步,四下张望。显然,它想寻找第二条可以逃生的路。但它很快明白,两边都是绝壁,除了这条铁索桥,没有第二条生路。它龇牙咧嘴,眼珠子瞪得溜圆,背毛耸立,脸上那条刀疤红得发紫,露出一副恶魔般的凶相,(左口右欧)(左口右欧)叫着,朝我奔来。我晓得,它想把我吓走,好率领豺群过铁索桥。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前面有一段三米长的桥面已变成了空心桥面,只横亘着两条拇指粗的铁链,除非它是豺类中的世界跳远冠军,绝不可能在晃晃悠悠的铁索桥上跳出这么远的距离来,除非它是会演杂技的马戏演员,也绝不可能像走钢丝那样踩稳细细的铁链越过这段空心桥面。
果然,刀疤豺母冲到空心桥前时,哀啸一声,停了下来,探出脑袋向桥底下的怒江望了一眼,立刻吓得缩了回去。这一段怒江十分陡峭,江心矗立着暗礁和矶石,汹涌而至的江水如野马奔腾,撞击暗礁,发出如雷的轰鸣声。其他豺跑到这儿,也都扭头往回走。
豺群拥挤在桥头,退退不得,进进不得,乱成一团。
枯枝败叶烧得噼噼啪啪响,烈焰腾空,一线天变成一片火海。风助火势,火扬风威,张牙舞爪的火龙渐渐逼近桥头。至多还有几分钟,野火就会蔓延过来。我看见,好几只豺都已经绝望了,神经质地互相噬咬起来,有一只胸毛已秃光的老豺,闭着眼睛,一步步沿着桥面往前走,显然是想在不知不觉中一脚踩空掉进江去,以减少临死前的恐惧和痛苦。
呦(左口右欧)——刀疤豺母仰天长啸,混乱的豺群这才稍稍安静些,互相打斗的豺停止了噬咬,胸毛已秃光的老豺也收敛了脚步,几十双豺眼盯着刀疤豺母,等着它拿出逃生的办法来。
刀疤豺母踏着碎步跑到桥中央,伫立在被我抽空了桥面的铁索前,定定地望着我。这一次,它的背毛没有恣张开,也没有龇牙咧嘴露出扑咬的凶相来威胁我;它嘴巴紧闭,蓬松的豺尾拖在地上,缩着脖子,显得很柔顺的样子。突然,它躺了下来,四条腿往外趴开,下巴贴在桥面,嘴吻上翘,耳郭下垂,露出柔软的易受伤害的脖颈,豺尾有气无力地摇甩,表情悲伤,呦呦呜呜,发出轻柔而又凄惨的啸叫。
我研究过豺的行为,当两只豺发生争执撕咬起来,斗败的一方就会做出刀疤豺母现在这种姿势,这是一种放弃抵抗、认输服输、无条件投降的姿势。在豺的社会里,一旦一只豺做出了这种屈服的姿势,另一方就会网开一面,停止扑咬。
在同类相争中,不咬认输者,是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禁忌。
这真是一只智慧超群的豺,它晓得豺群已陷入绝境,只有我才能让它们绝路逢生。
所有的豺,也都学着刀疤豺母的样,匍匐在地,朝我亮出易受伤害的脖颈,呦呦呜呜哀啸。
我的心一阵震颤。我本来就对强巴可怕的复仇手段持有不同意见。为了一条猎狗,就要把这群珍贵的金背豺全部消灭,这实在太过分了。我是动物学家,保护珍奇稀少的野生动物,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我想,我跟这群金背豺无冤无仇,我不应该帮着强巴对付它们。
野火蹿上铁索桥头,几团枯草,被火点燃,随风飘荡,像一群火鸟,飞落到铁索桥上。有一团燃烧的枯草,滚到刀疤豺母的背上,那块金色的背毛,吱吱被烧焦了,它烫得嘴都扭歪了,可还是匍匐在地,呦呦呜呜朝我哀求。
豺群已经火烧屁股了,要是我不帮它们,它们很快就会在火焰的驱赶中,像煮饺子似的一只接一只从空心桥面跌进波涛翻滚的怒江。
我不再迟疑,将一块木板伸过去,搭在被我抽空的桥面上。
木板还没放稳,豺们就一只接一只踏着木板飞跃而过,往对岸的丛林飞奔。
当豺群排着队,很有秩序地过桥时,刀疤豺母仍趴在桥面上保持着向我乞求宽恕的姿势,嘴里还呦呦呜呜地啸叫着。
顶多两分钟时间,七八十只豺全部从我伸过去的木板上蹿跃而过,安全地跑进对岸的树林。刀疤豺母这才站起来,最后一个踩着我重新铺设的木板越过那段空心桥面。来到我身边,它停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将嘴吻伸过来,在我裤腿上轻轻磨蹭了几下,呦呦(左口右欧)(左口右欧)叫了几声,好像是在对我放它们一条生路表示感激,然后才一溜烟越过铁索桥追赶豺群去了。
火龙蹿出一线天,蹿上铁索桥头,把木板铺设的桥面都点燃了,但金背豺群已逃得无影无踪。
事后,我对强巴扯了个谎说木板上的铁丝拧得太紧,我解了半天才解开,耽误了时间,结果才抽掉一块木板,豺群已到了桥上。他半信半疑地看了我一眼,长长叹了口气,没说什么。
七
没想到,被激怒的野驴是那么可怕,简直就像一群亡命之徒,盯着我和强巴不放。
我们是在山南一块平坦的牧场上找到这群野驴的。在我国,野驴被列为濒危动物,高黎贡山一带已有二十多年未发现野驴的踪影。我格外兴奋,躲在一丛灌木里,举着摄像机一个劲地拍摄。从我在书本上读到的资料看,野驴是一种机敏胆小的动物,因此,我根本没想到要对它们有所防范。
野驴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这群野驴共有一百多头。正值野驴交配季节,好几头年轻的公驴为争夺配偶互相啃咬,吭吭乱叫,斗得不亦乐乎。我拍摄了许多珍贵的镜头。好像故意要来抢镜头似的,一头黑脖子母驴啃着青草慢慢走过来,一直来到我和强巴藏身的灌木丛前。一点也不吹牛,近得我一伸手即可攥住驴腿。强巴从羊皮袋里掏出一根尼龙绳,绳子的一头系着一块月牙形铅巴,这是高黎贡山一带牧民特有的绊马索,逮马时,将绳索用力朝马腿扔去,月牙形的铅巴会将绳索缠绕在马腿上,马就会被绊倒在地。强巴朝我眨眨眼,做了个抛扔绳索的手势。我明白,他想绊倒那头黑脖子母驴。这主意不赖,能活捉一头野驴,对我的研究大有用处,我点了点头。
强巴突然站了起来,啊地大叫一声。平地爆出一个人来,黑脖子母驴大惊失色,扬起前蹄,身体竖立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强巴一扬手,将绊马索缠住黑脖子母驴的后蹄。
野驴体积只有普通马的三分之二大,但力气却不比马小。黑脖子母驴蹦跶跳跃,顽强地朝前奔跑,强巴拽不住它,被它牵出灌木丛,被它牵着在草坡上踉踉跄跄地奔走。野驴群惊慌地嘶鸣,跑到远远的地方观望。
“来,快来帮帮我!”强巴费劲地攥住绳头,朝我喊叫。
我放下摄像机,冲出灌木丛,飞奔过去。黑脖子母驴是在往下坡跑,速度很快,等我赶到强巴身边,已差不多是在缓坡的坡脚下了。我和强巴齐心协力,才算把它拽住,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它按翻在地。我抱住驴脖子,压在驴身上,强巴动手捆绑四只驴蹄。它躺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叫救命。
正忙乎呢,突然四面八方传来吭吭的驴叫,我抬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知什么时候野驴群已经团团将我们围住。一头身强力壮的白脸公驴,鸣叫着,跑前跑后,指挥驴群慢慢缩紧了包围圈。
也许,发情期的公驴胆子格外大,脾气也格外暴躁,它们见我们粗暴地捆绑黑脖子母驴,误将我们看作情敌,要与我们拼斗一场。
糟糕的是,强巴的猎枪和藏刀、我防身用的左轮手枪,全都放在坡顶那丛灌木里,离我们现在的位置至少有三四百米远。我们手无寸铁,草坡上连可以当作武器使用的石头也捡不到。
“啊——”强巴已将黑脖子母驴的四只蹄子捆扎结实,站起来挥舞双手,青蛙似的蹦跳,扯开喉咙大叫。我晓得,这是猎人惯用的伎俩,当不期然与野兽相遇,用这种最原始的示威方式,能将野兽吓退。但这一次,这一招不灵了。野驴们纷纷扬起前蹄,吭吭高叫;野驴的叫声本来就高亢响亮,因此享有叫驴的别名,群驴齐叫,气势磅礴,声音大得震耳欲聋,立刻把强巴的叫喊声压了下去。
白脸公驴闷着头朝我们冲过来,举起两只锤子似的前蹄,来敲我的脑袋,若让它得逞,我不是脑袋开花,就是重度脑震荡。强巴眼疾手快,一扔绊马索,月牙形的铅巴不偏不倚地砸在白脸公驴的嘴唇上,不知道是否敲掉了一颗门牙,它一转身子,放弃了对我的攻击,跑回驴群去了。
白脸公驴的攻击行为具有示范效应,其他几头公驴也都想演一出英雄救美的好戏,驴蹄咚咚咚咚像擂战鼓似的敲击地面,抖鬃甩尾,蠢蠢欲动。
我一看势头不对,忙说:“把黑脖子母驴放掉算了,别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