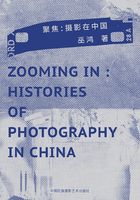
第一部分 以影像表现中国与自我
一 创造“中国式”肖像风格:以弥尔顿·米勒为例

有关弥尔顿·米勒职业生涯的资料不多。 根据能够找到的零散记录,他在中国从事摄影的时间不超过三年,所取得的成就却相当可观。在来华之前,他曾于1856年至1860年在罗伯特·万斯(Robert H. Vance,1825—1876)于旧金山开设的影楼里担任摄影师。
根据能够找到的零散记录,他在中国从事摄影的时间不超过三年,所取得的成就却相当可观。在来华之前,他曾于1856年至1860年在罗伯特·万斯(Robert H. Vance,1825—1876)于旧金山开设的影楼里担任摄影师。 万斯在1859年与另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摄影师兼企业家查尔斯·韦德(Charles Leander Weed,1824—1903)合作,韦德随即将他的影楼业务扩展到美国的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以至亚洲的远东地区。
万斯在1859年与另一位富有开拓精神的摄影师兼企业家查尔斯·韦德(Charles Leander Weed,1824—1903)合作,韦德随即将他的影楼业务扩展到美国的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以至亚洲的远东地区。 韦德在1859年移居香港,米勒也随行而来,在韦德开办的香港和广州的华德照相馆(Weed and Howard Photographic Gallery)担任“常驻摄影师”。
韦德在1859年移居香港,米勒也随行而来,在韦德开办的香港和广州的华德照相馆(Weed and Howard Photographic Gallery)担任“常驻摄影师”。 根据这家影楼在1860年刊登的一则广告,它“备有新近发明之大型阳光相机,可拍真人大小肖像,敬希贵客垂注”。
根据这家影楼在1860年刊登的一则广告,它“备有新近发明之大型阳光相机,可拍真人大小肖像,敬希贵客垂注”。 下一年韦德转往上海另寻商机,米勒于是承购了他在香港和广州两地的影楼,并改名为米勒摄影公司(Miller& Co., Photographers)。
下一年韦德转往上海另寻商机,米勒于是承购了他在香港和广州两地的影楼,并改名为米勒摄影公司(Miller& Co., Photographers)。 我们无法确定他在广州的分支经营了多久,但可以肯定时间不会很长:米勒在1861年8月称这间分馆只营业一个月,而且在此期间照相馆遭盗贼光顾,损失的财物包括“影楼中所有的物品”,包括一整箱底片。
我们无法确定他在广州的分支经营了多久,但可以肯定时间不会很长:米勒在1861年8月称这间分馆只营业一个月,而且在此期间照相馆遭盗贼光顾,损失的财物包括“影楼中所有的物品”,包括一整箱底片。 若干证据表明米勒主要以香港为基地,从那里前往澳门、广东等地承接摄影业务。比如1861年5月他曾乘船去日本长崎,在那里为美国出版商安东尼(E.& H. T. Anthony)拍摄了一系列立体照片。
若干证据表明米勒主要以香港为基地,从那里前往澳门、广东等地承接摄影业务。比如1861年5月他曾乘船去日本长崎,在那里为美国出版商安东尼(E.& H. T. Anthony)拍摄了一系列立体照片。 另一次则是受在广州医院任职的克尔医生(Dr. John Kerr)的聘请,给一名“身上和手臂上长了数百个肿瘤”的中国病人照了相片
另一次则是受在广州医院任职的克尔医生(Dr. John Kerr)的聘请,给一名“身上和手臂上长了数百个肿瘤”的中国病人照了相片 ——这是首次有案可查的中国医疗机构利用摄影进行医学研究的案例。他最后于1863年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佛蒙特州的家乡。回国以前他把香港的业务和所存底片全部卖给了店员豪尔希(S. W. Halsey)。
——这是首次有案可查的中国医疗机构利用摄影进行医学研究的案例。他最后于1863年离开中国,回到美国佛蒙特州的家乡。回国以前他把香港的业务和所存底片全部卖给了店员豪尔希(S. W. Halsey)。 返美后他改行投资地产,很少涉足摄影。在187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资料里,他的身份是“退休摄影师”。
返美后他改行投资地产,很少涉足摄影。在187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资料里,他的身份是“退休摄影师”。

图1.1 弥尔顿·米勒《“鞑靼”将军元配夫人》,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在19世纪中后期前往中国的西方摄影师中,米勒以擅长拍摄官员、商贾及妇女的肖像而闻名。对许多收藏家和摄影史学者而言,他的作品是珍贵的艺术和历史影像,不仅见证了摄影师本人的高超技术造诣,同时也揭示了相片中人物的个人性格,在有关中国的早期摄影作品中可说是相当罕见。 以他为一位老妇拍摄的照片为例(图1.1),她身穿清代品官夫人命服,包括精工刺绣的锦袍、背心与长裙,但其木无表情的面孔与盛装和花冠却形成了强烈对比——与其说是喜气洋洋或端庄肃静,不如说老妇脸上的皱纹显示的是她郁郁寡欢的一生。这幅肖像的视觉效果既微妙又直接。被摄者直对镜头,上方投下的光线集中在她的身体和脸上,将人像从朦胧的阴暗背景中凸现出来,在视觉效果上大大加强了人物的立体和真实。这种视觉上的直接感和对老妇的个性化表现,使观者直觉上将这张照片视为一幅“肖像”,
以他为一位老妇拍摄的照片为例(图1.1),她身穿清代品官夫人命服,包括精工刺绣的锦袍、背心与长裙,但其木无表情的面孔与盛装和花冠却形成了强烈对比——与其说是喜气洋洋或端庄肃静,不如说老妇脸上的皱纹显示的是她郁郁寡欢的一生。这幅肖像的视觉效果既微妙又直接。被摄者直对镜头,上方投下的光线集中在她的身体和脸上,将人像从朦胧的阴暗背景中凸现出来,在视觉效果上大大加强了人物的立体和真实。这种视觉上的直接感和对老妇的个性化表现,使观者直觉上将这张照片视为一幅“肖像”, 也说明米勒所拍摄的这类照片为什么会被认为是“19世纪最出色的中国正式人像”。
也说明米勒所拍摄的这类照片为什么会被认为是“19世纪最出色的中国正式人像”。
然而这名老妇究竟是谁?她真的像照片英文标题所说的那样是一位“鞑靼将军夫人”吗?这位鞑靼将军又是谁?这个朝廷贵妇为什么会身穿全套命服去米勒的影楼单独拍了这幅肖像?——这些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主要是因为照片的自然主义风格使人们马上相信这是为一个真实人物所拍的肖像。然而在2006年洛杉矶盖蒂研究所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 与会学者仔细观看这张照片和米勒的其他一些摄影作品之后,
与会学者仔细观看这张照片和米勒的其他一些摄影作品之后, 发现了其中有些蹊跷之处。一个费解的地方是,老妇穿戴的服饰在米勒其他作品中不断出现,由其他女性反复穿戴。这些“其他女性”中包括一位年轻女子,肖像上的英文标签将其称作一位广州官员的夫人。
发现了其中有些蹊跷之处。一个费解的地方是,老妇穿戴的服饰在米勒其他作品中不断出现,由其他女性反复穿戴。这些“其他女性”中包括一位年轻女子,肖像上的英文标签将其称作一位广州官员的夫人。
照片中的人是谁?
沿着在盖蒂研讨会中所发现的这个线索,我对米勒“中国肖像”中的主体人物、服饰、布景和道具进行了详细比较,尝试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通过这种比较,我发现了这些照片之间许多明白无误的关联:那位年轻女子既有单人照又有和她“丈夫”的合影;这位“丈夫”又与他自己的“母亲”及“弟弟”拍了合照;他的“母亲”不是别人,正是上面提及的“鞑靼将军夫人”;而这位老妇又与另一些妇女一起照了相。通过建立这种联系,我最后鉴别出十一张有着密切关系、享有共同因素的照片,其中身穿不同服饰的同样人物重复出现在不同的影像里。而且,虽然人物的组合不时调换,但是这些照片均在同一地点以同一风格拍摄。 至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这组具有相关对象和高度一致的摄影手法的照片应该是一项“拍摄计划”的成果,极有可能是米勒1861年在广州逗留时的作品,拍摄地点应该是米勒的广州影楼。
至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这组具有相关对象和高度一致的摄影手法的照片应该是一项“拍摄计划”的成果,极有可能是米勒1861年在广州逗留时的作品,拍摄地点应该是米勒的广州影楼。 在进一步考虑这批影像的意义之前,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更为仔细的视觉分析。
在进一步考虑这批影像的意义之前,我们需要对它们进行更为仔细的视觉分析。
在这组相片的摄影对象中,最上镜头和最常出现的人物是图1.2至图1.5中的年轻男子。图1.2中他身穿冬季补服,胸前方形补子上的飞禽图案是文官品级的标记。清朝官分九品,以补子上的图案标明。这张照片中补子上的鸟可能是白鹇,是五品补服的特征。图1.3是这名男子和他的“夫人”的合影,此处他换了一件纱质的夏季补服,上面补子中的鸟却跟前一张中的不一样,象征的是不同的品级。 此外,这个男子还出现在米勒的另外两张照片里,均身穿居家常服。其中一张是他和“夫人”及四名子女的合影(图1.4),另一张是与年老的“母亲”、“弟弟”和三名小孩在一起(图1.5)。但这三个孩子中只有两个是他的:按照传统习俗,坐在他“弟弟”身旁的男孩应该是他侄子。
此外,这个男子还出现在米勒的另外两张照片里,均身穿居家常服。其中一张是他和“夫人”及四名子女的合影(图1.4),另一张是与年老的“母亲”、“弟弟”和三名小孩在一起(图1.5)。但这三个孩子中只有两个是他的:按照传统习俗,坐在他“弟弟”身旁的男孩应该是他侄子。
他在图1.3中的“夫人”也见于其他照片(见图1.6、1.7及1.11)。在图1.3和图1.6中,她身穿全套命服,包括有补子的刺绣锦袍和匹配的长裙、镶嵌珠宝的花冠和串珠。刚才我们已经注意到,那位“鞑靼将军夫人”也穿着这套衣服照过相。同样难以理解的是:清代妇女只在盛大礼仪场合才会如此打扮,但这个年轻女子在图1.6中的慵懒坐姿,与她的服装所显示的社会地位及隐含的典礼场合实在是格格不入。相片中的她倚向一侧,一只手臂慵懒地搭在茶几上,长裙下露出三寸金莲。 图1.7显示了其他破绽:她身穿汉人的便服和长裙,但胸前却缀了品官的补子。补子配搭便服已经很不寻常,而这块补子又与上一张中的不同。对传统中国服饰有深入研究的李雨杭博士认为,这件衣服上的补子看来是随便加上去的,因为它直接缀在了从领口到对襟两边的刺绣镶边上,部分镶边被补子遮盖。
图1.7显示了其他破绽:她身穿汉人的便服和长裙,但胸前却缀了品官的补子。补子配搭便服已经很不寻常,而这块补子又与上一张中的不同。对传统中国服饰有深入研究的李雨杭博士认为,这件衣服上的补子看来是随便加上去的,因为它直接缀在了从领口到对襟两边的刺绣镶边上,部分镶边被补子遮盖。
那位年轻男子的两套官服,包括图1.2中的貂皮帽和貂皮领冬季补服和图1.3中的轻薄的夏服补服,都被穿在了图1.8和图1.9的一位中年男子身上。而在图1.9中,这名中年男子的“夫人”也再次穿起了那个年轻女子和老妇的服装(见图1.3及图1.6)。这对中年夫妇和那对年轻夫妇一样,也拍了身穿便装的照片(图1.10)。我们还看到图1.5中年轻男子的老母将便服换上命服,出现在本文起首处谈到的照片中,因此摇身一变成了“鞑靼将军夫人”(见图1.1)。仔细比较之下,我们发现她和图1.3、1.6及图1.9中的两名女子穿的完全是同一套服装和饰物,包括锦袍、裙、背心、花冠及串珠。我们也可以断定她的“鞑靼将军夫人”身份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在其他照片中她和子女们都穿着典型的汉人服装(图1.5)。在另一张照片里她又与几位年轻女子合影,扮演了一个家庭中三代女性同聚一堂的场面(图1.11)。
从地毯的菱形图案和素色背景来看,这十一张照片是在同一地点拍摄的,并使用了相同的道具,包括中、西式茶几各一架,两张一套的椅子和同一套盖碗茶杯。两张比较复杂的照片的拍摄进而加上了盆花、字画和座屏等道具,以营造更为浓厚的家居氛围(图1.3、1.4)。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细致地观察这些照片中人物的服装、饰物和官品补子呢?这是因为这些细节透露出的人物身份是我们发掘这批历史照片的“真实性”的第一步。任何历史解释都需要根据真凭实据,由于有关中国早期肖像摄影拍摄过程的信息少之又少, 证据的确立只能通过建立系统的影像资料库和对实际影像的内在属性进行细致分析来完成。这种初步的观察既是解构也是重建,它的作用一方面是把历史照片从未经证实的假设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为重新确立它们的真实历史意义做准备。
证据的确立只能通过建立系统的影像资料库和对实际影像的内在属性进行细致分析来完成。这种初步的观察既是解构也是重建,它的作用一方面是把历史照片从未经证实的假设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也为重新确立它们的真实历史意义做准备。

图1.2 弥尔顿·米勒《年轻中国人肖像》,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3 弥尔顿·米勒,《中国官员和夫人》,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4 弥尔顿·米勒,《中国家庭》, 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5 弥尔顿·米勒,《穿便服的官员与母亲、弟弟及子女合影》, 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6 弥尔顿·米勒,《中国妇人肖像》, 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7 弥尔顿·米勒,《中国妇人肖像》, 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就目前这十一张弥尔顿·米勒拍摄的肖像照来说,以往不断重复的相片中人的身份肯定不应该继续重复下去了。最先制造这些虚构身份的可能是米勒本人,而当这些照片开始在市场上流通,不断发行和复制的时候,新的身份和说明又不断添加进来,图1.2至图1.5中的年轻男子因此在不同出版物中被称作“广州官员”、“稗官”或“中国商人”。当图1.3、1.4、1.6及1.7中的年轻妇人身穿便服时,她被称为官员夫人或商家夫人,而穿着命服时则被称为“稗官夫人”或“广东总督元配夫人”。至于图1.1中的老妇,我们已经说到有些书籍介绍她为“鞑靼将军夫人”,但《摄影师和旅者眼中的中国》(The Face of China)一书的作者却认为她可能是“广东巡抚黄赞汤夫人”。到了《中国皇朝》封面上,她又成了“广东官员夫人”。泰瑞·贝内特在最近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则简单地称她为“官夫人”。 其实所有这类定名都缺乏确实的文献证据,单凭对照片本身的仔细观察就可以把这些身份一一驳倒。如上文所述,清廷官员不可能在同一时刻穿戴等级不同的官服,更难想象品官和夫人能够在洋人影楼里不断换装并以不同身份反复组合拍照。很明显,这些都是使用雇佣的模特所拍摄的“扮装照”,历史可信性令人怀疑。标签所赋予这些以自然主义风格拍摄的人物形象的,是其貌似可信的虚构身份。
其实所有这类定名都缺乏确实的文献证据,单凭对照片本身的仔细观察就可以把这些身份一一驳倒。如上文所述,清廷官员不可能在同一时刻穿戴等级不同的官服,更难想象品官和夫人能够在洋人影楼里不断换装并以不同身份反复组合拍照。很明显,这些都是使用雇佣的模特所拍摄的“扮装照”,历史可信性令人怀疑。标签所赋予这些以自然主义风格拍摄的人物形象的,是其貌似可信的虚构身份。

图1.8 弥尔顿·米勒,《中国官员肖像》,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9 弥尔顿·米勒,《身穿全套补服的官员与夫人》, 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10 弥尔顿·米勒,《中国家庭肖像》,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11 弥尔顿·米勒,《中国妇人肖像》,1860─1863年。蛋白照片。
照片反映的是谁的个性?
以上分析对这批被视为“19世纪最出色的中国正式人像” 的“肖像”性质提出了挑战,由此我们也需要对以往根据这种性质作出的历史叙事提出质疑。这个叙事的大体逻辑是:甚至早在1860年和1861年之前,许多家境富裕的中国人,包括一些清朝官员及其家眷,就已经非常喜欢拍摄,而且经常光顾西洋影楼。
的“肖像”性质提出了挑战,由此我们也需要对以往根据这种性质作出的历史叙事提出质疑。这个叙事的大体逻辑是:甚至早在1860年和1861年之前,许多家境富裕的中国人,包括一些清朝官员及其家眷,就已经非常喜欢拍摄,而且经常光顾西洋影楼。 使用这个历史叙事写作中国摄影史的一个例子是玛利·华纳·马利恩(Mary Warner Marien)的《摄影:一部文化史》,她以图1.3中的照片作为范例,写道:
使用这个历史叙事写作中国摄影史的一个例子是玛利·华纳·马利恩(Mary Warner Marien)的《摄影:一部文化史》,她以图1.3中的照片作为范例,写道:
西方发展起来的中产阶级肖像标准,被新的富有的中国顾客所采用。奢华的家具放在幕布围起来的封闭空间里,给身着精致衣物的人们和艺术摆设提供了背景。米勒的肖像通常拍摄的是中国的上层和中产阶级,以及在外贸商行工作的人。对象在照相时通常直接面对镜头。照片上的人物偶尔会露出些许表情,但是惯常的做法是在镜头和照相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马利恩在这里提到了米勒中国肖像照中的若干图像特征,包括奢华的家具、精致的衣物、艺术品摆设以及人物面部的凝重表情。由于这些照片的标签中从未透露被摄者姓名,我推测她之所以认为这些照片是中国“上层和中产阶级”人士的真实写照,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些特定的图像特征,以及照片的写实风格,特别是因为这种写实风格似乎抓住了被摄者的个人性格。确实,米勒制作的肖像照,不论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以中国传统视觉文化中罕见的自然主义风格触动观者。学者们也正因如此,把他和马修·布瑞迪(Mathew Brady,1822—1896)以及马库斯·奥理略·路特(Marcus Aurelius Root,1808—1888)进行了联系和比较。与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19世纪肖像摄影师一样,米勒的作品融合了精确的造型和戏剧化的视觉效果,通过细心控制的光线来表现人物的面部结构和衣服之下的身体。在这批照片的几张男子肖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捕捉对象细微的面部表情所做的努力(图1.2—1.4,1.8)。身处空空的摄影室内,这些人物的形象从略为模糊的单调背景中浮出,像是要和观者对话。
这种对自然主义风格既熟练又富于创造性的运用,使米勒跻身1850年代及1860年代的美国主流肖像摄影师之列。摄影史学者已经指出,这一时期美国人心目中的理想肖像照,是那些能够揭示人物内在性格的逼真影像,必须以“人物的外表为内在性格和真实本质的记号或表征”。 为了满足上层人士对“性格化”照片的执著,肖像摄影师的最大任务是“如何营造个性,如何表现个性,如何保存个性,而最关键的是如何鉴别出人物的个性”。
为了满足上层人士对“性格化”照片的执著,肖像摄影师的最大任务是“如何营造个性,如何表现个性,如何保存个性,而最关键的是如何鉴别出人物的个性”。 对人物个性的鉴别和表达不仅发挥了摄影的拟态功能,更重要的是促使摄影师展现自己的艺术理念和才华。一个摄影师如果能够成功地表现出照相人物的内在性格,他便超越了简单地以机械手法记录影像的普通摄影师水平,而变成一个思想敏锐的“艺术家”。正因如此,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于1855年说,一个艺术摄影师“必须发挥他的内在潜力,使他的天赋远远超出单纯的机械能力……超出仅仅复制自然的达盖尔照片,以达到真正艺术的高度”。
对人物个性的鉴别和表达不仅发挥了摄影的拟态功能,更重要的是促使摄影师展现自己的艺术理念和才华。一个摄影师如果能够成功地表现出照相人物的内在性格,他便超越了简单地以机械手法记录影像的普通摄影师水平,而变成一个思想敏锐的“艺术家”。正因如此,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于1855年说,一个艺术摄影师“必须发挥他的内在潜力,使他的天赋远远超出单纯的机械能力……超出仅仅复制自然的达盖尔照片,以达到真正艺术的高度”。
有关米勒摄影事业的最早资料显示,1856年他在罗伯特·万斯的影楼任职,这座影楼位于旧金山市蒙特哥马利街与萨克拉门托街交角处。 万斯在1850年代号称美国“西海岸摄影界的潮流先锋和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斯在1850年代号称美国“西海岸摄影界的潮流先锋和举足轻重的人物”。 米勒的在场和万斯在同一年开办这家影楼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广告宣传,似乎并非巧合。以下是万斯在《旧金山商业宣传报》(San Francisco Advertiser)上刊登的广告,高调宣扬其影楼的高超技术和无出其右的艺术品位及风格时尚:
米勒的在场和万斯在同一年开办这家影楼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广告宣传,似乎并非巧合。以下是万斯在《旧金山商业宣传报》(San Francisco Advertiser)上刊登的广告,高调宣扬其影楼的高超技术和无出其右的艺术品位及风格时尚:
每一张底版事先都被仔细涂上一层纯银,用它们拍摄出来的图像清晰醒目和持久,备受赞誉,这是使用一般底版的艺术家无法仿效的……他[万斯]在经过诸多试验之后,将生产化学制剂的设备臻于完美,制造出写真界从未使用过的合成物,这保证了他在每次摄影中都能制作出完美逼真以及清晰、柔和、美丽的色调,使其所有作品备受仰慕。
1857年刊登的另一则广告强调影楼得到“州内另一位杰出摄影艺术家”的加盟效力,“旨在完美掌握最新摄影技术,并在影楼推出相关服务”。 不论万斯所指的“杰出摄影艺术家”是否为米勒,这两则广告都道出了米勒远来东方之前的工作环境和野心。为满足万斯的要求进而在竞争激烈的商业摄影市场中生存,米勒必须精研摄影技术与技巧,顺应当时美国人对肖像摄影理想的要求,并参与建立有关这种理想的标准,以此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非一名庸碌的匠人。
不论万斯所指的“杰出摄影艺术家”是否为米勒,这两则广告都道出了米勒远来东方之前的工作环境和野心。为满足万斯的要求进而在竞争激烈的商业摄影市场中生存,米勒必须精研摄影技术与技巧,顺应当时美国人对肖像摄影理想的要求,并参与建立有关这种理想的标准,以此证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而非一名庸碌的匠人。
在这个历史情境中去理解,米勒所拍的中国肖像的高度“个性化”所显示的,实际上是米勒本人发掘拍摄对象的个性、表现对象个性的能力和艺术才华,而非对象本人性格的自然呈现——特别当这些对象不过是些受雇的模特。我们也需要考虑到,虽然米勒此时来到香港工作,购买他照片的顾客实际上都是西方人而非本地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这组照片拍的是各具外貌特征和特定性格的中国人,米勒却从来没有记下他们的姓名,只是用英文标上一些一般性的标签。此外,在一次见诸文字的法律案件中,他对本地苦力之漠不关心甚至歧视虐待的表现,也令人怀疑他是否会在意雇佣模特的性格和心理。
通过把“个性”赋予籍籍无名的本地人,这些照片反映了新型的肖像摄影和老派的“中国类型和职业”(Chinese types and professions)图像的奇怪结合。我们可以将这个老式视觉传统追溯到尼奥霍夫(Johannes Nieuhof)在17世纪编著的《使节出访:从省会联邦东印度公司到觐见中国皇帝鞑靼汗》。 稍晚的一批代表作是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画的一批水彩画和版画,是他于1792年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以后创作的。
稍晚的一批代表作是英国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画的一批水彩画和版画,是他于1792年随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以后创作的。 在这些画作中,亚历山大记录了遥远的中国城市、风景和充满异国风情的建筑,以及从事不同行业、服饰有别的男女人物。这些图像在19世纪早期的西方受到了广泛欢迎,在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及美国都曾被复制出售。跟随着尼奥霍夫和亚历山大的脚步,1840年代以后来到中国的欧美摄影师开始创作自己的中国形象,利用新的视像技术和当时的艺术品味为国际观者重塑中国人的形象。亚历山大《中国服饰》一书中木偶般的人物在这些摄影师手中变成了有血有肉的“肖像”,但是他们依然无名无姓。我在下文中将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变体现的并不是一个民族的自我认识,而是西方科学与艺术在全球的扩张。这一扩张使来自西方的观察者不仅可以记录当地的服饰和风俗,还可以将本土人民塑造成“个性化”的人物,以此显示出他们自身的现代情结。
在这些画作中,亚历山大记录了遥远的中国城市、风景和充满异国风情的建筑,以及从事不同行业、服饰有别的男女人物。这些图像在19世纪早期的西方受到了广泛欢迎,在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及美国都曾被复制出售。跟随着尼奥霍夫和亚历山大的脚步,1840年代以后来到中国的欧美摄影师开始创作自己的中国形象,利用新的视像技术和当时的艺术品味为国际观者重塑中国人的形象。亚历山大《中国服饰》一书中木偶般的人物在这些摄影师手中变成了有血有肉的“肖像”,但是他们依然无名无姓。我在下文中将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变体现的并不是一个民族的自我认识,而是西方科学与艺术在全球的扩张。这一扩张使来自西方的观察者不仅可以记录当地的服饰和风俗,还可以将本土人民塑造成“个性化”的人物,以此显示出他们自身的现代情结。
再造中国肖像风格
米勒于1860年到达香港时,那里已经有多家西方和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后者包括创建于咸丰年间(1851—1861)的宜昌画楼,以及赖阿芳于1859年创办的摄影社。 1860年代末到1870年代初,著名英国摄影师汤姆逊来到中国游历,他注意到香港的维多利亚皇后大道旁有多个“华人摄影师”经营的影楼。
1860年代末到1870年代初,著名英国摄影师汤姆逊来到中国游历,他注意到香港的维多利亚皇后大道旁有多个“华人摄影师”经营的影楼。 正如郭杰伟(Jeffrey W. 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和黎健强(Edwin K. Lai)在研究文章中谈到的,商业影楼的兴起和涌现是中国摄影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中外摄影师开设的影楼在中国沿海的主要商埠共存,彼此竞争激烈。郭杰伟和范德珍还引用清末维新派人物王韬对上海影楼的评价,认为上海中国影楼出产的作品优于西人。
正如郭杰伟(Jeffrey W. 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和黎健强(Edwin K. Lai)在研究文章中谈到的,商业影楼的兴起和涌现是中国摄影史中的一个重要篇章。中外摄影师开设的影楼在中国沿海的主要商埠共存,彼此竞争激烈。郭杰伟和范德珍还引用清末维新派人物王韬对上海影楼的评价,认为上海中国影楼出产的作品优于西人。 但意味深长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媒体也开始不断嘲笑中国人对照相的“特殊要求”。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中国本地人在拍摄肖像时必定要拍正面像,坐姿端正,双耳露出,眼睛直视镜头,似是与相机对峙。他们的身旁必须放上一个小茶几,几上摆设假花。他们的脸上不可以有阴影,照相时必定要穿最好的衣服,手持扇子或鼻烟壶等心爱物品,而他们的长指甲也必须在炫耀之列。
但意味深长的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媒体也开始不断嘲笑中国人对照相的“特殊要求”。根据这些媒体的报道,中国本地人在拍摄肖像时必定要拍正面像,坐姿端正,双耳露出,眼睛直视镜头,似是与相机对峙。他们的身旁必须放上一个小茶几,几上摆设假花。他们的脸上不可以有阴影,照相时必定要穿最好的衣服,手持扇子或鼻烟壶等心爱物品,而他们的长指甲也必须在炫耀之列。 汤姆逊在一份题为《香港摄影师》的专题报道中确认了这些西方人眼中的古怪当地习惯。但与其他类似报道不同的是,这篇登载在著名的《英国摄影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上的文章通过一名称作“阿雄”的当地摄影师之口对这些习惯进行了陈述,因此在中国摄影师的专业眼光和中国顾客的无知偏好之间画上了等号。
汤姆逊在一份题为《香港摄影师》的专题报道中确认了这些西方人眼中的古怪当地习惯。但与其他类似报道不同的是,这篇登载在著名的《英国摄影期刊》(British Journal of Photography)上的文章通过一名称作“阿雄”的当地摄影师之口对这些习惯进行了陈述,因此在中国摄影师的专业眼光和中国顾客的无知偏好之间画上了等号。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汤姆逊还为文章加了一幅漫画(图1.12)。伍美华(Roberta Wue)对其做了以下评述:“被拍者坐姿僵硬,双目直视前方,四平八稳的对称姿势极不自然,有如一只青蛙,乏味的家具和道具陈设得一板一眼。汤姆逊的这幅漫画的目的是图解和嘲讽,批评中国肖像摄影中人为的、缺乏深度的死板造型。”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汤姆逊还为文章加了一幅漫画(图1.12)。伍美华(Roberta Wue)对其做了以下评述:“被拍者坐姿僵硬,双目直视前方,四平八稳的对称姿势极不自然,有如一只青蛙,乏味的家具和道具陈设得一板一眼。汤姆逊的这幅漫画的目的是图解和嘲讽,批评中国肖像摄影中人为的、缺乏深度的死板造型。”

图1.12 约翰·汤姆逊《香港摄影师》,载于《英国摄影期刊》第656期(1872年11月29日)。
这类明显反映西方优越感的报道却在读者眼里成了事实。使这类写作格外有说服力的一个原因在于它们采用了“对称性话语”(discursive symmetry)的逻辑:它们所描绘的“东方肖像摄影”处处与“西方肖像摄影”相对,因此确认了西方人思想里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东西文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事实上,这些报道的注视点,包括人物姿势的安排、四肢的摆放、目光的方向、光线的来源以及背景和道具——都是当时西方肖像摄影中的基本规则所在。 一本于1854年出版的美国摄影指南中这样写道:“照相人的坐姿应该舒适自然,手脚不要伸得太远,身体不要过于后靠。眼睛不应直视镜头,而是应该稍为偏倚,凝望旁边的一件物品。千万不要盯着照相机上方,否则照出来的面容便会现出悲伤或不悦的表情。”
一本于1854年出版的美国摄影指南中这样写道:“照相人的坐姿应该舒适自然,手脚不要伸得太远,身体不要过于后靠。眼睛不应直视镜头,而是应该稍为偏倚,凝望旁边的一件物品。千万不要盯着照相机上方,否则照出来的面容便会现出悲伤或不悦的表情。” 有意思的是,这类指南既提出了一套“合理”的肖像表现方法,又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感知结构以确定任何“异己”的摄影习俗。因此,甚至在到达中国以前,西方摄影家已经把自己放在预想的中国习俗的对立面,并由此将这种习俗定义和建构为他者的怪异行为。
有意思的是,这类指南既提出了一套“合理”的肖像表现方法,又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感知结构以确定任何“异己”的摄影习俗。因此,甚至在到达中国以前,西方摄影家已经把自己放在预想的中国习俗的对立面,并由此将这种习俗定义和建构为他者的怪异行为。
作为罕见的有关早期中国摄影的文字资料,汤姆逊的报道和其他来华西方人士从“现场”提供的消息,引起了学者对界定“中国式”摄影肖像风格的浓厚兴趣。 然而,在仔细查看了数百张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肖像照片之后,摄影史家狄瑞景(Régine Thiriez)认为,中、西影楼拍摄的影像基本上没有很大分别。在背景的制作和人物姿势的安排上,中国影楼大都采用了西方规范;同样,一些西方摄影师的作品也相当符合上述报道中所讥讽的“中国习惯”。
然而,在仔细查看了数百张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肖像照片之后,摄影史家狄瑞景(Régine Thiriez)认为,中、西影楼拍摄的影像基本上没有很大分别。在背景的制作和人物姿势的安排上,中国影楼大都采用了西方规范;同样,一些西方摄影师的作品也相当符合上述报道中所讥讽的“中国习惯”。 郭杰伟、范德珍和胡素馨的观点与狄瑞景的结论一致,而我对中国和海外摄影档案的研究也有相同的发现。
郭杰伟、范德珍和胡素馨的观点与狄瑞景的结论一致,而我对中国和海外摄影档案的研究也有相同的发现。 这些实证研究显示东西方早期肖像摄影之间并不存在当时西方观察者一再坚持的文化鸿沟,存在的实际上是实践和话语之间的断裂。
这些实证研究显示东西方早期肖像摄影之间并不存在当时西方观察者一再坚持的文化鸿沟,存在的实际上是实践和话语之间的断裂。
这个断裂引导我们去反思西方关于中国肖像摄影报道的实质和影楼作业的复杂性。换言之,我们所研究和讨论的话题将不再围绕中、西影楼之间在摄影风格上的区别,或中国人是否对肖像摄影有特殊要求。毫无疑问,传统中国有着独特的肖像画传统,这种传统很自然地会影响19世纪的人对摄影的态度。我希望讨论的是发生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的一个特殊现象,即对一种 “独特中国肖像风格”的自觉塑造。据我所知,当时的中国作家或摄影师没有人撰文谈过这种风格和有关的摄影实践,我们只能看到西方观察家的报道和评论(包括引述“当地人士”的看法),其前提均为中国肖像与欧美肖像之间的区别。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中西之间的视角是非对称的。中文写作对于“肖像摄影”文化特殊性的失语,显示出“比较”观念在中国作者及摄影师的思考中的缺失,而西方有关“中国肖像风格”的强调则全然奠基在一种根深蒂固的“比较”观点之上。这种观点被米勒的摄影实践所内化。分析他的作品,我们看到不少按照当时的西方标准为洋人和一些中国人拍照的肖像。但除此之外,他也开始着意对“独特中国肖像风格”进行建构。
这一研究方向把我们带回到前述的11张照片。但是我们的着重点不再是照片中人物的服装、饰物和官阶标记,而是他们的姿势、动作、道具及人物组合。换言之,我们的注意力从人物的身份转移到照片本身的表达模式。这11张照片中有五张为单人肖像,其余为多人合影。下文的讨论将集中在这五张单人肖像上。
在这五张中,有四张沿用了一个标准构图:照片中的男子或女子均处于构图中心,坐姿端正,面朝前方,双眼直视相机镜头(图1.1、1.2、1.7、1.8)。这些静态的影像拒绝显露任何肢体活动,如同凝固在静止的时间之中。本来就很僵硬的姿势进而被方方正正的椅子和身边的茶几固定得更为刻板生硬。纵深方向的空间性被减到最低。即使人的面部和着装显示出一些立体感,照片也整体被布置在水平展开的二维平面上。我们不难识别出这一构图的渊源:如果说米勒对人物脸孔和身体的处理手法来自西方流行的写实风格,那么他的构图则是模仿了中国传统的祖先像。将一幅同时代的祖先像(图1.13)放在这四张照片旁边,我们会发觉两者之间的甚多相似之处,包括同样的正面端坐的姿势、同样的直视的目光、同样的空无一物的背景、同样的压缩空间、同样的被强化了的二维画面,以及同样的静止和凝固的感觉。 以下的证据进一步证明,米勒在拍摄这些肖像时必定是有意模仿了19世纪中国视觉文化中仍旧流行的这类祖先像。
以下的证据进一步证明,米勒在拍摄这些肖像时必定是有意模仿了19世纪中国视觉文化中仍旧流行的这类祖先像。

图1.1 弥尔顿·米勒《鞑靼将军元配夫人》,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2 弥尔顿·米勒《年轻中国人肖像》,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7 弥尔顿·米勒,《中国妇人肖像》,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8 弥尔顿·米勒,《中国官员肖像》,1860─1863年。蛋白照片。
首先,与传统祖先像相同,这几幅照片中的人物都是身穿官服的全身肖像(就连图1.7中年轻女子的胸前也缀有官品补子)。其二,米勒的照片显示出几项常见于祖先像中的细节,包括单手轻触胸前悬挂的串珠、对称的摆成八字形的双脚以及脚下放置的木制脚踏。其三,图1.2及图1.8中的男子像几乎占满了整个画框,这种“顶天立地”的构图在人像摄影中相当少见,但却是传统祖先像的一个常见特点。其四,与米勒的肖像照同时或稍后,中国祖先像也成为一种国际商品,被画工复制销往外国。 其五,丽昌等位于香港的早期华人照相馆产品均采用当时流行的西方肖像风格,完全没有传统祖先像的意味(图1.14)。
其五,丽昌等位于香港的早期华人照相馆产品均采用当时流行的西方肖像风格,完全没有传统祖先像的意味(图1.14)。 最后,把这四张照片与米勒的其他肖像作品相比较,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他刻意营造典型中国肖像风格的意图。
最后,把这四张照片与米勒的其他肖像作品相比较,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他刻意营造典型中国肖像风格的意图。
米勒所拍的这些“其他肖像照”包括中西人士,他们的身份常有明确的说明和记录。图1.15所示是某位雪佛尚先生(J. H. Chevechon)。他坐姿悠闲,手持帽子,身后的扶栏和立柱构成了界框他身体的纵深建筑空间。图1.16拍摄的是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将军。他穿着长马靴的腿几乎伸到相框之外,那近乎完美的侧面与中国祖先像正襟危坐的正面造型形成了鲜明对比。坐在图1.17中心的人是身穿便服的清朝广州提督,与儿子和下属在家中花园合影。这几个例子反映出米勒肖像摄影作品的多种构图方式,根据不同的人物或目的选用不同类型的构图,并安排相应的布景、姿势和空间。这种灵活性也在我们所研究的单人照片中的第五张中反映出来(图1.6)。这张照片中的年轻女子侧身下视,其构图与四张正面肖像(包括同一女子的一张便服照)明显有别。在拍摄这张照片时,米勒放弃了正面取景模式,镜头从斜角拍摄,女子的身体连同椅子和茶几形成一个三维立体空间。为什么他在拍摄这幅照片的时候放弃了祖先像的模式?一个可能的答案是:非对称的构图可以使所拍的妇人看起来更加娇柔袅娜,更完善地达到表现一个“中国美人”的目的。米勒以类似的构图为这位年轻女性拍摄了不止一张照片。比较现存的两个版本(图1.6,1.18),我们可以发现摄影师对她的身体和面孔的方向做了略微的调节,看来是希望找到最佳的拍摄角度来完美地捕捉这个中国女性的妩媚身姿。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米勒还给同一个女子拍了一套立体照片(图1.19)。这种照片一般是为更大市场和流通制作的,也进一步证明了他这整个摄影计划所具有的商业目的。

图1.13 佚名《扎拉丰阿像》, 19世纪下半叶,绢本着色。华盛顿市史密森学会赛克勒美术馆藏。

图1.14 丽昌(Lai Chong), 《僧格林沁将军》,达盖尔银版照片,1853年。

图1.15 弥尔顿·米勒,《雪佛尚像》,摄于香港,约1860年。蛋白照片。

图1.16 弥尔顿·米勒,《约翰·米切尔爵士像》,摄于香港,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17 弥尔顿·米勒,《蒙古将军与儿子及侍从》,摄于广州,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6 弥尔顿·米勒《中国妇人肖像》, 1860─1863年。蛋白照片。

图1.18 弥尔顿·米勒《中国妇人肖像》, 1860─1863年,蛋白照片。盖蒂研究所藏。

图1.19 弥尔顿·米勒《中国妇人肖像》,1860─1863年,立体照片。泰瑞·贝内特提供。
通过模仿祖先像的正面图式,米勒的四张正面肖像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创造出一个本质化的和具有永恒性的中国肖像风格。我们不应忘记这些照片预设的顾客是居住在中国或前来旅游的西方人。他们之所以有兴趣购买中国和中国人的照片,主要因为这些图像所显示的异国风情,用视觉形象见证了异域的文化和思想。为了最好地满足这种需求,米勒雇用了中国模特,让他们穿戴上指定的服装和饰物,做出指定的动作或姿势,并摆出指定的人物组合。但同时他也希望向预想的主顾证明,摄影师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具有超出以往“东方图画”插图的造诣和趣味。他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以当时流行的西方摄影风格,使用高度的写实风格表现出对象的性格和个性。这两个不同的期望混杂在一起,所生成的图像既不反映真实的中国,也不属于真正的西方,而是混合了本地的视觉传统,西方人的期望以及摄影师的野心。在下一节中我将谈到,这种风格在米勒之后被提炼得愈来愈明确和“程式化”。但即使是在1861年,米勒这四幅肖像照片的核心特点——以中国传统祖先像的模式表现生活中的中国人物——也已经将这些形象与其他类型的肖像照片有意识地区别开来,将自身定位为从内容到形式都正宗地道的“中国式影像”。
作为“程式”的中国肖像风格
米勒并没有“创造”这种肖像风格——他所做的是将本土的传统视觉文化进行演绎和挪用,以此制造出一种典型的“当地影像”以供应全球市场。和当时许多在华工作的西方摄影师一样,米勒在自视优越的同时也会被他作品的主题——中国——所吸引。同时他在香港的商业艺术实践与当地政府的殖民政策和经济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植根于殖民结构之中,米勒的作品很容易得到各种各样带有优越感的西方顾客的认同;他的“中国肖像风格”不但被创造它的殖民地文化自然认可,而且成了本土影楼仿效的楷模。
但是在香港这样的地方,什么算是本土影楼呢?我们不应该忘记,不加批判地使用“本土”一词,本身就已经接受了殖民者的立意和术语。实际上,香港市中心有多家由中外人士经营的商业影楼,二者的营业场地和作业方式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黎健强指出,许多早期中国摄影师都是商业画师出身,专门绘制西式图画向外国游客和居民出售。 这些影楼基本上都坐落在主要的殖民通商口岸,它们的业务被殖民者的管理系统、商业运作和视觉文化深深地影响乃至控制。大部分影楼从西方同行那里学得摄影技术,他们登载的广告也不断强调与西方摄影界的这层关系,以示其产品的正宗和优良。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中国影楼自然愿意认同由殖民者构建的“地道的”中国肖像风格,甚至将其标榜为自创的风格。而且,由于这种风格确实是部分来源于本土题材,它再次逆转成为本土文化的过程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在这个逆转过程中,新的“中国元素”被融合和接纳:新道具和时髦服装不断出现,而太过明显的西方诉求被进一步隐藏和淡化。这个调整的过程——即对已被挪用的本土视觉文化的再挪用——最后完全掩盖了殖民者塑造这一本地风格的初衷,将西方的执迷彻底演变成中国人的自我想象。
这些影楼基本上都坐落在主要的殖民通商口岸,它们的业务被殖民者的管理系统、商业运作和视觉文化深深地影响乃至控制。大部分影楼从西方同行那里学得摄影技术,他们登载的广告也不断强调与西方摄影界的这层关系,以示其产品的正宗和优良。在这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中国影楼自然愿意认同由殖民者构建的“地道的”中国肖像风格,甚至将其标榜为自创的风格。而且,由于这种风格确实是部分来源于本土题材,它再次逆转成为本土文化的过程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在这个逆转过程中,新的“中国元素”被融合和接纳:新道具和时髦服装不断出现,而太过明显的西方诉求被进一步隐藏和淡化。这个调整的过程——即对已被挪用的本土视觉文化的再挪用——最后完全掩盖了殖民者塑造这一本地风格的初衷,将西方的执迷彻底演变成中国人的自我想象。
到了1872年汤姆逊在《英国摄影期刊》撰写有关“中国摄影”报道的时候,这一肖像风格的演变或“回收”过程已大致完成。因此在这份报道中,虚构的香港摄影师“阿雄”可以对“中国肖像风格”高谈阔论。另一名英国摄影师格里菲斯(D. K. Griffith)也信心十足地宣称这种风格是顺应中国顾客的要求而产生的。![格里菲斯(D. K. Griffith)于1875年5月28日在《伦敦摄影新闻》(London Photographic News)第260页上发表《天朝摄影楼》一文,其中写道:“[中国人]在照相前总是要做充分准备。照相人的最好服装由苦力送来,他们一边商量一边小心翼翼地把衣服穿在身上,然后坐下来,将锦袍尽量铺展,一手拿着鼻烟壶,另一只手拿着扇子。肖像必须为正面照,要清晰地看到双耳、两边脸庞必须一样大小。双脚要整齐排好,长度一样,中国人根本不理解角度。他们双手总有一两只花巧的长指甲,也都喜欢在肖像中展示。假如可能的话他们都想摆些花,例如在桌上摆个小花瓶,或者,假如主角有一台心爱的法兰西时钟,他也会放在身旁。”引自伍美华《道地中国人》,第265页。](https://epubservercos.yuewen.com/42D423/10086363703832401/epubprivate/OEBPS/Images/note.png?sign=1745039670-fmeZBq4rJ9pfeI5YH7twoFIBmvvRqI4Y-0-20eba3ef8d0d76cc05a819d60c9d6463) 在1870年代出现的这些斩钉截铁、不证自明的写作显示出,“中国肖像风格”不但在视觉上,同时也在话语中被进一步确立。第二个阶段的演变和完成依据的是三种操作:一是典型中国肖像形式的完全固定化,
在1870年代出现的这些斩钉截铁、不证自明的写作显示出,“中国肖像风格”不但在视觉上,同时也在话语中被进一步确立。第二个阶段的演变和完成依据的是三种操作:一是典型中国肖像形式的完全固定化, 二是西方参与塑造这种风格的作用被隐蔽得更深,
二是西方参与塑造这种风格的作用被隐蔽得更深, 三是把这种地方肖像风格与高等“艺术”进行强制分离。汤姆逊报道中的一段文字和所配的附图(图1.12)提供了综合运用这三种操作的一个典型例证:
三是把这种地方肖像风格与高等“艺术”进行强制分离。汤姆逊报道中的一段文字和所配的附图(图1.12)提供了综合运用这三种操作的一个典型例证:
他们[即中国肖像]都采用同一姿势,被摄者坐在方方正正的茶几旁边,这种茶几像是用方块小心搭成的框架,方块一个叠一个,活像演讲厅用来讲解几何原理的装置。几上放个花瓶,盛着假花──那是模仿自然花卉的俗艳制品。背景是素色布帐,垂着的两幅布帘形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空间。主人公就身处其中,姿态犹如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习题。
在这个描述中,中国肖像风格意味着由无限重复所造成的一成不变和墨守成规。 属于这种风格的作品拒绝柔和的曲线、自然的动作和浪漫的氛围,它们所显示的是由缺乏感觉的冰冷元素所构成的对称几何形状。这种风格不但被视为当地人心理素质的自然反映,也被形容成为纯粹的中国产物。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无法找到米勒中国肖像中文化和艺术风格的杂糅痕迹。有意思的是,米勒和其他西方摄影师对建立这种风格做出的贡献也被有意地抹杀。汤姆逊特别提出中国肖像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放在人物身旁古怪的“绝对方正的茶几”,认为这是中国肖像摄影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是这种茶几实际上是米勒影楼里的常备装置,在本文所讨论的十一张照片中,有七张都出现了(图1.1、1.2、1.6-1.9、1.11)。最后,按照汤姆逊的审美判断,如此执著不变的程式化影像不能视为艺术品。他之所以使用一张漫画来图释他的观察——其中特别明确地绘上茶几上的“俗艳”假花——目的就在于强调这种摄影的“非艺术性”,甚至不应该用摄影图像来表现。霍米·巴巴(Homi Bhabha)对“程式化”(stereotyping)做了这样的阐述:“(程式化)是一种知识和认同的形式,它摇摆于永远‘在场’、已为人知以及总是需要被紧张重复的东西之间。”
属于这种风格的作品拒绝柔和的曲线、自然的动作和浪漫的氛围,它们所显示的是由缺乏感觉的冰冷元素所构成的对称几何形状。这种风格不但被视为当地人心理素质的自然反映,也被形容成为纯粹的中国产物。到了这一步,我们已经无法找到米勒中国肖像中文化和艺术风格的杂糅痕迹。有意思的是,米勒和其他西方摄影师对建立这种风格做出的贡献也被有意地抹杀。汤姆逊特别提出中国肖像中的一个特点,就是放在人物身旁古怪的“绝对方正的茶几”,认为这是中国肖像摄影的一个典型特征。但是这种茶几实际上是米勒影楼里的常备装置,在本文所讨论的十一张照片中,有七张都出现了(图1.1、1.2、1.6-1.9、1.11)。最后,按照汤姆逊的审美判断,如此执著不变的程式化影像不能视为艺术品。他之所以使用一张漫画来图释他的观察——其中特别明确地绘上茶几上的“俗艳”假花——目的就在于强调这种摄影的“非艺术性”,甚至不应该用摄影图像来表现。霍米·巴巴(Homi Bhabha)对“程式化”(stereotyping)做了这样的阐述:“(程式化)是一种知识和认同的形式,它摇摆于永远‘在场’、已为人知以及总是需要被紧张重复的东西之间。” 通过将中国式肖像照片转化为粗俗的漫画,汤姆逊完全抹杀了它们作为摄影作品的物质性和历史时间性。但是这幅漫画也说明他不愿意面对真实照片的紧张感——包括米勒二十多年前所拍的“中国肖像”。
通过将中国式肖像照片转化为粗俗的漫画,汤姆逊完全抹杀了它们作为摄影作品的物质性和历史时间性。但是这幅漫画也说明他不愿意面对真实照片的紧张感——包括米勒二十多年前所拍的“中国肖像”。
最后,中国肖像风格的程式化和话语化,为中西文化对话和自我想象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1885年,香港摄影师华芳为一名外国男子拍摄了一幅“中国式”肖像(图1.20)。为此他不但让这位顾客穿上中式服装,在他手里放了一支水烟袋,还让这个外国人正襟端坐,直视镜头。顾客周围的道具,包括一张方形茶几和几上的一瓶假花,都严格地按照汤姆逊所讽刺的样式设计(比较图1.12及图1.20)。与24年前米勒拍摄的第一代中国肖像遥相呼应,它的目的已不再是创造摄影中的当地风格,而仅仅是通过摄影消费这种风格。

图1.20 华芳《穿华服的洋人》,摄于香港,约1885年。蛋白照片。澳大利亚国家美术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