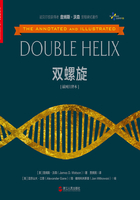
初版前言
在本书中,我将从自己的角度介绍发现DNA结构的整个过程。在叙述这一过程的时候,我将尽我所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学术界的整体气氛渲染出来,因为与发现DNA结构相关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那里。我希望本书能够向读者说明,科学极少会像旁观者想象的那样,以合乎逻辑的方式一直向前发展。恰恰相反,科学的进步(有时则是倒退)往往体现为一系列的人为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当事人本身以及文化传统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这本书中,我将致力于再现我当时对有关事件和人物的最初印象,而不是在通盘考虑DNA结构发现以后,在了解其他信息的基础上,再做出的某种评价。虽然后者可能更加客观,但这种方法无法真实地向读者传递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在于,一方面自信满满,另一方面又坚信真理(只要真的被发现了)必定是简洁和美妙的。因此,本书中的许多评论似乎都比较片面,有些甚至是不公正的;但在决定自己喜欢(或不喜欢)某个新观点或某种新生事物时,我们人类确实经常会在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就匆忙得出结论,这其实是真实人性的反映。无论如何,这本书反映了我在那个时期(1951—1953)对事物的观察:关于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关于其他当事人,也关于我自己。
当然,我非常清楚,这本书中涉及的其他当事人很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讲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这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有人的记忆绝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对于同一件事情,任何两个人的看法都不会完全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出一部天衣无缝的DNA结构发现史的任务,没有人能够完成。我觉得有必要讲述一下这个故事的部分原因还在于,许多科学界朋友对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过程非常好奇,对他们来说,即使本书叙述的内容挂一漏万,也必定聊胜于无。更重要的是,我发现普通公众对于怎样“从事”科学研究这一点仍然十分陌生。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切科学研究都是按本书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事实也远非如此。科学研究的类型、风格和方法极其繁杂多变。在这个由争强斗胜之志和公平竞争之心共同拉动,并因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而变得复杂起来的科学世界里,DNA结构的发现绝不是一个例外。
早在发现双螺旋结构的那一刻,我就开始酝酿着要写这本书了。我对与这项工作有关的许多重要事件的记忆,比我在其他人生阶段对事情的记忆要完整得多。在开展研究的过程中,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给父母写一封信,我在写作本书时充分利用了这些信件,它们对我确定许多事件的确切日期有着莫大的帮助。同样重要的是,许多朋友都提出了宝贵意见,他们读了初稿,有的还为我对事件的叙述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补充。毫无疑问,在某些情况下,我和其他人的回忆肯定会有出入,因此,本书只能看作是我对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这个事件的个人看法。
本书的前几章是在阿尔伯特・森特-哲尔吉(Albert Szent-Györgyi)、约翰・A.惠勒(John A.Wheeler)和约翰・凯恩斯(John Cairns)的家中写成的。我要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静的房间,房间里面还有正对着大海的书桌。后几章内容的完成则要感谢古根汉姆基金会(Guggenheim Fellowship),它授予了我学者奖,使我有机会在短期内重返剑桥大学,并受到了伦敦国王学院教务长和教务委员会成员的热情款待。
在本书中,我还尽可能多地收入了当年在事件发生时拍摄的一些照片。为此,我要特别感谢赫伯特・古特弗罗因德(Herbert Gutfreund)、鲍林、休・赫胥黎(Hugh Huxley)和冈瑟・斯腾特(Gunther Stent),他们赠寄给了我很多照片。在本书的编审过程中,我也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莉比・奥尔德里奇(Libby Aldrich)提出了一些深刻的意见——这些建议,正是我期待从这位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高才生这里得到的。乔伊斯・莱博维茨(Joyce Lebowitz)在语言文字上为我把了关,使我不致于误用英语中的修辞,还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让我明白了一本好书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此,我向他们深表感谢。最后,我还要向托马斯・威尔逊(Thomas J.Wilson)致以谢意,从本书的第一稿起,他就给了我莫大的帮助。要是没有得到他智慧、热情的指点,这本书不可能以现在这个样子呈现在大家面前,而这是我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样子!
詹姆斯·沃森
写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