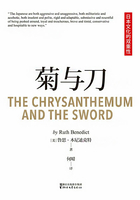
第10章 明治维新(1)
开启了近代日本历史的宣传口号是“尊王攘夷”,即“王政复古,驱逐夷狄”。这个口号试图使日本免受外部世界的负面影响,重回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以前的10世纪黄金时代。当时天皇在京都的宫廷最为反动。天皇派的胜利,对天皇的支持者来说意味着洗刷耻辱和驱逐外国人;意味着重建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剥夺“改革派”在各种事务中的发言权。强大的外样大名掌控着日本最有势力的藩国,他们成了推翻将军幕府的先锋。他们希望通过“王政复古”来取代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当然他们只想变更一下当权者,并不想改变体系。农民希望能多留下一些稻米,但同样讨厌“改革”。武士想要保留自己的俸禄,并能挥刀作战以赢得更多的荣誉。商人从财力上支持王政复古的军队,希望推行重商主义,但他们也从未责怪过整个封建体系。
当1868年反德川家族的力量胜利后,宣告王政复古,“双重统治”结束。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胜利者将推行的是极端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但事实上,从第一任开始,新政权就采取了相反的措施。它掌权几乎不到一年,就废除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税权。它收回了土地登记簿,并且把农民本应该交给大名的40%的税收占为己有,但在没收的同时也给予了一些补偿。政府分发给每个大名相当于他原本收入一半的俸禄。同时,政府也替大名免除了养活武士家臣和承担公共建设开支的义务。和大名一样,武士阶层从政府直接领取俸禄。在接下来的五年中,新政权又粗略废除了阶层之间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譬如,它规定用徽章或服饰来区分种族和阶层是非法的——甚至脑后的辫子也必须被剪掉——贱民们被解放了。新政权又撤回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移除了隔离各藩的关卡,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了1876年,大名和武士的俸禄又被换算成偿还期为五到十五年的秩禄公债,一次发给,金额可大可小,主要依据每个人在德川时代领取的固定收入而定。这笔钱使得大名和武士有资金在新的非封建经济中开创事业。“这一步最终巩固了商业金融巨子和封建土地贵族之间的特别联手,而这种联手在德川时代已很明显。”
明治政府雏形期的这些重大改革却并未受到民众欢迎。比起改革举措,民众对1871年至1873年侵略朝鲜一事更有热情。但明治政府不仅坚持进行激烈的改革,还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它的施政方针违背了多数曾为其上台浴血奋战过的人们的意愿,于是在1877年,反对派的领袖西乡隆盛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他的军队代表了尊王派想要维系封建制的愿望,而这个愿望在王政复古的第一年就被明治政府否决了。明治政府召集了一支非武士的自愿军,打败了西乡隆盛的武士。但这次叛乱证明了明治政权在日本究竟引起了多么强烈的不满。
农民的不满也很强烈。在明治政府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间(1868—1878),至少爆发了190起农民起义。新政府行动迟缓,直到1877年才第一次下令减轻农民身上的重税,也难怪农民觉得新政权辜负了他们。此外农民们还反对诸如建立学校、征兵制、土地测量、强制剪辫子、贱民的法律平等化、对佛教国教地位的限制、改用阳历和其他一系列改变了他们固定生活方式的举措。
那么,究竟是这个“政府”中的什么人在推行这些激烈而不受欢迎的改革呢?答案是,由日本封建时期的特殊国情孕育的低等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些低等武士在为大名当家臣管家时学会了治国才能,并运作和管理着采矿、纺织、造纸等封建垄断行业。而这些商人们则“购买”到了武士的地位,并在阶层内部普及生产技巧和知识。这个武士商人联盟很快把自信而有能力的人推举为官员,由他们制定明治改革政策和落实计划。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层,而在于他们是如何变得这么精明能干且把握现实的。19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就和今天的泰国一样弱小,却产生了一批有能力的领导人,构想并落实了最有政治风范的成功改革,远超其他国家。这些领导人的强项和弱点其实都深植于传统日本人的性格之中,而本书的主要目标正是讨论日本民族性格过去和今天都是什么样的。在这里,我们只能先了解一下明治政治家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明治政治家们根本没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心中的目标是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容小觑的强国。他们不是打破传统者,因而没有抨击或者摧毁封建阶级。这些政治家只是用丰厚的俸禄诱惑封建阶级,令其转而支持政权。他们最终改善了农民的处境。之所以推迟十年才这么做,与其说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拒绝农民的要求,不如说是因为明治初期国库匮乏。
但是这些精力充沛且足智多谋的明治政治家却拒绝一切终止日本等级制度的想法。王政复古已经简化了过去的等级秩序,废除了将军的地位,使天皇位居顶峰。在王政复古后,政治家们又通过废除各藩,消除了忠于封建领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但这些改变并没有打破等级制的习惯,只是给了这些习惯一个新的位置。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日本新领导人为了向民众推行卓有成效的纲领,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他们通过交替采用“索取”和“恩赐”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当公众舆论反对改用阳历、建立公共学校和废除对贱民的歧视时,他们从没想过要去迎合民意。
自上而下的恩赐手段之一,是1889年天皇对他的子民颁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给予人民地位,并设立了议会。“阁下们”在批判研究西方世界的各类宪法后,精心起草了这部宪法。但是宪法的起草者们却“尽可能地小心谨慎,以防止民众的干涉和公共舆论的侵扰”。起草宪法的机构是天皇内务部门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神圣不可冒犯的。
明治政治家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在19世纪80年代,宪法的起草者伊藤博文公爵就派遣木户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遇到的问题咨询赫伯特·斯宾塞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后,斯宾塞写下自己的意见给伊藤。在等级制度的议题上,斯宾塞写道:日本的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有利于国民康乐的无与伦比的根基,应该对此加以维护和培养。他说,对上级长辈的传统义务以及超越一切的对天皇的义务,都是日本社会的一大优点。日本可以在它的“上级们”的领导下稳步前进,并克服许多在个人主义国家中不可避免的困难。明治政治家们很满意,因为斯宾塞的意见肯定了他们本来的想法。他们意图在现代社会中保留遵循“各就其位”的优势,并且维护等级制习惯。
无论是在政治、宗教还是经济领域,明治政治家们都规定了国家和民众之间“各就其位”的职责。他们的整个纲领和英美截然不同,以致美国人通常会忽视其基本要点。当然,上层强有力的统治可以忽视公众舆论的导向。政府掌控在位于等级制顶端的那些人手中,却从不包括选举出来的人物。在这个层面,民众没有发言权。1940年,这些政府最高层的组织者都是一些和天皇有“联系”的人、天皇身边的顾问,以及天皇御玺任命的高官——包括内阁大臣、府县知事、法官、国家级各局领导和类似高官。但选举产生的官员在整个等级体系中享受不到这样的地位。毫无疑问,议会中由选举产生的成员在许多事务上也没有发言权,譬如任命内阁大臣或者财政局局长或交通局局长。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代表了民众的意见,虽然它拥有一定的质疑或批评高级官员的特权,但它在任命、决策和预算等问题上完全没有发言权。它也从未颁布法令。众议院甚至受到非选举产生的贵族院的制约。贵族院中有一半是贵族,另外的四分之一是天皇任命的。由于它和众议院在批准法令的功能上具有同等权力,等于为众议院多加了一道等级性的制约。
因而,日本保证那些身居政府高位的人能保住“阁下”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各居其位”的体制中就没有自治。在所有亚洲国家,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层的权威总是向下伸展,和来自底层的自治权在某个中间地带相遇。不同国家的差异主要在于:民主责任制能影响多大的范围?它能负起多少的责任?当地领导层能否对整个社区负责,还是他们会被地方势力利用,损害民众利益?德川时代的日本和中国一样,人口中最小的责任单位是由五到十户居民组成的“邻组”。这些由相邻家庭组成的团体的领导人,对组内的事务享有领导权,保证组内居民行为守法端正,上报任何可疑形迹,并把被通缉的个人交给政府。明治政治家们起初废除了这一套,后来又恢复了它,也称之为“邻组”。政府在城镇中积极促进邻组的发展。但在今天的乡村,邻组很少发挥作用,更重要的组织单位是“部落”。部落既没有被废除,也没有被编入政府系统的行政单位。它们是一片国家政权尚未涉足的地带。这些由十五户左右家庭组成的部落在今天依然井然有序地运转着。他们的首领每年轮换,职责主要是“看管部落财产,监督部落对亲人去世或发生火灾的家庭提供援助,定下集体农耕、建造房屋或修葺道路的日期,以拉响火警铃或以敲击节奏的方式宣告节日和休息日”。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不同,这些部落首领无须承担在社区内征收国家赋税的重任。他们的地位很明确,主要就是在民主责任制的地区行使职责。
日本近代的平民政府正式承认市、镇、乡的地方行政机构。公选产生的“长者们”挑选一个有责任心的首领,作为社区代表与代表国家的府县公署和中央政府交涉一切事宜。在乡村,村长通常是一个老居民,一个拥有土地的农民家庭成员。他上任后虽然会有一些经济损失,但获得的声望却是巨大的。他和长老们一起管理村子的财务、公共健康、学校维修,特别是财产记录和个人档案。村公所业务繁忙,它既要负责花费政府对小学教育的拨款,还要负责从当地筹集并花费更大份额的学校开支,管理村子公共产业的租金,土壤改良和植树造林,以及管理所有财产交易记录(这些交易只有在村公所登记后才是合法的)。村公所还必须维护和及时更新当地正式居民的个人信息,包括住址、婚姻、子女出生、领养、前科等等。此外,它还要维护一个家庭档案,其内容和个人档案相似。任何这类信息都会从日本各地转给该居民的原籍官方办公室,并被录入他的档案中。每当该居民想要申请工作,或接受审判,或因任何需要证明身份时,他都会写信或者前往自己的原籍办公室,获得一份个人档案副本,交给有关方面。因此人们是不会轻易让自己在个人或者家庭档案中留下不良记录的。
因此,市、镇、乡肩负着相当大的责任。这是一种社区责任。20世纪20年代,日本出现了多个全国性政党,这在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从此有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交替执政。但哪怕到了那时候,日本的地方行政机构也丝毫未受影响,还是由长老们领导,对整个社区负责。但是地方行政机构在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所有的法官都是由国家任命的,所有的警察、学校老师都是国家的雇员。由于大多数日本的民事案件都是通过仲裁或者第三方调停解决,所以法院在当地行政中的功能非常小。警察反而更为重要。每逢有公共集会时,警察必须在场。但这种任务不常有,警察的大部分时间被用于维护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国家经常调动警察们的岗位,以免他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和当地牵扯太深。学校老师的岗位也经常调动。国家规定了学校的每个细节:和法国一样,全国的每个学校在同一天,学同一本教材,上同一门课。每个学校都在早上的同一时刻跟随同样的广播跳同样的健美操。当地社区在学校、警察和法院三个方面没有自治权。
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的做法在所有基本点上都和美国迥异。在美国,最高行政和司法责任由公选出来的人担负,地方的管理则由当地警局和法院负责。但是,日本政府在形式上却和荷兰、比利时等西方国家没什么两样。譬如说,荷兰和日本一样,由女王的内阁起草所有法律条文,议会实际上从未颁布任何法令。荷兰女王依法任命每个城镇的市长,尽管在实践中她通常都认可地方的提名。因而,较之1940年前的日本,荷兰女王的权力更进一步地渗透到地方事务中。在荷兰,警察和法院直接对女王负责,但任何宗教团体都可以自由创办学校。日本的教育系统则和法国一模一样。同样,在荷兰,开凿运河、围海造田和当地建设都是整个社区的责任,而不是市长和政治选举产生的官员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