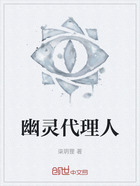
第4章 沉默的解剖台
行动总结、嫌疑人移交、证据初步清点……等陈思安处理完所有后续工作,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自己位于刑侦中心的独立办公室时,窗外的天空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办公室不大,但整洁有序得如同她的思维。文件柜里的卷宗分门别类,标签清晰。办公桌上只有一台高性能电脑、多显示器、一个笔筒和一盏护眼台灯。
唯一显得有点“杂乱”或者说有“人味”的,是桌面一角,一个不起眼的原木相框。
相框里,是一张泛黄、边缘微微卷曲的旧照片。照片的清晰度不高,像是翻拍的。画面中是三个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孩子,站在一片模糊的绿荫背景前,似乎是某个公园?中间的小男孩大约五六岁,笑得一脸灿烂,缺了一颗门牙,手里紧紧抓着一个木制的彩色小风车。左边的小女孩年纪稍小,扎着两个羊角辫,脸蛋圆圆的,正有些害羞地抿着嘴笑,一只手紧紧抓着旁边大姐姐的衣角。右边的大女孩七八岁的样子,是三人中最高的,已经能看出几分清秀的轮廓,她微微侧着头,脸上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安静而略显担忧的神情,一只手臂保护性地揽着小女孩的肩膀。
这就是陈思安仅存的、关于童年的模糊印记——一张没有父母、只有三个孩子的合影。照片背面用褪色的蓝墨水写着三个名字和日期:“安安、小瑾、小迁,摄于XX公园,199X年夏”。这是她辗转多个福利院后,最终被一户善良但无子女的老警察夫妇收养时,唯一随身携带的“财产”。
关于照片的来历、照片里的弟弟妹妹去了哪里、自己的父母是谁……养父母也一无所知,只说送她来的人只留下了这张照片和一个模糊的出生日期。
陈思安疲惫地坐下,身体陷进宽大的办公椅里。她没有开大灯,只拧亮了桌角的台灯。昏黄柔和的光线洒在桌面上,也照亮了那个小小的相框。
她伸出修长的手指,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玻璃表面,停留在照片中间那个缺牙大笑的小男孩脸上。指尖下,隔着玻璃,是那个被称作“小瑾”的孩子无忧无虑的笑容。这个名字,连同“小迁”,是她心底最深的谜团和最柔软的角落。
二十多年了,她从未停止过寻找。利用警方的资源,她做过无数次人像比对、失踪人口数据库筛查,甚至偷偷做过DNA库的盲比,结果石沉大海。
但线索如同投入大海的石子,杳无音信。弟弟妹妹是否还活着?他们过得好吗?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三个孩子流离失所?这些问题如同跗骨之蛆,在每个疲惫的深夜啃噬着她的内心。
她的目光缓缓移向照片右边那个安静的大女孩——那就是童年的自己,“安安”。照片里那双清澈的眼睛,此刻透过泛黄的岁月,与现实中陈思安疲惫却依旧锐利的目光静静对视。那眼神里的担忧……是在担忧什么呢?担忧即将到来的分离?还是……在那一刻,小小的她已经预感到了什么不幸?
一种难以言喻的孤寂感和深藏的悲伤,如同潮水般悄然漫上心头,冲淡了破获大案的短暂喜悦。
她破获了无数案件,将许多罪犯绳之以法,帮助许多家庭找回了失散的亲人,却唯独找不到自己的根。这份缺失,是她内心深处无法填补的空洞,也是驱动她不断前进、追求真相的隐秘动力之一。
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敲响,是李明,手里还拿着个文件夹。“陈队,还没走呢?局长说放你一天假,好好休息。”他看着陈思安疲惫的脸色和桌上亮着的台灯,关心地说。
陈思安迅速收敛了外露的情绪,恢复了干练的模样:“马上就走。还有事?”
“哦,这是‘影梭’案关键电子证据的初步分析摘要,还有……关于那条匿名信息,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暂时还是没有任何头绪。发送者非常专业,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追踪的电子指纹。目前只能存档为‘X信息源’。”李明将文件夹递上,语气带着无奈。
陈思安接过文件夹,点点头:“知道了,辛苦了。‘X信息源’继续留意,有异常第一时间通知我。”她将文件夹放在桌上,正好压住了相框的一角。照片里“安安”那双担忧的眼睛,被文件夹的边缘遮住了一半。
离开警局时,天已微亮,深秋的清晨寒气袭人。陈思安拒绝了李明和其他同事去喝早茶庆功的提议,独自走向公交站。她租住的警局宿舍位于市中心一个老旧小区,优点是离单位近,缺点是环境嘈杂,尤其是清晨,楼下早餐摊的叫卖声、车流声、邻居的争吵声总是不绝于耳,让她本就因高强度工作而脆弱的神经得不到真正的休息。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房屋中介小吴发来的微信,还附了几张图片:
“陈姐,早啊!昨天您说想换个安静点的地方,我连夜给您筛了几套!重点推荐这套‘暮云公寓’!虽然是老建筑翻新,但位置闹中取静,安保据说很好,关键离你们市局也不算太远!性价比超高!图片您看看,感兴趣的话随时约看房![位置链接][公寓外观图][样板间图]”
陈思安点开图片,暮云公寓的外观图在晨曦中呈现出来——崭新的玻璃幕墙包裹着隐约可见的旧砖石结构,带着一种奇特的、新旧交织的矛盾感。
这矛盾感让她莫名地心头一动,照片里公寓显得很安静,环境清幽,绿化也不错。位置确实符合她的要求,离市局车程在可接受范围内,价格也在预算内。
更重要的是,“暮云”这个名字,以及那种新旧交融的独特气质,不知为何,让她想起了那张泛黄照片里模糊不清的背景,以及那个丢失在时光深处的、叫做“家”的地方。一种难以言喻的、如同磁石般的吸引力,悄然在她疲惫的心底滋生。
她站在微凉的晨风中,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空,又低头看了看手机屏幕上暮云公寓的照片。然后,她回复了中介:“就这套吧。今天下午三点,带我去看看。”
……
海津市法医病理学中心的空气,永远带着一种独特的、深入骨髓的冰冷。那不是空调刻意营造的低温,而是一种混合了消毒水、福尔马林、以及某种更深层、更难以名状的无机质气息的、属于死亡国度的恒常温度。这种冰冷,能穿透最厚实的衣物,渗入肌肤,试图冻结所有属于生者的躁动与温度。
此刻,已是深夜十一点。中心大楼的大部分区域都已陷入沉睡般的寂静,只有位于地下二层的核心解剖室,依旧灯火通明。
惨白的无影灯光从天花板倾泻而下,将室内照得亮如白昼,没有一丝阴影可以藏匿。冰冷的金属器械在灯光下反射着森然的光泽,整齐地排列在器械车上,如同等待检阅的士兵。巨大的不锈钢解剖台占据着房间中央,台面微微倾斜,连接着隐藏的排水系统。
空气中,那股浓烈到足以让普通人瞬间呕吐的恶臭,如同无形的粘稠液体,沉甸甸地压迫着每一个进入者的感官。
尹随迁站在解剖台前,身影在强光下显得有些单薄,却又带着一种磐石般的稳定。一身合体的深蓝色法医制服包裹着她纤瘦的身躯,外面罩着同样深色的防水解剖围裙。乌黑的长发被一丝不苟地挽成一个紧致的发髻,藏在一次性手术帽下,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和线条优美的颈部。她的脸上戴着一个贴合度极高的N95口罩,上面加戴了一层透明的防护面屏,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
清澈,平静,深邃得如同幽潭。没有厌恶,没有恐惧,甚至没有一丝波澜。面对解剖台上那具高度腐败、视觉冲击力足以摧毁常人理智的河漂尸体,她的眼神专注而纯粹,如同一位最严谨的科学家在观察一件极其复杂的标本,又像一位最耐心的考古学家在清理一件深埋地底的珍贵文物。
所有属于人类本能的、对死亡和腐烂的生理性排斥,在她这里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屏障彻底隔绝。
尸体呈现出典型的“巨人观”晚期特征:全身肿胀如鼓,皮肤呈现出污绿色与暗紫色交织的斑驳,紧绷得近乎透明,仿佛随时会爆裂开,渗出里面高度腐败的液态组织。面部五官扭曲变形,眼球突出,口唇外翻,露出暗色的牙龈和部分牙齿。大量腐败气体在皮下积聚,使得胸腹部高高隆起。皮肤表面覆盖着一层滑腻的、灰白色的尸蜡样物质,夹杂着泥沙和水藻的碎屑。更令人作呕的是,尸体表面和自然开口处,密密麻麻地蠕动着大量灰白色、半透明的蝇类幼虫,它们贪婪地啃食着腐败的组织,发出极其细微、却如同魔音灌耳般的“沙沙”声。
空气中弥漫的恶臭,是腐败气体混合着河水腥气、淤泥土腥味以及蛆虫分泌物形成的、一种复杂到极致的、足以粘附在灵魂上的恐怖气味。
它无孔不入,穿透口罩的过滤层,顽固地刺激着嗅觉神经。
然而,尹随迁对此似乎毫无所觉。她的呼吸平稳而悠长,透过口罩的节奏没有丝毫变化。她只是微微调整了一下头顶无影灯的角度,让光线更精准地照射在尸体的双手部位。
解剖开始前,尹随迁进行着一套近乎仪式般的准备动作。这不仅是技术规范,更是她进入工作状态的必要心理程序。
她首先戴上第一层薄而贴合的乳胶检查手套,仔细检查确保没有任何破损。然后,再套上第二层更厚实、防切割防穿刺的丁腈解剖手套。
两层手套之间,她习惯性地撒上少许滑石粉,确保绝对的贴合与灵活。戴好手套后,她会反复握拳、张开数次,感受指尖的触感。
紧接着做好相应的防护,在N95口罩外再加透明面屏,确保飞溅物和可能的病原体被彻底隔绝。
做好一切之后,她的目光扫过器械车:锋利的手术刀、各式剪刀,比如直头、弯头、组织剪、镊子有齿、无齿、精细尖头、骨钳、肋骨剪、取样用的无菌容器、棉签、载玻片、放大镜……每一件都摆放得如同尺子量过一般精确。
她伸出戴着双层手套的手指,轻轻拂过手术刀的刀柄,确认其稳固性,如同剑客确认自己的佩剑。
在正式触碰尸体前,她拿起一瓶75%的医用酒精,仔细喷洒在解剖台边缘、器械车表面以及自己的双层手套上。酒精浓烈的气味短暂地压过了尸臭,带来一丝冰冷的洁净感。
一切准备就绪,尹随迁拿起锋利的手术刀,刀锋在无影灯下划过一道冰冷的弧光。
解剖过程是沉默的,没有多余的言语,只有器械触碰组织、骨骼时发出的细微声响:刀锋划开肿胀皮肤的“嗤嗤”声、剪刀剪断筋膜的“咔嚓”声、骨钳分离肋骨的沉闷“咯啦”声……以及,那无处不在的、蛆虫蠕动啃食的“沙沙”背景音。
她的动作精准、稳定、高效,没有丝毫犹豫或多余。每一个切口,每一次分离,都遵循着最严格的解剖学路径,最大限度地保存可能存在的损伤证据。
她的助手,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法医助理小王,站在一旁,脸色苍白,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冷汗,即使戴着口罩也能看出他在极力忍耐着不适。
他负责记录、传递器械和拍照。他看着尹随迁那冷静到近乎冷酷的操作,看着她面屏后那双毫无波澜的眼睛,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震撼和……一丝敬畏。
尹随迁的目标明确:在高度腐败和自然环境破坏的双重干扰下,寻找那些被掩盖、但尚未被彻底摧毁的真相密码。
首先,是胃内容物:最后的晚餐与致命线索。
腐败使得腹腔脏器如同一锅粘稠的、污秽不堪的浓汤。尹随迁小心翼翼地切开高度膨隆的胃壁,一股更加浓烈的、混合着酸臭和腐败食物残渣的气体涌出。
小王忍不住干呕了一声,下意识后退半步。
可尹随迁恍若未闻,她使用特制的宽头镊子和勺子,极其耐心地在腐败的食糜和半消化的组织碎片中仔细翻找、筛选。她的动作轻柔而稳定,如同在淤泥中淘金。
很快在胃底部,避开腐蚀最严重的区域,她找到了一些相对完整的、未被完全消化的食物残渣:几片深绿色的、边缘锯齿状的植物叶片碎片;少量半透明的、类似虾壳或小型甲壳类动物的残骸;几粒微小的、呈不规则多面体的深蓝色颗粒,质地坚硬,与食物残渣明显不同。
她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关键残渣分别装入不同的无菌容器中,贴上标签。尤其是那几粒深蓝色颗粒,她用精细的尖头镊子单独夹取,放入一个微型物证瓶。
“胃内容物样本,重点分析植物叶片种类、甲壳类来源,以及…这些蓝色颗粒的化学成分。”她的声音透过口罩,冷静地指示小王记录。
尸体的双手肿胀变形,指甲缝里塞满了黑色的淤泥和水草。尹随迁用镊子夹起死者的手指,凑近灯光,拿起一个高倍放大镜仔细观察。
她使用细小的探针和冲洗器,极其耐心地、一点一点地清理掉指甲缝中的淤泥。这不是简单的清洁,而是一场在方寸之地进行的精密考古。
下一秒,她在右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甲缝深处,淤泥之下发现了一些异常的微量物质:几根极短的、亮红色的人造纤维,材质看似化纤。几颗极其微小的、半透明的、不规则的晶体颗粒,夹杂在淤泥中。还有一些深灰色、带有金属光泽的粉末状微粒。
她用沾湿的精细棉签,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微量物质分别从指甲缝中沾取出来,转移到专用的微量物证载片上,并立刻覆盖保护盖玻片。
“指甲缝微量物证:红色纤维、未知晶体、金属粉末。需进行显微形态学观察、纤维成分分析、晶体X射线衍射、粉末能谱分析。”她的指令清晰明确。
相对于其他,尸体上蠕动的蛆虫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但在尹随迁眼中,它们却是精准的“死亡时钟”。
只见她使用宽头软毛刷,小心地从尸体不同部位收集了不同发育阶段的蝇类幼虫样本,放入装有特殊防腐液的收集瓶。
同时,她还收集了一些附着在尸体上的蝇蛹和空蛹壳,以及几只尚未飞离的成蝇标本。
随后她拿起一个放大镜,仔细对比不同部位蛆虫的体长、体节形态、口器特征。“主要种类为丝光绿蝇和伏蝇,幼虫体长在1.0-1.5厘米区间,部分进入三龄末期,有少量蛹壳出现。成蝇为丝光绿蝇。”她低声自语,如同在解读一份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