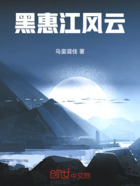
第2章 黑惠江与腊罗巴的前世今生
乌蛮滋佳童年的底色,是阿公段勇火塘边摇曳的橘红色火光,以及窗外永恒流淌的黑惠江低沉的絮语。阿公的眼睛,是乌蛮滋佳见过最深邃的潭水,比黑惠江最深处的漩涡还要幽深。那里面沉淀着几十年的风霜雨雪,映照着江畔世世代代腊罗巴人负重前行的背影,也闪烁着古老故事不灭的微光。在珠街彝族乡层峦叠嶂的山坳里,依山而建的土坯房如同大地的褶皱,而屋内那一方用厚实石板垒砌、终年燃烧不熄的火塘,便是整个家、乃至整个族群精神世界的“心脏”。阿公段勇,就是守护这颗心脏的长者,他口中流淌的故事,如同在火焰上轻盈跳跃、永不疲倦的精灵,将无形的文化根须,深深扎进滋佳幼小的心田。
流过昌宁县珠街彝族乡的黑惠江,绝非一条寻常的河流。它是澜沧江左岸血脉贲张的最大支流,更是横亘在滇西高原脊背上一条奔腾不息、承载着磅礴自然伟力与厚重人文积淀的“活态史诗”。它的源头,在遥远的丽江玉龙雪山晶莹的冰川融水之中,一路向南,像一把无畏的刻刀,深深切入横断山脉千沟万壑的褶皱地带。在珠街乡22.5公里的蜿蜒旅程里,它年均123立方米/秒的丰沛流量,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命脉。江水如一条碧绿的丝绦,将大理、保山、临沧三州(市)的山川人文悄然串联,下游的剑川沙溪古镇沉淀着茶马古道的蹄印,漾濞石门关诉说着造化的鬼斧神工。而在珠街,它则挥毫泼墨,绘就了“一江分两岸,群山拥水来”的壮阔画卷。江水切割出陡峭的峡谷,两岸梯田层叠如登天之阶,村寨星罗棋布,仿佛群山忠诚的守卫,日夜聆听着江水的脉搏。
“滋佳哎,过来。”阿公的声音低沉而温和,带着火塘烟熏火燎的暖意。他伸出布满老茧、沟壑纵横的手,从窗台上一个盛满各色江石的粗陶碗里,拣出一块。那石头约莫鸡蛋大小,通体是深邃的青黑色,表面异常光滑圆润,在火光的映照下,泛着温润如玉的光泽,仿佛被江水亿万次的抚摸赋予了生命。“你看这江滩上的石头,”阿公将石头轻轻放在滋佳摊开的小小掌心里,那冰凉坚硬的触感瞬间传递过来,“每一块都是黑惠江的孩子,肚子里都藏着江水讲不完的故事呢。”
滋佳的小手紧紧攥住石头,冰凉的感觉从掌心蔓延到心底,他睁大眼睛,专注地听着阿公用那特有的、如同江水漫过卵石滩般沙哑悠长的语调讲述:“老辈人传下来的话,说这黑惠江啊,原本是天上的银河,不小心落了一段在人间。天上的神仙怕凡尘的喧嚣惊扰了星辰的清梦,就派了两条神通广大的巨蟒下来镇守。一条是通体乌黑的黑蟒,一条是鳞甲如雪的白蟒。它们潜入江底,首尾相连地盘桓守护,它们的魂魄啊,就化作了这江水的精气神。你看那江水,深的地方墨绿幽暗,是黑蟒在蛰伏;浅滩浪花翻涌雪白,那是白蟒在嬉戏游动。”阿公的手指随着叙述,在空中虚划着巨蟒游弋的轨迹。
乌蛮滋佳听得心驰神往,小小的身体不自觉地挺直了。他攥着那块冰凉的江石,仿佛真的能感受到来自远古洪荒的森然气息。他望向窗外沉沉的夜色,想象着黑惠江的源头,在那云遮雾绕的玉龙雪山深处,是不是真有星辰坠落时遗落的点点微光,在冰冷的山涧里汇聚,最终奔涌成这条充满灵性的大江。阿公常说,黑惠江流经的土地,就是腊罗巴人血脉扎根的地方。昌宁县珠街乡这一片被群山环抱的河谷坝子、层叠梯田,是江水用千万年不屈不挠的冲刷和沉淀,在坚硬的山体间硬生生“拓印”出来的家园。没有黑惠江,就没有腊罗巴人。
“我们腊罗巴人啊,”阿公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神圣的庄重,他拿起靠在墙角、被岁月和手掌摩挲得油光发亮的长杆烟锅,装上自家种的烟叶,就着火塘里跳动的火苗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辛辣的烟气弥漫开来,与松脂、柴火的香气混合,“是踩着黑惠江的节拍过日子的。江水涨落,就是我们的日历;江水的声响,就是我们的歌谣。”
他缓缓吐出一缕青烟,目光仿佛穿透了土墙,投向奔腾的江水:“开春,江水解冻,水色一天天由深绿转成透亮的浅碧,岸边攀枝花开得像烧着的火云。这时候,就得去江边‘祭水神’了。要请水神爷爷开恩,赐下恰到好处的雨水,让江水既不要像脱缰的野马冲垮田地,也不要吝啬得断流,让田里的秧苗渴死。”滋佳仿佛看到薄雾清晨,长者们肃穆的身影。
“等稻谷抽穗,田野一片翠生生的绿浪,风吹过沙沙响,那是丰收在跟你打招呼。这时候,就得在田边,对着江水唱‘栽秧调’了。要把心里的期盼,把汗水的咸,把日头的辣,都唱给江水听,让它把这期盼带到土地深处,带到老天爷的耳朵里。”阿公的语调模拟着栽秧调的高亢悠扬。
“最热闹的,还是火把节。到了农历六月二十四,整个寨子就像被点着了一样!家家户户扎火把,松枝要干,茅草要韧。天一擦黑,火把点起来,汇成一条火龙,直奔江边的空坝子。男人们吹起过山号,‘呜——呜——’的声音能撞到对面山上再弹回来!围着篝火‘打歌’,那三弦、芦笙、笛子响成一片,脚步踏得地皮都在颤!要把一年的晦气、病痛都跳走、烧光!火把的光映在江面上,一跳一跳的,那是给祖先引路的灯,照亮他们回家看看的路……”阿公的眼睛在火光中熠熠生辉,滋佳仿佛听到了那震天的号角和热烈的舞步声。
阿公的故事,从不空洞,总是像江岸上茂盛的植物,生长出具体的枝蔓和果实。他会细致地描述腊罗巴女人如何“纺线织布”:坐在木楞房的屋檐下,古老的木制纺车吱呀作响,她们灵巧的手指捻动着从山野采来的木棉和自家种的苎麻,纺成粗细均匀的线。然后,在简陋的木织机上,梭子如鱼般来回穿梭,将阳光的金线、江水的碧纹、山林的青黛,都一丝一缕地织进土布里。再用蓝靛、核桃皮、紫草根等天然染料,染出象征高远天空的深邃蓝,象征肥沃土地的温暖褐,象征生命火焰的炽烈红。那些绣在衣襟、围腰、包头上的繁复花纹——羊角纹、蕨菜纹、太阳纹……每一针都是对自然的摹写,对祖先的纪念。
他会绘声绘色地讲月夜“打歌”的热闹场景:皎洁的月光洒满晒谷场或江边空地,男人们盘腿坐在地上,或抱着粗犷的三弦,或吹着清亮的竹笛,或按着浑厚的芦笙。女人们换上最鲜艳的绣花衣裳和围裙,银饰在月光下叮当作响。弦声一起,脚步便不由自主地跟上,从舒缓的“两步一跺”,到欢快的“三步一颠”,再到狂放的“苍蝇搓脚”、“喜鹊登枝”……脚步踏地的节奏,应和着弦声的韵律,竟与江水拍打石滩的哗哗声奇妙地共振。那不是表演,那是生命力的自然奔涌,是族群情感的集体宣泄。
他还会讲“吃火酒”的古老规矩:逢年过节,或是重要的祭祀之后,家家户户会用土陶罐在火塘边煨上自家用苞谷或高粱酿造的米酒。酒热了,香气弥漫开来。第一碗酒,必先恭敬地泼洒向火塘上方(敬天),再泼洒向地面(敬地),最后庄重地洒在堂屋供奉祖先牌位的角落(敬祖先)。然后,家中的长者,通常是阿公自己,才会端起酒碗,抿上一口,再依次传给围坐火塘的家人。那酒味醇厚,带着米粮的甜香,也带着黑惠江水的清冽,更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暖意在酒碗传递间流淌。
乌蛮滋佳最着迷的,是阿公每每讲到兴浓时,会颤巍巍地起身,从火塘上方悬挂杂物的木梁上,取下那把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竹笛。笛身因年深日久的抚摸而呈现出深沉的琥珀色,温润光滑。阿公吹笛的动作很慢,布满老年斑和皱纹的手指,在笛孔上起落、滑动,那动作轻柔得仿佛不是在按孔,而是在深情地抚摸黑惠江那永不停歇的、起伏的波纹。当气息透过笛膜,低沉、苍凉又带着一丝沙哑的笛音便在火塘边幽幽响起。那笛声没有固定的、写在纸上的曲谱,全凭阿公的心绪流淌。时而如江水呜咽,时而如山风低徊,时而如鸟雀啁啾。滋佳觉得,那就是黑惠江在用自己的语言,呢喃着那些藏在浪花深处、只有江底石头和岸边古树才知道的古老秘密。
“阿公,”有一次,乌蛮滋佳趴在窗台上,望着黑惠江蜿蜒流向远方,消失在云雾缭绕、层峦叠嶂的尽头,忍不住问,“江的那边,是什么样子?”
阿公拨弄笛孔的手指停了下来。他放下竹笛,目光追随着江水消失的方向,久久地凝视着。火塘的光在他沟壑纵横的脸上跳跃,那双深潭般的眼睛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有对远方的遥想,有对已知世界的笃定,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未知的淡然。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缓开口,声音比平时更加低沉:“滋佳啊,江的那边……还是山。重重叠叠的山,比我们这边或许更高,林子或许更密。山的那边,也还是我们腊罗巴人的寨子,说着一样的话,跳着一样的舞,敬着一样的神灵和水神。再远一些……山外面,或许就是坝子(平坝地区),住着种水田的傣族,住着养牛羊的藏族,住着做生意的汉族……他们过日子的法子跟我们不一样,穿的衣服不一样,唱的歌也不一样。”阿公顿了顿,拿起烟锅深深吸了一口,目光重新聚焦在滋佳充满好奇的小脸上,语气变得格外郑重:“但是啊,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远,水,总是连着的。澜沧江连着黑惠江,黑惠江又连着无数的小溪小河,最后都流进了大海。人心呢,有时候也像这水。我们腊罗巴人,祖祖辈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走到哪里,脚底板都要记得梯田的泥巴是啥感觉;耳朵里都要留着黑惠江哗啦啦的响声;心里头更要装着阿公教给你的这些老规矩、老故事。它们是根,扎得深,人才站得稳,走得远。”
那时的乌蛮滋佳,对“根”的理解还很模糊。但阿公眼中那份前所未有的郑重,以及话语里沉甸甸的分量,让他把这些话像珍藏最心爱的江石一样,深深地藏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他懵懂地意识到,窗外日夜奔流的黑惠江,绝不仅仅是一条提供水源的河流;阿公火塘边那些似乎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也绝不仅仅是打发长夜的消遣。它们是某种更宏大、更深刻、更本质的存在。像千年古树深扎大地的虬根,牢牢抓住滋养他们的土壤;也像无形的丝线,将他小小的生命,与脚下这片名为“珠街”的土地,与“腊罗巴”这个古老的名字,紧密地、永恒地缝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