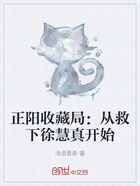
第12章 家喻户晓
煤炉的火光在博物馆修缮室的窗玻璃上跳动,映得苏浩然的的确良衬衫泛着暖黄。他握着修复笔的手悬在《千里江山图》上方,笔尖距离绢帛半寸时,掌心的青铜钥匙突然传来细密的震颤——那是系统任务触发的信号,像极了正阳门小学下课铃在神经深处的回响。视网膜边缘泛起极淡的金圈,“修缮传世之作《千里江山图》”的信息与画中石青颜料的荧光完美重合,恍若王希孟的笔锋穿越八百年,在他视网膜上重新勾勒出少年画师的锐意,那些被虫蛀的裂痕在他眼中化作可解的算术题,每道皴法都是需要对齐的公式。
正阳门的晨光裹着煤炉的硫磺味钻进窗缝,牛爷的鸟笼在槐树上晃出细碎的响。笼中靛颏儿正啄食着徐慧真送来的熟小米,瓷食罐沿还沾着小酒馆的酱牛肉碎屑。李大娘的棉鞋刚踏进胡同,石板路上的积雪就“咯吱”作响,立刻有三五个婆娘围上来,棉袄上的补丁在晨光里泛着不同的布纹——有陈雪茹送的丝绸边角,也有徐慧真小酒馆的粗布,针脚间还隐约可见“增产节约”的字样。“李大姐,苏老师真在故宫修皇上的画?”张婶的声音里带着敬畏,她袖口的补丁恰好拼成个“山”字,像极了《千里江山图》里的峰峦。
“可不是嘛!”李大娘拍着《选民证》封面的小本本,五角星徽章歪向一侧,露出底下补了三次的内衬,“石先生都说了,苏老师的笔锋能接住王希孟的火气。”她压低声音,目光扫过街角范金有的住处,后者正蹲在地上用炉灰掩埋臭鸡蛋,搪瓷缸踢得叮当响,“昨儿陈雪茹往苏老师宿舍送了三匹杭缎,说是给修画的人‘补补气血’,慧真那边更实在,一早熬了牛骨汤,让我捎给苏老师——你说这俩女人,较着劲呢。”
胡同深处,范金有的搪瓷缸“当啷”摔在地上。他盯着墙根的臭鸡蛋——不知哪个孩子学大人的样,用草纸包着扔在他门口,蛋液顺着砖缝流成歪扭的“苏”字,冻成冰碴的蛋黄像极了他胸口的街道办徽章。隔壁传来徐合生的咳嗽声,这位曾经挺直腰板的小学教师如今佝偻着背,每天清晨都要对着墙根的毛主席像鞠躬三次,镜片上永远蒙着层白雾,像极了修缮室里未干的胶矾水。他床头的搪瓷缸里泡着隔夜的棒子面粥,缸沿刻着“为人民服务”,却被酸馊味浸得发暗。
博物馆修缮室的煤油灯结着灯花,灯芯“噼啪”爆响,火星溅在苏浩然的帆布包上,那里装着从藏宝室带来的明代浆糊瓶,瓶盖上的“盘尼西林”标签早已磨掉,露出底下系统奖励的“矿物调和术”图谱。他的笔尖终于触到最后一处金粉隐笔,手腕因长时间悬停而发抖,却在接触绢帛的瞬间,系统灌注的“劈笔皴”技法如皮影戏般在眼瞳里展开,连王希孟当年握笔时虎口的汗渍痕迹都清晰可辨。修复进度条跳至 100%的瞬间,青铜钥匙突然发出几乎不可闻的“咔嗒”,像古籍合页时的轻响,更像正阳门老窑砖在火中开裂的声音。
他眼前一阵发黑,却在倒下前看见石先生的白胡子在画案前颤动——老匠人正用放大镜检查最后一道皴法,镜片上反着激动的泪光,手中的竹尺无意识地敲出《千里江山图》的节奏。快手张的山东腔混着煤炉的咕嘟声炸开:“小苏老师熬了五宿,把千里江山的火气续上了!”他袖口的石绿粉末落在苏浩然的帆布包上,与包里的老窑砖拓片相映成趣,那些系统奖励的“蓝色收藏品信息”正以汴京官瓷的冰裂纹路,在拓片边缘悄然显形。
石先生亲自给苏浩然盖上蓝布被,发现他衬衫口袋里露出半张粮票,正是李大娘给的那半张,边缘还留着小酒馆的油渍——徐慧真总在粮票背面画小酒坛,说是“看着解馋”。“等小苏醒了,去职工食堂换碗红烧肉,”老人对陈雪茹派来送布料的伙计说,“就说故宫的老师傅们凑的粮票——范金有那小子,今儿晌午刚把自己的工作证擦了三遍。”修缮室的空气里飘着石青与石绿的混合气息,像极了正阳门胡同里各家各户熬中药的味道,带着岁月沉淀的醇厚,又有新社会的蓬勃。
苏浩然醒来时,修缮室的煤炉已换成了电炉——这是文物局特批的“先进设备”,金属表面还带着新漆的气味,与他帆布包里的青铜钥匙形成奇妙的冷热对比。他摸着饥肠辘辘的肚子走到胡同口,炸酱面的香气立刻勾住了脚步,那浓郁的酱香里混着正阳门特有的黄土味,像极了他在藏宝室调配的矿物颜料。“来三碗!”他的声音惊得掌柜的差点摔了面碗,瓷勺在大锅里划出清亮的弧光,面条端上来时,黄瓜丝与豆芽在酱色里浮沉,像极了《千里江山图》里的江水波纹,系统提示的蓝色收藏品信息正以汴京官瓷的纹路在他视网膜上流动,那是比《书生饮酒图》更高阶的存在,或许藏在正阳门某户人家的夹墙里,等着他用修画的笔锋去唤醒。
付账时,苏浩然摸到口袋里的青铜钥匙发烫,想起藏宝室里的《千里江山图》残片——那是修缮时特意留下的,边缘的虫洞被他用陈雪茹送的杭绣线补成竹节形状,此刻正与系统奖励产生共鸣。他忽然明白,所谓蓝色收藏品,或许就藏在正阳门的老窑深处,那里的砖纹与画中隐笔的“天下太平”暗合,就像他给学生们讲课时,用粉笔在黑板上画的每一道弧线,都在为某个更大的图景添砖加瓦。
修缮室的木门“吱呀”推开,石先生的中山装换了新布,第三颗纽扣终于缝上了——这次用的是陈雪茹送的湖蓝线,针脚细密如苏浩然给学生们抄题时的字迹。老人的白胡子梳得发亮,别着枚极小的五角星徽章,是李大娘硬塞给他的:“戴着,沾沾正阳门的喜气。”“小苏啊,”他的声音里带着难得的颤音,“文物局要办庆功宴......”话音未落,快手张的山东腔从门外传来,带着浓浓的酒气和瓷瓶相碰的脆响:“别墨迹了!老子把故宫的‘乾隆御酒’都顺出来了,就等你开瓶呢!”他抱着酒坛进门,袖口还沾着修缮时的石青,像极了从画中走出的仙人,酒坛封口的红绸上,赫然印着“为人民服务”。
窗外,陈雪茹的丝绸店挂起了新幡,“庆祝《千里江山图》修缮成功”的红绸在风中猎猎作响,与徐慧真小酒馆新贴的“苏老师庆功宴专用”红纸相映成趣。徐慧真正往保温桶里装热汤,特意多撒了把陈雪茹舍不得用的八角,蒸汽顺着门缝钻进修缮室,混着墨香与酒香,织成一张温暖的网。她不知道,陈雪茹此刻正在店里对着镜子调整旗袍,领口别着枚极小的青玉竹节胸针——那是苏浩然修缮时送她的答谢礼,用的正是画中剥落的石青粉末。
苏浩然摸着帆布包里的修复工具,忽然听见远处胡同里传来孩子们的笑声,像极了他课堂上粉笔划过黑板的“沙沙”响。雪又开始下了,修缮室的电炉“滋滋”作响,映得《千里江山图》上的峰峦愈发青翠。他望向画中隐笔处的“天下太平”,忽然觉得这四个字不再是古人的祈愿,而是此刻正阳门的煤炉、小酒馆的热汤、丝绸店的机杼声,是牛爷的旱烟、李大娘的小本本、甚至范金有颤抖的搪瓷缸——是无数双手共同托举的文明传承,就像他修复的不仅是一幅古画,更是一个时代对美的执着与守望。
当快手张的酒坛在画案上磕出清响,当石先生用竹尺在宣纸上画出第一笔庆功宴的请柬,当正阳门的炊烟与博物馆的灯火在雪幕中交织,苏浩然知道,属于他的故事才刚刚开始。那些在修缮室度过的日夜,那些与老匠人碰撞出的火花,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温暖,都将成为他继续前行的底气——就像《千里江山图》在绢帛上绵延的峰峦,他的路,正随着时代的笔锋,向更广阔处延伸,而手中的修复笔,终将在时光的绢帛上,画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丹青长卷。